-- �@�̡G�Z�ҫU�l
-- �o���ɶ��G2008/2/13 �W�� 11:26:39
--
���U�����ԧ�
 ���D�D�����Ϥ��p�U�G ���D�D�����Ϥ��p�U�G

�m�g�L�n
�X����Q��A���W�X�}�I�X
�b��o�X�L�Ǥf��A���t�q���ש�U�O�⤺�����b����X�}�C���ɹ�o�����x�Ʀ�ʡA���t�a�W�U�èS���Ӥj���~�{�C�X�@�G�U���d�H���j�x�A�I�J���i�A����u���T�d�H���k��´�ЫH���A���t�q���s�b���˩ʪ��u�աA���ɤ��t�a�������{���q���|�D�J���Z�C����Q��A�W�U�H�������w�����b���t�]���~�A�dzƦV���i�X�o�C���t�j�x�����W���j�N�O�軷�����쨦�����D���쪽��(���F����)�C�����O��[�J���t�a���s�ѥ~�˲��A�o�����X�}�]�O�V���t�a���ܩ��ߪ��@���ҩ��C�t�@�������W�j�N���O�~�ȤQ�E�����Q�����d�A�]�N�O��Ӫ��w�t�a�d�C���d�b��}�X�x�������Ԥ��A�]���־ԥ\�ӳƨ����t�q�����g��F�Ӧb�����ĤG�����X�}�A���d�@�v��@�d�l�H�P���쪽���@�P�X�o�C���W�����ۤ��t�]�����|�}���X�o�A�}�l�F�o���v�T���j���ԧЪ��ǹ��C
�ܩ�q�����x���ХN�a�ڲ����X�}����A�@�������Q�黡�ΤQ�G�黡�C�m����k�v���y�n���O���u���t�q����A�H���n�ѤU�A�J����a�������C���@�e�B�����B�T�e�T��o�G�X�}�R�O�A��զX�@�G�U�l�M�K�����K�øS�T�~����Q��A�j�N�q�����@�e�X�o�A着�}���êK(�@�e�j���t����)�K�v�A�ӡm�v�@���O�n�P�˫��X�u�@�e�ꤵ�t�q����A���h�v(����)���{(´�ЫH��)�A�v�|�U�l���H�ơA��øS�T�~����Q��۩���(���t�])�X�o�K�U���K�v�H�ᦳ���֥v�ѳ��H�u����Q��v���q���X�}������C���ھڥv�ƫH�̩ʸ������m�T�e���y�n�O���A�q���X�}���������Q�G��C���̰��V����Q�G�黡�C�ƹ�W�A��ɥN���x�D�B��D��סA���h��e�ǤT�H�æ�A�ƶq�e�j���j�x�q�L�o�ǯU������D�ɡA��x�t�צ۵M�|���v�T�C�ھګ�@�x�ƱM�a������A���U�����ԫe�᪺���t�x�A�䲾�ʳt�ץ����O�T����(�m�饻�ԥv�D��s(�G)�n)�C�]���A�������ʤ��ɡA�N�X�{�������H���A���W�����P���}���������A�������ɶ��W���۹j�A�o�˥��}�����~�බ�Z���X�}�C�A�̡A�������X�}�ëD��}�ϴ���ʡA���W�B���������õL�ݭn�@�P��x�F�A�[�W�����ӥX�}����W�B������x����x�ɮt�A�Q�G�餧���k���T����X�z�C
�X����Q�G��A���M�`���X�}�I�X
�q���b�Q�G��q���t�]�X�}�C�@�p�W�z�A´�ЫH����q�����T���ͤ��F�¯١C�Ӥ��R���ɪ��F�v���ҡA�b���w�x�T��P�����O�@�U�A���t�⪺�_�B�F�⭱�����O�Ȯɱo������A��b�O�X�}�����n�ɾ��C�i�O�A�����֥v�Ƴ��O���q���X�}�ɪ��غةDz��{�H�C�P�ɥN���Ѫ��m���N�O�n�O���u�q���V�T�e�i�o���ɡA�o���_�S���ڡC�ڤ����(�q���̥ȼs�f��)��q�����y�����X�}��������]�I�z�q���^���D�y���D�ڤ��Ĥ]�A�����Ϋv�H�z��ܤS���y���t�a������o�A�i���ܶܡH�n�T�d�ܡH�z�q���ڿ��C����A�q�L�@�e�êK���ɡA�q�������ܥߩ��m���A����M�l�A���q���e�ᤧ�̫o�ݤ���C���_�S���ƫv�I�v(���@)���ҩP���A�q���̥ȼs�f���b���ܤ��t�a�����쪺��ܤ��ä��L�Ѧ۱��A�m���N�O�n�N�O�y�z�ȼs���`�F�U���q������X�}�C���F�m���N�O�n�~�A����٦��ܦh�U���U�˪��Dz��ǻ��A���O���X�q���X�}�O���N�����ơC�n���m���n�O�n���O���u�W���u�d���F�C�{�a�����ƥ��M�X�{�A�b�q���X�}�A�V�L�w���t�ɤ]��M�X�{�A�q����ظ@�K�v�t�~�A�������q���X�}���ɡA�ǻ����u���t�]�����s���ժ���M�ݽ��}���Ӧ��A�ɤH�Y�١u���t�a�O���X�}�D�����]�I�v�����C�q�W�z�ݨӡA�n�����ܦh�譱�����k���w����q���b���U���Ԧ������C���M�A�o�j�h���O���G�סA�H�q���������i�ӳЧ@�}�F�A��b�O�������H�C
�X����Q�T��A�V�����i�o�I�X
�q�����x�b�Q�G��X�o��A�P���F�êK�A�ӥ��W���h��F���������t���C�Q�T��A���t�q���������d�b���t���A�ӥ��W���w��L���������s�t�A�V�ް����i�o�C���t���O���������@�ӭ��n�����A�]�O�F���D���u�W����u�n�I�A��O�J�@�e�����g�a�F�������A���t���O�t�d�u���@�e���䪺�̫�@���C���ɪ����t�����D�O���t���ХN���Y�����X�¤�`���¡C�¤�`��P�T���O���t�a���̭��n�a�ڡA��Q�묰������t�a����j��W�C�j�æ~�����m���t�W�ؿ��n�ĤT�Q�G���N���X�T���G�����ê��L�δ¤�`�S�������ೣ��֦������L�a�ڪ��a��C�i�����t�a�ﱾ�t���Բ��N�q�O�D�`�������C
�Q�|��¡A�q�������}������L���s�t�A�ש��F�軷���ް����C�ް����S�W曵�����A�]�N�O��Ӫ��تQ���C�ް����O�軷���������A�P���t���P�˪��x�ƭ��n�ʡC���L�A�ѩ�ް����U�m(�ް����m)�O�軷�����g�٭��ߡB���x���a�A�S�{���ئW��A�O�F���D�����T�B�I�A�G�����h���Q�@�}�B�j�W���ܤ����a�C�]���A���ɪ����D�]�O�q���������X�������s(�]������k�����s�s��)�C�b���夺�@���A�������X���O�A�������a�z���ҡC�����j�P�����_�B���B�F�B��|�����A�_�����ݤs�S�a�a�A��q�B�B��W�_���F���j�@�ΡC�]���A�Ѧ�ܪF�����O�ߤ@����q�u�A�q���b�U�ӭ��I�ϯì��m���ڦu�ơA�ت��N�O�n�T�O��⤺�������t�C�i�O�A�i�J�T�e��A�N���t�@�Ӱ��D�X�{�K
�X����Q����A�L�J�T�e�I�X
��F�軷�����ް�����A�q���b�ݤQ����[��v�L�i�J�T�e�N�Ы��A�Q����L�ܤT�e�������T�C���ɤT�e���O���t�s��a�A�����t�q���u�b�F�T�e����������c�T�A�Ӥ��t����T�e�������٦s�b���~�C�b�h���P´�ЫH�q��ԫ�A�q���~��´�Юa�b�T�e���դO���^���i�A��´�Юa�b��T�e�̵M���v�T�O�A�ר�O��T�e�����ڤ�����D��´�Юa���A�T�e���M�����Oí�w�C���t�q�����ΪQ���@�ڤ]�N�O�n�ǥH�ⱱ���T�e�����ơC�������A�i�J��T�e��A�ѩt�B´�Ш�a���դO��b�T�e�B���i����Ҧa�a���ۥ���A���t�ժ��A�פw�q�V�L�ۻ�A�C�C�i�J�{�Ԫp�A�A���M�������P�C��F���T���ɡA�H�Q�����d�Τ��쪽�ˬ��������W���w��F�T�e���U�{(����)�A�]�N�O���i�B�T�e����ҫe�u�C����Q�C��A���q�����}��F���U�{�ɡA�Q���B���쵥�w��L�Ҥt�A�i�J���i�Ҥ��C�Q�K��A�]�N�O���U�����Ԫ��e�@��A���t�q�������]��L�Ҥt�A�i�J�F���i�A�öi�n���n�����(�a)���A�ӷ��ɪ����D�N�O��˦V���t���[�����ô��K�C�N���A���t�q���ΤG�U���d���T��j�x�ש�}�l����i�����K
�X����I´�ЫH�����Iֹ�Բ��I�X
���蘆�t�q�����T��j�x�@�B�@�B�V���i���i�A´�ЫH���S������ﵦ�H�ƹ�W�A�H���b�o�ɤw�}�i�F�w�蘆�t�ժ��Iֹ�Բ��C�@�p�e�z�A���t�q���o��s�f���~�B�ЦN���l�Τ᳡�F�����Ӧ����j���B����⫰(�m�H�����O�n)�C�j���λ���⫰���O���i�������a�a�A�P�M�w�����Z�������A�]��H���եj���X���˨��u�c�����j���¯١C�]���A�H�����ϥΤ϶��p���h�s�f���~�B�᳡�F�A����������¯٥����A���t��ϦӬ��r�N�����u��(���H)���Ϸ����ӤJ�m������F�A�̡A������O���a�Q�ӫت������A�m�H�����O�n�O���u��������A�n�{�¥��t(���t)�J���K�V�F���s�����s���A��S���`�СA�ѪF�ܥ_�笰�s�a�K�U���v�A�t�~�A�j�����]�O�@�y���[�c��`���A�������Y�ΤG���Y��Ӧ���(�m�j�����j��ø�ϡn)�C�]���A�H�H���ǷL���L�O�A�ڥ������H�ާL�ܨ��A�G�H���ק�b�ī�(�j���B���)�e�u�v�Iֹ�A�Χ@����B���_�ɵ��u���ΡA�P�ɤ]�O�n�o��@���������t�����L�O�C
�ۥøS�G�~(1559)�_�A�H���}�l�v���ӥIֹ�X���U�B���Ӧx�B���q�B�Y�ڤ��l�z�A�ΥH���O�������B�j���⫰�C�m�H�����O�n���ֹ���@�Φ��ԲӪ������G
�@�B ����(�����)�۹j�G�Q���A���j�μź٬����U�A�O�����sֹ�C
�u�ƪ̬������a�M����(�Ω��s)�B�s�f���ѥ�s��(�Φu���B����)�B�C�ӥȿ��Y����B�u��P�Q���B�v�Q���Φ�Q���ê��C
�G�B(�ۻ����)�F���j�ݵ����x�A�n�`�]�C���[���k�ê��H���B�˧̥��ʧU�˲�(�ΫH��)�u�Ƥ��C
�T�B �n�����q���p���A�v����ֹ�A�H梶�t�����ê�����(�Υ��~)�Ƥ��C
�|�B �¥��t���A�����_����B�j�����s���A�v���sֹ��ҡC�Y�ڤsֹ�Ѧ��[���j�Dz���(�Ωu��)�B�s���äE���q�˦u�ơB�A���ȿ��C
���B �z�sֹ�h��´�Хȿ��q�ӡB�����u�w�v�������u�H�v�C
�Ӯھڡm�勵�T�e���g�O�n�A��ԭz�Uֹ���u�ƧL�O�G
���Uֹ�T�ʥ|�Q�T�M�A���Ӧx�|�ʤ��Q�M�A���qֹ�G�ʤ��Q�M�B�Y��ֹ�@�ʤ��Q�M���l�zֹ���ʤG�Q�M�C���M�A�u�M�v�o�ӳ��O�ȱo��ê��A�]���@�M�����W�Z�̷|���a���ܤ��W���B�L�����A�G��O���Ӧxֹ�N�w���_�X�G�d���ʾl�H�A�[�W��lֹ�X�@�L�O�w�W�L�@�U�H�A�o�ä��X�z�A�G�����u�H�ơv�A�Ϊ̥u�O�L���a�������M�L�C
�b���A�٦��@�Ӻðݭn�ѨM�C���U�B���Ӧx�w�������A�ӤY�ڡB�l�z�h�w��j�����A�o�|ֹ��¾�d�A�����������qֹ���d���O����A�b�m���O�n�W�èS�����T�����C�v�a�p�M�Э��k�{�����q�O�Χ@�s���W�U��ֹ�A�]�N�O���ϳs�I�C���̫h�{���A���qֹ�O�w������C������F���D���T�e�B���i����t�a�a�A�Ӥ��qֹ����F���D���n�D�W�A�H���b����j�������l�A�]�����ѨӦ۪F���D�����t�x�i��i���a�H
�X����Q�K��A���t�x���p���I�X
���U�����ԫe�@���X����Q�K��A���t�B´�Ш�x�U���ﵦ�w�ơC�q���b�Q�K��i�n�����A�b����l���ѱN�i��xij(�m�³��»D��藁�n�B�m���U���X�O�n)�C����xij���e�èS���Q�O���A���̱��_�A�xij�����e�z����ѱN�A���T�w��´�Ъ��@�Ԧ�ʦw�Ƥγ��p�A�]�A���ܦV�j�����B�J�x³�����ȡC�t�@�譱�]�U�F�@�Թ����B�ۤ��t�X���վ�C���M�H����蘆�t�ݫ���I�Iֹ�Բ��A���q���]�P�˧@�X�Iֹ�Բ��C�m�H�����O�n�����X�u����x�v�cֹ�B�n�`�v�i�O�A���x���T���m�A�ܤ��������_�w�A�������{�b�W�j�Υ������Цx��}�A���w���o�Ӫ��A�Ϊ̦b�F���D��D����C�m�勵�T�e���g�O�n���O���A���x���u�N�O�u���s�Ƥ��u�ӦN�B�T�������U�q�N�B�����e�u�P��βL���p�|���F�ӵ��v�C�N���ӻ��A���t�x���զb���i�u�F���D�@�a�v���[�j�i�������ơA�ǥH�[���H���誺�]��ζi���C���O�A���t���٦��@�ӥ��ȥ��������A���N�O��j�����i��L³�ɵ��C
�X�Q�K��]�A�Q�����d�V�j�����B�J�L³�I�X
���@�����̱q���t�q�����p���i��ɡA�Q�����d�]�^�R�B�L³�ܤj�����C�j�����ѩ�Q�l�zֹ�ΤY��ֹ�]��Τ��_�F�ɵ��u�A�G���ݭn�x³�ɥR�C�P�ɡA�]�����k���A�o�O�]���q���N�i�n�j�����Өƥ��dzƪ��u�@�A�o�O��ܡA�e��A�͡C
���Q�����d�B�e�x³�J�j�����@�ơA�j�Ӫ���ѳ������P���ɶ��O���C�b�w�t�����ɥN�A�j�����B³�@�ƬO�x��q�|�a�d�ߥ\���ª��@摏�j�ơA�G�b�x��B�������s�b���ֲ����B���G���v�T�~��(1557)�B�øS���~��(1558)�B�øS�G�~��(1559)�ΥøS�T�~��(1560)�C�H�v�Ƽƶq�ӭp��A�øS�G�~�����T���F�j�h�ơC�䤤�H�w�t�x��O����ѡm�³��»D��藁�n�O���u�øS�G�~�K�q���R�Ϸ����U���v(��)�u�j�����C��]�����L³�ʥF�A�q����R��(���d)��e³�̤@���K�v�W��O�����O�u�øS�G�~�v���ơA���P�媺�����������u���ơA�ѰO�~�N�����P�A����k�ƪ��y�B�e���s���a���ûD�ѵ������v�T�~�|�뻡�A������w�D�ѡB�T�e���y�D�øS���~�F�Q���O�B�T�e�O�j���B�T�e�O�K�n�h���øS�T�~����A���U���ԨƤ��e���Ƥ]�C���~���H�Ϸ����ө�(�øS)���~�i�n�j�����A�G(�B³)������~�ᤧ�Ƥ]�K�v�A�ܩ���@���@�ǥv�a�A���{���øS�G�~���몺���k���X�z�A�u�øS�T�~���D�O����Q�K��A���ɥ��ȶ}�l�i���l�z�B�Y�ڤ��ɡA�b���ɤ~�V�Ĥ@�e�u�B�e�L³�A�Z�D�ƫe���L�dzƶܡH�Y�Ϧp���A����N�i����i�����t�x�A�Y�ϧL³�����A�]�ܤӥi��_�I�B³�K�v(�p�q�s���D�m���t�q���n)
����A�s���Q�����d���S���b�øS�T�~����B³���u�@�H���̻{���B³�@�ƤD�O�øS�T�~���ơA�]���W�z����L���~���èS����L���Ҥ���A�]�S���������d�������M�i�J���i�B³�A�欰��³�@�ƴN���u���i�O���X�z���C�ӥB�A�p�q�s�������k���K�a�����G�ת������A�H���u����J�I���i�v�D���j���ơC�i�O�A�Q�E�骺���U�����Ԩä��O�q���J�����j�ԡA�]���O����q���Q�w���A�P´�ЫH���M�Ԫ����X�A�G���A�@�몺�B³�dzƬO�z�ҷ��M���C�t�~�A�H���誺�O���m�H�����O�n�]���O���u�w�t�a�d(�Q�����d)�Ԥ����A�V�j�����B�J�L³�A�ðѥ[�Y�ڡD�l�z���K�v�G���A���̻{�P�øS�T�~�����T�X�z�C
����A���d�B³�@�ƪ��L�{�S�O�p��H�ھڡm�H�����O�n���O���A�露�d�B³�@�ƨèS�����骺�O�z�A�Ӥ@�Ǥ��t��μw�t�誺�O�����y�A�p�m�T�e���y�n�B�m�勵�T�e���g�O�n����B³���O���Φ��~�O�A�ä��ӥi�H�C�Ӯھڡm�����a�ǰO�n�O���u�øS�G�~�A���t�q��������{�j�����A�Ϸ����ӤJ�m���C´�ЫH���惡�b�Y�ڧ��v��ֹ�B�K�����K�P�~�G���v�{��(���d)�X�}�A�U�O�V(�j��)���B³�A���{��(´�Ф�)�����ӥ��ϧ�ê�]�C�����s�Ӳv�L�P���۾ԡA�v������Ĥ�A���ɭ����V���B�J�L³�A�q���̦��V�s�Ӥ�o���P���]�v�q�W�z���O���o���A�Q���զb�B³�~���A���P�b�Y�ڡD�l�zֹ��´�жլ۹J�A�õo�ͤp�ԡA���̲׳����\�B�J�L³�C���M�ԲӪ��g�L���ӲM���A���z���P���X�J���j�C
�b���A���̷Q�N���d�@�ƥ~�g�@�ǸɥR�C���@���֤H���H���A�w�t�a�d�b���t���]�@�H������A�D�����M�I�Τ�]���x���C�i�O�A�o���L�O����ɥN��u���g�a�d�v��W�@�ԦӨ��Q�~�����G�@�@�Ӱl���]�ѡA�P�ɥH�b���t�⤺���H��ɥN�A�Ϯa�d�i���H�ۭ@�Ԫ��ʮ�@�@�Ӹ����C�A�̡A�]���a�d�b���U�����ԫ�A�p���������t��u�W�ߪ����ߧ@�@���G�@�C�M�ӡA�o���O���ӥ��T�A�Ϊ̲������ƤF�u���g�a�d�v�C�b���t�q�������e�U�A�a�d�o�줵�t�a�x�v�ӭ�R�����Ш|�A�o�ä��O�@�ӤH�����o�쪺�ݹJ�A�άO���A��u�H��v�ӻ����T�O�u�L���v�C�t�~�A�b�a�d���A���ɡA�o���q�����W�u���v�@���a�d���W�r�u���H�v�B�u���d�v�C�b���ɡA�����q�����W���H���������H�B�T�����F���@�ŭ��ڡA�o�S�O���O�@���u�H��v���a�d�i�H�ɨ���H�A�̡A�q���]��ۤv���c�k���f��(�v�s��)�U���a�d�A�������A�a�d�w�������t�a���@�����C�o�@���S�@�����S�ūݹJ�A���̻{���A�q���q���H�H���ݮa�d�A�ϦӬO���i�a�d�����t�a���s�@�N�j�N�A�����Ө��A�q���N�O�n�H�a�d�@���T�e�Q���Ҫ��D�a�a��A�Ǵ��ɮa�d���a��A��ۤv�����T�e�@�ƥ����ơA�Ǧ��]�i�s���q�����F�v�ޥ���b�D�`�����C
�X����Q�E�����X�i��I�Y�ڡD�l�z�I�X
���\���j�����B�J�L³��A��q���Ӱf���A�i�U�ƭѳơA�W�իݵo�C�]���A�q���U�O�b�j�������Q�����d�i��U�@�������ȡA�N�O�����V�Y��ֹ�o�ʧ����C�Y��ֹ���j�������F�_��A���u�q���j�����j���p�D�A�u�N�O���[���j�Dz����Φ��[���u�����H�C�ھڡm�Z�w�s�~�����n�Ρm���U���X�O�n���O���A���d�v��Q�����@�@�d�H(�@���G�d���ʤH)��Q�E�龤���i��u���|�ʤH�u�ƪ��Y��ֹ�C����h��ۤv�@�����ĭx�A�`�u�N���[���������u����(�Y��)���M�h�|�ʡA�b���t���j�L��𤧡A�����a�����A�U��i�t���h�]�A�ڤ@�H�b���Ԧ����o�K�v(�m�Z�w�s�~�����n)�A�i���������蘆�t�x��������_�ɶq��ܡA�õL�H�ߡC�u�D�U�H�P�H�����x�X�y�C�i�O�A�P���u�N���A���ȿ��V�����D�i�n���X���A�{��Ţ���]�����קK���������G�A�Ϥ��P�Q���@�ԩΦ���}���i��C
�t�@�譱�A�]��Y��ֹ���Q�����d��x�դ����T�����X���L�t�d���������A�C�L�t�d�����_ŧ�H�Τ��d�����j���C�`���W�ѥۤt��V�u�a������A���L�ѧέ�Q���S�C���a�s�v��A�C�L�h�ѯਣ�Q�������k�ê����N�v��A�˪j���N�Ѱs�������Υۤt�ƥ�������C�N�b�Q������m�}�ɭԡA�Y��ֹ���j����M���}�A�������|���M�L�b���[�������ΪA���ȿ����v��A�V�Q���լ�ŧ�C�����Φ��A���d�V���x�U�O�u�p���L�ղz�����u�����A���o�X�Ӥ@�ԡA�i����N�����M�A�������@�Ԥ]�A�ڤ赴���i�]�Ӱh�Y�A�H�}�B���D�ԡA���عܨ������I�v(�m�勵�T�e���g�O�n)�������b�L�O�W���Үt���A���u�ħ����覹�ɤ��n�A�����ڭ���������A���D�ʤd���~����s�ܡH�v(�m����k�v���y�n)�i�����ɪ���Ԩƹ�W�B�ۡB�@�i�@�h���E�Ԫ��A�A���L�A�ѩ�l�צs�b�L�O�W���t���A�̲פY��ֹ�b���W�E�ɨ�Q�ɥ��k�����C���������[���������N�L�@�P�Ԧ��A���ھڡm�T�e���y�n���O���u���[��(����)��X�A�۪��B�ɨo�K�P�a�����Ұk���Գ��K�v�G���[�������]���i���X�Գ��A�P�H���X�y�A���걡�w���Ҥ���C���M���\�ܨ��F�Y�ڡA���Q���զb�T�Ԥ��]�l���G���C�m�T���O�n�B�m�Z�w�s�~�����n�O���A�Q���a�ڪ��D�n���F�����Q�����ˡB�Q�������B���O�����θc���h���Ԧ��A�i�����[���誺�����ä��O�ܮz���A��Q����ӻ��A���T�O����N�~���j�����C
�Y��ֹ�������������[�Ǩ�q�����}�A�o���ӪA���q���ߧY�U�O�Q�����d��j�����𮧡A��ѭ�u�N�Ϸ����ӻ�L�X�}�C�m�H�����O�n�]���ۭY���O���u�w�t�a�d(�Q�����d)�Ԥ����A�V�j�����B�J�L³�A�ðѥ[�Y�ڡD�l�z�A�̦��j�\�Ҥ]�A�H���@��A�~�}�j���C�v�ѩ��@����ɥN��a�d�b�j�����B³�ΤY�ڧԪ��\�Ҥj�[�ŶǡA���K���Ҹرi�Q���յ��H�����i�A�H���a�d�J�m�j�����O�u����v�B�u���ҡv�C���@�p�W�z�A�ѩ�Q���զb�Y�ڤ@�ХX�{�N�~���j�l���A�[�W�s�s�ʭ��A�w���O�@��i����W�}���L���A�G���o���b�j�����ȧ@�𮧡C���L�A�o�]�i�ݨ�q�����@�Ԧw�ƫD�`�X�z�A�H�Q���@���i��B�e�B�������u�@�A��j��������ê�M����A�A�ﬣ�b�j�����u�ƪ��Ϸ����ӥN���X�}�A�L�O�Φ�ʤO�èS������v�T�A�Ϧӥi�@���O�������O��í�w�A�o���O�ҩ��q���b���i�Ԥ�����ߪ��p���ܡH
�N�b�Q�����d�j��Y��ֹ���P�ɡA���t�q���]�U�O�a���i�N�¤�`���§����t�@�Ӱw��j�������I���X�l�zֹ�C�u�Y�ګ�(ֹ)�������P��A���t����W���N�¤�`�Ƥ��u����(���¤��~�O)�j���l�z���ī��A�ó����C�v(�m�Z�w�s�~�����n)�A�������A���t��w���ӥI����������������P�ɶi��A�H�[�֥ؼЪ��F���t�סC���¤�`�ժ��L�O�O���A�ä��O�C�m�s�����T�e�O�n�N�����u���d�M�v�A���L�A�u�M�v�o�ӭx�Ƴ��D�`�e�j�A���d�M�����G�U���d��T�U�H���k�A�o�ä��X�z�A�G�����u���d�M�L�v�Ρu���d�H�v���~�O��������C�Ӭۤ�Q�����d�����Y�ڡA�¤�`�誺�Ԫp�O���D�`�֤�²�u�A�䤤���������Ԫ����m�勵�T�e���g�O�n�u�Q�E��A�q�������W�¤�`�Ƥ��u����(���¤��~�O)�B����H�@�u���������l�z�����C���D�����u(�w�v)�Ψ�������u(�H�v)�B´�Хȿ���(�q��)���V�|��U�O�A�}�B�K���p�B����g�X�A�dzƨ��ԡA�M�ӧ�����j�x�s�Ⱓ���J���A�פ�����~�A�u�N�����u(�w�v)�H�U���L�h�b�Q���A�l�Ҧ۫��X�k�X�A�U�۴����K�v�W�z���O���ϬM�X�l�z���u�N�Ӽ˱Ĩ��u�աA�P�Y�ڪ��X�������Ҥ��P�A�����O�u���άO�X���A�⫰���b�E�ԫᤣ�[�����C���L�A�q��ֹ���Ԫ��i�ݱo�X�A´�Ф誺�u�Ƥj�N�èS���]���t�j�x���ӦӥߧY�뭰�A�Ϧӷ��O�u�ƨ�̫�@��A�o���O��ϬM´�ЫH�����y�O���K
�X����Q�K��]�A���R���M�����X
�b���t��n���o�ʭx�Ʀ�ʪ��ɭԡA�b�M������´�ЫH���S������ﵦ�H��@�H�j���{��´�Ф�蘆�t�誺ŧ�ӳ��B���H�L�`�Ϊ̥D�i�뭰�������ﵦ�C�ھڡm�`���O�n���O�z�u´�ФW�`���H�����b�M�����A�D�i���V����X�ʡA�E�P���t�@�Ԥ]�I�L����u(�q�s)���סy�ĥ|�U�A�ڤ�T�d�A�b���ԨèS���ӧQ���Ʊ�A�G���b�M������Ţ�]�I�z�V���Ϥ��A�M���������]�I�K�v�N�m�`���O�n���O�z�A�ݨӤQ�K����]�����s�b�蘆�t���ﵦ�Q�סA�ӪL�q�s���j�ګh�O��Ţ�����W�C���L�A�ھڤӥФ��@���m�H�����O�n�O���A�èS���W�z���ơu�e���K�y�@�B����Q�C��A���t�q�����着�}�A�ݤ�V�j�����B�J�L³�C�Q�E��¡A���t�դ����x�X�ʡA�N���麦���ɧ�ֹ�A���p�w�D�]�C�z�Q�K����[���j�ǡB´�Хȿ��N�������i�V���i���C�M�ӷ��]�A�H�����èS���S�O���x�Ʀ�ʡA�P�a�ڦU�����͡A�β`�]���ɡA�R�U�a�ڴ��h�k�v�C�U�a�ڼJ���D�y�p�쩯�B�����A���z����]�ܳ��t�o�z��U�����h�K�v�i���u�P�a�ڦU�����͡v�@�y�A��ܷ����èS���xij����^�Φw�ơA�u�O���͡A��ӭxij�H�v�a�å�������X�A�W�z�L�q�s���o���A�ά���@�p���a�p�p�j�u�g���@�C�Y�ϦҼ{Ţ�����]�O���X�z�A�Ĥ@�A�p�Uֹ���ҳ��A�h�M�����p�P���r�A�L�Ω��ܥ~�ġC�P�ɡA�p�GŢ���A�N���ܹ�~ֹ�\�X��A�סA�]��������������C
�W�z���`����ܦ��[���j�ǵ��P�H���@���O���p���A�P�ɦ��[���j�Ǥ]�⤵�t�x���@�|�@�ʧi���H���F�ѡA������ܫH���ëD�Ĩ��������A�סA�U�a�ڪ������]��ܥX�H���P�a�ڤ����èS���Ӷq�ﵦ���ߺD�A�G���A�U�a�ڤ~�b���u���ɡA�H�J������k�V�H�����D�C�o�����P�C�q�|�DZФh��ե촵�ҵ۪��m�饻�v�n����H�����y�z���ѦӦX�u�L(�H��)�Ⱦ̤@�H�A�q��ť�a�ڤ������A�U�H�u��L���߬ȷq�Ӥw�K�v���M�U�a�ڹ�H���ä���i������U�A���o���N���H���P�a�ڤ����w�U�ۤ��ߡC�b�Q�E�馭�¡A�H���X�}��ԳӤ����A�S������a�ڦb�~���ϫq�έ˦V���t�q���A�o���O���´�ЫH�����j���ɪ̪��y�O�ܡH �]�p�P�T��ɥN���������ԡA ���M �F�d �b�Mij�e�j�a�N�����[�C �����F�Mij�H��A �j�a�N�µۤ@�ӥؼЧV�O�A �ש������\�C ���[��N�� �ܤ�Ԫ��A �ѽ��w�g�U�O����ܾԤF�A ���뭰�饻��僞�x���O�Q�������Q�ѻ\�a�A �u���H�ˤ߰ڡ^
�X����Q�E����A��ֹ�����I�H���X�}�I�X
�N�b�U�a�ڳ��^�U�۪��ΪɭԡA�H���w����̷s�������C�u�]�����ɡA�l�zֹ�B�Y��ֹ�Q���W�i�v(�m�H�����O�n)�¤�`�B�Q�������I���������b�t���h���ɶ��Ǩ�M�����A�@�V�O���I�q���H���ש��ʡC�u�o������污����A�H�����l�R�������R�A�ð�着�y�H�ͤ��Q�~�A�P�U�Ѥ����۸��A�{�p�ڤۡC�@�ױo�ͩA�Z�������̥G�H�z���G�y�j��(����)�z�B�y���㨬�I�z�@�Ӥ@�өR�O�U�F�C����㨬�A�T�m�����ơB�����i�W�A�H�����a�¤W���A�ĥX�����K�v�o�N�O����z���H�f�����`�A�������u�T�m�����ơv�N�O���T�ܮɥN�H�ӡA�j�N�X�}�ɥ��n���Φ��C�u�T�m�v�N�O��蚫�B�ӮߤΩ����A�b��媺�N��N�O�u�s�������Ӯߡv�A�]�N�O����P�u�ӧQ���k�v���A���@�j�N�X�}�ӧQ�C���F�m�����n�~�A�H���]���ۥX�@���W���u�����@�w�v�����m�p�q�C���סm�����n�Ρm�����@�w�n���p�q�A���H���了�`���D�n��Q�C�H���ۥX�o�Ǻq������]�A�@�p�v�a�G�����@�Τp���a�z�����һ��u�o�O��ۤv���@�Ӵ��ܡv�A�u�����@�w�v�N�O��ۤv���A���ä����ߡA�������A�O�@�Ӧۧڦw�����ۨ��ۻ��a�C
 ���D�D�����Ϥ��p�U�G ���D�D�����Ϥ��p�U�G

���H����W�X�}��A�u���Ǫ����u���@���M���p�m��������H�C�D�q���M�P���L�G�ʾl�H�ܤT���~�����СC������(���W�C�ɦܤE��)���ɡA��W���ڳ¯���(���Я��c)���e�A�����F�観����ϦV�W�����C�H�����o���l�z�B�Y�ڨ�ֹ�����]�C�v(�m�H�����O�n)�q�W�z���O���i���A�l�z�B�Y�ڨ�ֹ�b�C�ɦܤE�ɥ��k�Q�A�b�o�ɡA�H������u���X�ʤH���k�C��@���O�������H���b���Я��c�����o�{��j�_�ݡA�@�ӬO�b�H���b���Ъ������ݾl�L���ɡAť�o�������Z��o�X�n�T�A�H���b���ɻ��u����ť�o�Z��@�T�A���j�N���]�I���������Фj�������s���@�v�I�v�t�~�A�m�j�g�H���O�n�ҰO�A���H���dzƥX�}���ɡA�o�{�@����O�۪����V�F�迬���A���L�H�����s�X�K�H���ΦU�N�L���H�����j�N�A�Q�w�X�L���w�j�Q�C���~�A�٦��üֿ��⭱�ҦP���ѻ��y�Ǧb�����C���L�A�o�ǻ��k�èS�����ҡA�ӡm�H�����O�n���H���b���Я��c�ɪ����p�A�èS���@���b�y�A�o���T�����_�w�W�z���y�ǻ��k�O�_�s�b�A�γ\�u����@�Χ@�q�|�H���b�ԨƤ��ԳӪ��@�ӡu�w���v�Ӥw�C�t�~�A�����H���b���Я��c�W�^�Գӧi��@�ơA�]�S����誺�ҩ��A�b�{�ɪ����Я��c�A�]�S���d�U�o�ӡu�i��v�A���Ȥ]�O��@�p���a���Ч@�Ӥw�C
�H���b���Я��c�@�u�Ȱ��d��A�K�A�ץX�o�C�m�H�����O�n�O���u�q���ЦV���䤧�D��i�A�M�Ӯɭȼ麦���ɡA�G��q�������D��i�C���J���Uֹ�A�A�i���Ӧxֹ�A���ݦU�L�h�Ѷ��A��ư}�e�C�v���Ӧxֹ����T�ܵ�D���A�O�䤤�@�Ӱw���������I���C�ھګ�@���ҡA���Ӧx���C�W�A���U�i�����e�誺���qֹ�A���n��i�����l�z�B�Y�ڥ_�����s�C�A�O�Բ��W���n�������|��C�Ӧb���ɡA�w���l�z�B�Y�ڪ����t�աA�z���x���ﵽ�Ӧx��V�����u�A�������A�H���誺��ʦb���t�誺���u�U�A�ڥ�������_ŧ�i��C������ܡA�e��A���K
�X�������T�I�q�������ġI�X
�����H���V���Ӧx��V�i�x���ɡA�Y�Q�E�饿�ȫe��A���t�q���u���ɩ���U���s�P�|�U���d���L�����K�v�A�夤���u���U���s�v�P��H�@��F�Ѫ����U�����Ҥ��P�C�b��Ӫ��p���x�O�O���A�q���b�����a�Ϊ����U���𮧡A���m���O�n�����O�u���U���s�v�A�ھڥv�a�p�q�s�������_�A�u���U���s�v�Ӭ�����ɥN���iÿ�D�w�t�q���ҰO�z�u���U���s�v�A�P�ɥN�s�����m���U���ϡn�A���X�q�������}�������a�@�y�а������Q�|�̪��s�C�W�A�Ӥ��O��N�y�����A�Ӥl���ڮǪ����U�����C���ȥ��k�A�q�������l�z�B�Y�ڨ�ֹ�����������A�m�H�����O�n�ήe���ɪ��q���D�u�߱����n�A��}���������Ĥ����A�T���j�ۺq���]�K�v�q���i���q������i���i�P��D�`���N�C���O�A�q���b���U���s�𮧪��P�ɡA�u�V����(��_��)���ơv(�m�H�����O�n)�A���M�o�γ\���ӥФ��@�ӤH�����_�A���L�]����_�w�����s�b�ҳ����q�ǡC�]���A�o�Υi�ϬM�q����ä��p�@��һ��A��H������ʤ@�L�Ҫ��A�o�]�O��@�p���a��H���ƫ�ԳӪ��@�ӹw����ģ�A�����S�C�q������O�C
�����q���i�n�s���𮧮ɡA���t�e�x����_�訾�ƥi��X�{���ĭx�A�Ʀ]���U���s�P´�Ф�e�u�����qֹ�u���j���⤽���A�q���b�Ѱ��j�������M����A�w���Ϸ����ӵ��V�_���i�A�G�u�V����(��_��)���ơv�]���O�q�����}���e�x�V���q��V�i��A��֤��qֹ���X���i��A�P�ɤ]�o��Ӧx��V���X���i��C���L�A�q�������L�X���Բ��A�]�������L�b�Ƥp�ɫḮ�����U���s�I�U��u�K
�t�@�譱�A�i�J���Ӧx���[���H������@����H�������C�t�d�ݾ��ԩR�������G�H���B�d��u�����o���H���i�J���Ӧx��A�V�U�H���u�o�˪��ܡA�G�u�O���n�����|�I�v(�m�H�����O�n)�K�v��T�ʤH�V����������t�x���i�C�¦������k�{���o�O�H�������ʧ@��(�˧�)�A�ϸq����H���H���w�g�X�ʡA�ǥH�����v��_ŧ�����ϡC���L�A�o�ӻ��k�s�b�ȱo�O�d���a��A�Ʀ]�L�k�ҩ��H���P�����B�d����s�b�pô����H�A�ӥB�A�����G�H������ʤϦӹ�H���ӻ��A��O��M�l���C�H���H�L�L�x�լD�Ըq���A�����L�O�z��������N�y���A�o�˥O�H�����ԳӾ��|�j����֡A���I�����A�������H���ҦҼ{�C�����G�H�����H�P���t�e�x�b���qֹ����E�ԡA�̲״X�G���x�ШS�A�u���e�ЧQ�a���Q�ƤH�ȱo���K�C���t����o�����B�d��H�����šC�o�����Գ����q����ť�o�l�z�B�Y�ڨ�ֹ�������������ġC�m�H�����O�n�O���u�o���O�Ƥ��q���סG�y�ڤ��٨Ϥ��]�����礣���A�j���v�I�z�߱����ΡA�~������K�v�i���A�����G�H���Τd��u�����Ԧ���H���x�ӻ����T�O�����n���l���A����q���ӻ��A�o�O���i�Ԧ��\���@�j�e�B�C�M�ӡA�����G�H�X���@�ƫo�O�q����X�{�Y�{�פW���P�ӡA������Ӹq���x�����p���ä���K�C
 ���D�D�����Ϥ��p�U�G ���D�D�����Ϥ��p�U�G

 ���D�D�����Ϥ��p�U�G ���D�D�����Ϥ��p�U�G

�X��i�I�H���A�X�}�I�X
����d��u���Φ����F���Ԧ��������H���A������w�O�L�L�k�A�v�L�V���qֹ���i�C���ѩӦx�ܤ��q�����u���@���U�����ж��d�D�i�H�q�L�A�ӥB�e�褣�������Ĥ�X�{����H�A�G�@���a�ѳ���着�H������ů�A�չϿϤ�A�����ǡC�H���K�v�G�d�l�H�V���qֹ���ʡC���[��A�H���V���x�o���uť着�I�ĤH��Q�]�U�j��(��)�B�e�L³�A�S�V�Y�ڡB�l�z�i��A�U�N�h�w���h�֡C�Ӧ����ҷs��]�C�y�Y�ϬO��դ��x�A�b�j�x���e��������ߡA�B�ۦb�Ѥ]�z�A���j���^���Ҫ��]�C�Ĩӫh�ޤ��A�Ǿ��ϧ�A�N�����ˡB�l���C�����Τ����A��˭��šC���Ԥ��Ӫ̡A�O��ģ�@�ڤ��a�A�D�ܦ��\�W�y�ǫ�@�l�]�A�j�����H�P���@�ߤ]�I�v(�m�H�����O�n)
�q�W�z���O��o��@�ӭ��n����ơA�N�O�H��������P�ζաC�H���H���t�d�B³���Q���x����@�����������A���]�@�s�ꪺ��ʦӤj���֭ˡC���L�A�@�p�W�z�A�Q�����d�J����A�w���Ϸ����ӱ����A�G�L�O�èS���p�H���һ��u�w���h�֡v�C�ҩ��F�H�����x�Ʀ�ʩΫذ����P�����_�W�A���L�A�o�]���i��O�H���S�N���y���x�A�o�u�o�H���@�H�~���C�V���x���ܫ�A�H���v��e�ЧQ�a�B��Q�Q��(�s�U)�����x�@�G�d�h�H�V���U���s���i�o�K
�W�z���O���D�P�@��Ҫ����L�z���Ҥ��P�C�q�e�����k�O���H�����H�z�L�ҳ��o���q�����b�u���U�������v�𮧡A�òv�L�۵��Ӧx�V�F�_�j�許�j�A�b�s��¶�L�Ӥl���ڬ�ŧ�q���x�C�i�O�A�o�����@�X�@�ǽ�áC�Y�ϫH���u���o��ҳ����q���A�T�{�F�q�����Ҧb�A���b�j�許�j���U�A��_�x���q�����}�����ʬO�ȱo�h�ê��A�������A�H���������w�q���b���j�������d���B�A����|���h�j�H�P�ˡA�H���x�b���j���ɡA���e���ۦܤv�x�����n����O�ӶO�A�b�M�Ԥ��ɡA�����L�O�w���t�Z��´�Эx������o���ľԪ��ĪG�C�A�̡A�e���w�z�A�q�����H���誺��ʤw���@�w���ʹ�A�Ӹq�������}�]���b���U�����������C�G���A�u�����_ŧ���v���i��ʫD�`�C�A�ҿת��_�ݩγ\�u�s�b�p���������q�Ӥw�C
�_�w�u�����_ŧ���v���ܡA�H������ʴN�p�m�H�����O�n�һ��A�۵��Ӧx�V���q���i�A�A�V�F���D�����U���s��i�C�������A�H���x�Ĩ�������ŧ���ԳN�A�V���t�նi�x��V�����C����A������q�����H���誺��ʬݦ��@�L�Ҫ��H�v�a�Z���E�ۦb�m��X�Խסn���X�A�ѩ�簗�Х����v�⪺�Ԫ̾�����u�~�����t���J���`�A�O���t�q����H���誺��ʴx����w�C���T�A�ԫ�H���ץ\��ध�ɡA�߭��\�����O�V�q�������i�𪺪A���p���ӬK�w�A�]���O�Q���q�����Ū���Q�s�U�Ө��A�ӬO簗�Х����A�i���Z�����k���T����ھڡC�t�~�A�m�H�����O�n���t�@�Ӹ����C�u�b���U���s���K��A��M�Ѫũ��t�A�j���jŧ�A���B�ϩ����ʷn�j�a����B�ۦB��b�U着�C���ɭ��B�V���峠�F�j�A�u�~���ɯɭˤU�C�H�H�ҿצ��D���Щ������s�O�]�K�v�q�W��o���A�H���x�V���U���i�����ɡA��M���ɭ��B�V�F�jŧ�C�Ѧ����_�A���t�x���e�x�Φ]���B�����n�A��H���x����ʨS���@�X�ήɪ��^���F�A�̡A���U���@�a�Ҭ��_�w���C���a�a�A���t�է�����~�Ӫ��n���@�X��{�C
�X�R�B���d�q�I�q�����^�������I�X
�����H���x�����ܥ������V�q�����}���i���ɭԡA���t�q���惡�å����Ӥj�������C�ƹ�W�A���ɸq�������������Q�W�m�s�ԡC�m�Q���O�n�z���u���¤��X�ԡA�ӧQ�b��]�I�K���䤧�x����i�W�s�ԡA�U���j���|�M�Ӷ��v�b��ɥN�A�x���n�O�٦x�⪺�w���A�����Ԥ����R�ݡA�q�`���n�V�ԳӤ�W�m�u�����v�έx�Ϊ��@���O�@�C�Ѧ��i���A�q�����e�u���`�N�ש��㦳���P�ӡA���L�A�ۤU�A�������Ԫ��ӧQ�ϸq�����ҩ��P�ٳƤ]�O���`���ɡA�A�[�W���B�A�q�����}�Φ]���B�Ӧ��һ����C�m�T�e���y�n���]�O���D�u�q���ο����ɡA���b���B�J�����K�v�A���B�J�����ɡA�q�����n���b���\�A�b���T�V���ɡA�@�몺ĵ�٤ߤ]�|�H���Ӵ�C�C
�N�b�q���Ѷ���ĵ�ٴ�C�ɡA�Q�E�餤�Ȥ@�ɡA�H�������@�G�d�H�����B�����U�A��}�F���t�e�x�A�V�����@���������q�����}���i�C�u���[�ѪũA�H�������j���V�ѡA�j�n�W着�̫᪺�R�O�y�X���v�I�İڡI�z���x�V�q�����}��ġC�ظ@�o�ӱ��Ҫ����t���H�Y�ߨ�Y��A�}�B�j�B�K���ұ˱��ǡA������Ҵ��áC�q�������֤]��m�]�A���ɤD����(�U�Ȥ@�ɦܤT��)�C�v�@�p�m�H�����O�n�һ��A���t�չ�H���x���������T�P����M�����A�i���b���t���}�����èS���o���H���ժ���i�A�j�B�οҳ��������@�Φ]�Ӭ���C�q���i���R��A�q����]��H�����_ŧ�S���ƥ����dzơA�ӳQ�H�����������ؼСC���A�Y�ϫH����X�q�������}�A���n�q���d�H����X�q���@�H�[�H�Q���A�ä��O�e�����ơC�i�O�A�ѩ�q���S���dzơA���������֤Ϧ����e���Q�o�{�C�]���A�H���x�b��X�ؼФU�A�V�q�����}���i��h�IJv�C
�����q�����}�X�{�V�áA���ä��O�@IJ�Y�����C�u�b���V�ä����A�q���Q�T���M�]��@�P��h�C�v�Ѧ��i���q����b�H������ŧ���A�èS�������Y��A���ߪ�������O���M��������C�i�O�A���T���M�O�@��h���q���èS������Q�M�X�Գ��C�u��(�T���M)�ҳQ´�жծ����A�b�ƫת������U�A�u�l�U���Q�M�C�v�N�b�o�ɡA´�ЫH���]�[�J�ԨơA�����q���p���u�H�����]�U���A�V�J�X���������j�V�Ĭ����C�P�̬ҫi�Ԥ]�A�d��H��E�Ԧ]���i�}�C�v�b���᪺�ѳ��ԨƤ��A�H���w���ֿ˨��W�}���ġA�γ\�o��ϬM�H����ԳӪ�����a�I�@�몺���k�����q���Q�H����ŧ�U�A���[�K�Q���A�����q�����������@�����ζH�C�M�ӡA�m�H�����O�n�����q�����������O�z�u���Ԥ����j�B�p�m�����~���˩ξԦ��v�q�������H�����j�]��U�A�̵M�@�X�īi���̫�ϧܡA�M�ӡA�H��IJ��l�פ�����మ�[�C�u����A���p���ӭ����V�q�����A�q���ޥX�ؤM�A�٦V�A�������K�M�Ӥ��פ�Q�s����i�A�q�����פ]���Ƥ��ΡA��Q���j��릨�\�A�ñ��䭺�]�I�v�q���b�ľԤ��U�A�̲פ]���K�@���A�u�F���D�@�}���v���^�����t�q���A�q���R����U���s�����C
 ���D�D�����Ϥ��p�U�G ���D�D�����Ϥ��p�U�G

�A���p���Ӫ��j�����q��
�m����}�x�d�n�O���A���ɸq�����p�m���q�Х��ʦV�q����ij�k�V�j�����A���̲׳Q´�жհl�ΦӦ��`�C�L�q���O�_���N�ب�j�����A�ۨ���k���X´�Ф誺�����C�ܩ�q�����T�ꦺ�`�a�I�A�v�ѨèS�����T���O���C�b�l���q�����P�ɡA�Ԩƥ���V�l�Q�ԡA���b���U�����a�a�ɰl�v��ԡA�̲פ��t�ճQ����s�U���ж��A�ѩ�`������A���t�N�L�o�B�����A�Q´�Ф�@�@�Q���C�W�A�q�������a�������U���s�Y�ܥЦa�����C�b�l�Q�ԧi�@�q����A��Ӭ�ŧ�ԥ�i�����C�ƫe�Q�{���@���˪��B�j�z�a�����B���t��i�ͯ��ΧL���ԨơA�Ϧ������t�q���Ψ�˧L���������a�A�u�Գ��ܤƤ��w�v�@���G�u�����C
�b�s���ԨƧ�����A�j���|�ɥ��k�A�H���U�O�^�M�����i�歺������A���x�ͱۦ^�x�C�ھڡm�Z�w�s�~�����n���O���A���t��Ԧ��̡u�M�h���ʤK�Q�l�H�A���L�G�d���ʾl�H�v�@�T�d�H�Ԧ��A�������M�]�]�A���t�q�����H�F�C�m�Q���O�n�h���A�Ԧ��̥]�A�������s�Τ��쪽�����H�A�������A�ԨƤ����Ԧ����ä��O���q���N�h�A�ӬO���t�a�����a�쪺�a�ڲ��A�i�����Թ蘆�t�a�������`���C
�X�ӧQ���n�i�I�M�������ˡI�X
�ԨƧ�����A�٦��l�i���F�A�¤�`���¤Ω������H�����t�j�N���b�i��@�ԡC�t�~�A�m�H�����O�n�O���A���@�W�@�e�����N�h�s�зs�k�ê��b�o���q���Ԧ���A�����ĦV´�жզӾԦ��A�G�O���D�Q�����K���P�䭦�ҤG�ʤH�@�P�ĦV�Գ��A�Q�Q���C�ƫ�o���q�����T���¤�`���»�L�^�컷���A�ӻ�����N�������H�h�̵MŢ�����X�C�N�b���ɡA�^��M�������H���b�Q�E��ߦܤG�Q����i�歺�ˡA�@�o���ŤT�d�l�C�P�ɤ]�H��Q�U��E���k�ê��K�ˮ��q���P�B���v�����A����U���Ū������A���M�]�]�A�q���b���C���ˤ���A�H����\�v������P�q�������šA�b���{������U�A��^�@�e�C�M��A�H���U�O�b�M���ܼ��Ф������G�Q�m���n���P�f���q���v�_�u�q����v�A�öi��d���g�H�@�Ѿi�A�Ӹq�����R�M�u����r�ʤM�v�]�ܦ������H�����R�M�C
���q�����Ū����D�A�����s�b�����C�m�Z�w�s�~�����n�ҰO�A�u���U�b���{�����t�j�N�Ұk�A�M������D�����u��(���H)�l�װ��u�A�G�Q��H�Ӥ@�����ګH���աC���t�����Ѱe�ѫH���h�X�A�M�u�����֡C�H�����P�A�M�N�M���A���u�����D�A�����Q�Q�H���q�������šA���P�v�����@�P�ܻ�����K�����o�q�������šA��O�q����h�^�@�e�C�v�H���O���A�����������H�����V�H���ܦ^�q�����šA���̻{���m�Z�w�s�~�����n���O�������m�H�����O�n�O�z���ԲӤưO��A�ƹ�W�A�m�T�e���y�n�]���O�z���ơA�z���O�T����ơC�����ɥ��|���Ѩ������t�x�ӻ��A�������H���欰�i���L�Ȧ��A���ǡm�T�e���y�n���۪̤j�[�O���Фj�g�������H���u�Z�h��Ų�v�A�P�ɤ]�ϬM�H��������V���H����a�I
�t�~�A���M�d�b�j�������Q�����d�b�Q�E��ߦ���q���Ԧ��������A�����d�èS���]���ӥߧY�M�h�A�ý�áu�����_�Ǥ]�I�v(�m�Z�w�s�~�����n)�A����]�����H�����Ӫ��L���D���˨��U���U�A���d�l�h�A�g����^�i�T�e�K
�ۦ��A���i�������t��դO�]�@���M���A´�ЫH���̲��DZ��U������ŧ�ԡA�Q�����t�q���A�O���t��G�U���d�j�x�b�T�鶡��������i�Ҥ��A��M�w�ʪ����U�����Ԥ]�]�����W�y���K
[�����l�w�g�Q�@�̩�2010/12/29 �U�� 12:00:59�s��L]
|
 ��@�`�t���t�q���O���u�W���v�x�ѤU�j�v������A�ӡu�q���W���v���@���X�۹����߭�H�R(1794-1870 )�sġ���y���ׯu�ѤӻװO�z�A�ëD�v��C
��@�`�t���t�q���O���u�W���v�x�ѤU�j�v������A�ӡu�q���W���v���@���X�۹����߭�H�R(1794-1870 )�sġ���y���ׯu�ѤӻװO�z�A�ëD�v��C ���D�D�����Ϥ��p�U�G
���D�D�����Ϥ��p�U�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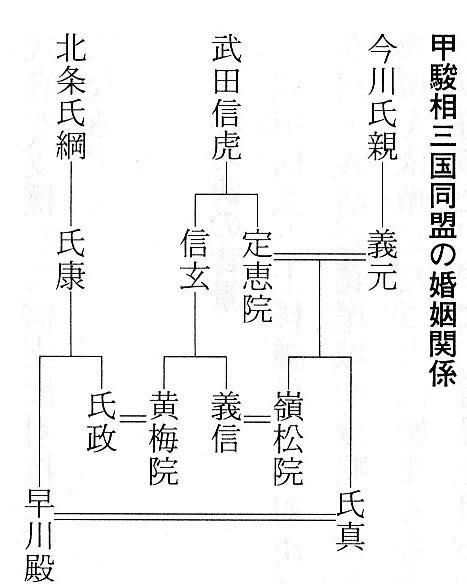
 ���D�D�����Ϥ��p�U�G
���D�D�����Ϥ��p�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