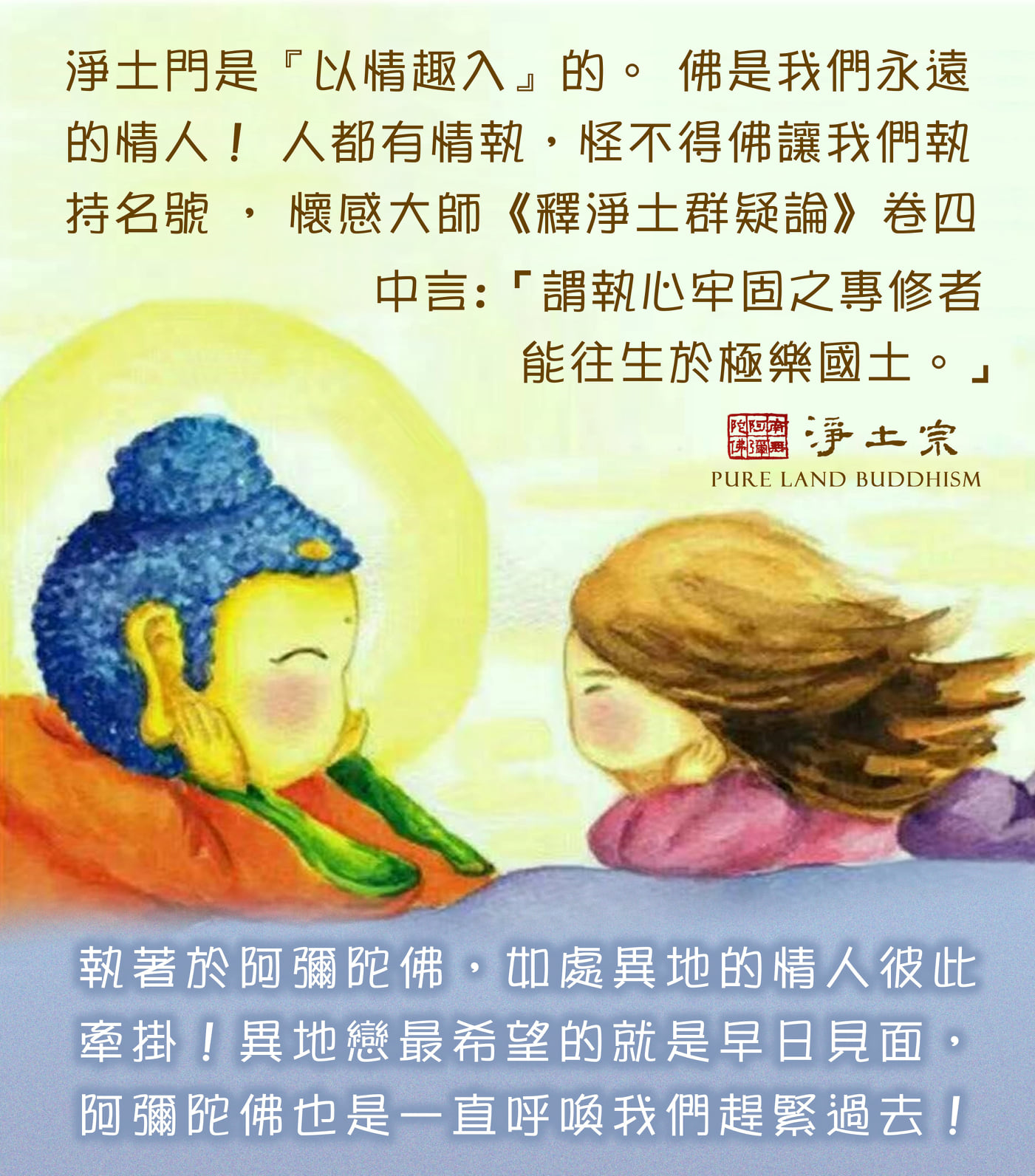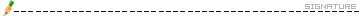此時,兩大名臣的權勢是天壤之別,張居正以帝王師的身份為首輔,權傾天下,萬歷皇帝幾乎是個擺設。而海瑞在官場卻是空前的寂寞,作為以耿直忠貞之名聞於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僅僅是個符號,他在政壇沒有朋友,更不可能有黨徒,自己的政治抱負沒有實現的平台。
張居正因為害怕海瑞的“峭直”,儘管面對輿論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為此後人很是詬病張居正,認為他心胸狹窄,嫉妒海瑞,拚命地打壓海瑞。
我以為張居正作為明代見識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壇上爐火純青的權術,海瑞望塵莫及,以海瑞這種個人道德高潔得讓人不敢親近的官場異類,在那個大染缸裡面,不可能威脅張居正的地位。張居正根本不用擔心海瑞這個政壇的“低能兒”在權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擔心的是,這個連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頭,一旦進了中樞,又是以道德的標準來對待政治,對張居正的政策橫挑鼻子豎挑眼,鬧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潔癖的人,很容易獲得輿論的支持,但讓他真正去辦大事,可能處處碰壁,從而一事無成。
張居正對海瑞的棄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場中要幹大事,僅僅憑道德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對這點張居正深有體會,他在官場上的發達已證明了要有大的作為,是不能保持個人品德的高潔,有時還得不擇手段,自污名節。
對張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評價不高。*臣嚴嵩當政時,“嵩亦器居正”。徐階代替嚴嵩為首輔後,同樣“傾心委居正”,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達到的。高拱秉權後,“兩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橫亙在他面前的石頭,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為首輔。於是他又私下裡結交司禮秉筆太監馮保。“神宗即位(萬歷帝),保以兩宮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為首輔。”
可見,張居正的政治品德實在不怎麼樣,怎樣對自己有利他就怎樣干,毫不在乎什麼名節。在個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麼樣。他好色縱欲,因為常服春藥,大冬天都滿腦袋冒熱氣,不能戴帽子。父親死了後,為了權柄不落入他手,和馮保共同策劃,促使皇帝下達了“奪情”的旨意,在父喪期間依然緊握手中大權。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喪後,必須丁憂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屬下的官員賄賂他的財物不計其數。
就這樣一個公德和私德一無是處的人,卻是奠定大明短暫中興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條鞭法”,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明史》載:“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評價他“通識時變,勇於任事”。
當然,因為二十一歲以前的萬歷皇帝一直生活在張居正的陰影下,對他有著父親般的畏懼,所以張居正死後萬歷皇帝終於爆發了,抄沒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權威,終於在死後引起了禍患。
張居正是個悲劇人物,無論是他生前的作為還是死後的子孫的遭遇。可是在那個時代,張居正不這樣做,他能掌握權柄,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嗎?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說明,個人的品德只有符號意義,在權力場中是蒼白、不堪一擊的。張居正死了,應該沒人擋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為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偷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這樣的官員,沒人喜歡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個閒官,誰在他手下當差誰倒霉。海瑞這樣的人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來,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倫理價值觀,在現實生活中和政治目標的實現總是矛盾的。儒家對士人有著道德的高標準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為道德完人,在政治場上基本上不會有什麼作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們真的像張居正那樣掌握了極大的權力,還能說“仁者愛人”,“吾養吾浩然之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