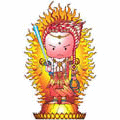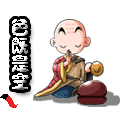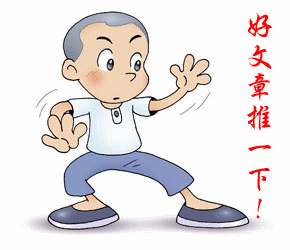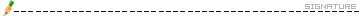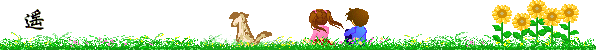大悲 觀 音 信 仰 在 中 國
郭祐孟
覺風季刊第30期(2000)
觀音菩薩在中國、西藏、日韓等地都是正信佛教與民間信仰中的大宗;以漢地而言,流傳最普遍的就是「大悲咒」。而圍繞在這一法門周圍的圖像也極為豐富,滋潤著古今佛門子弟和廣大社會群眾的心靈。本文就從佛教史及圖像學當中去參訪這一段大悲觀音信仰史,並對這尊永不褪色的法相致上最深的禮敬
一 大悲觀音信仰入華的情況
大悲觀音的根本經典為《大悲心陀羅尼經》(以下皆稱為《千手經》),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由智通翻譯的《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為最早的譯本,唐高宗永徽、顯慶年間(650-682)又有伽梵達摩所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兩本雖有繁簡之別,但關鍵語皆相同,都在禮敬「具大悲心而環顧眾生的聖者」,唐代敦煌的寫經就同時流通著「智通本」和「伽梵達摩本」。此時的密教比起六朝時期所傳佈的零星密法,已經逐步將傾向於世俗利益的祈禱咒願淨化,並加強佛法義理與瑜伽行法間的緊密聯繫,在高宗永徽年間由阿地瞿多所譯的《陀羅尼集經》中就完備了諸尊壇法,為百年以後入華的開元三大士提供了傳播純正密宗的背景條件。當然,《千手經》的魅力非凡,初傳時就帶動佛教界一陣雕造熱潮,留下莊嚴的法相。
開元三大士的德學席捲了八世紀的中國佛教界,他們所攜入的《千手經》梵本計有:金剛智翻譯的《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身咒本》、《金剛頂瑜伽青頸大悲王觀自在念誦儀軌》,不空所譯的《青頸觀自在菩薩心陀羅尼經》、《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悲心陀羅尼》,及《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自在王菩薩廣大圓滿無礙自在青頸大悲心陀羅尼》等等。至於大悲千手像的相關製作法則由善無畏譯出《千手觀音造次第儀軌》及不空的《攝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經計一法中出無量義南方滿願補陀落海會五部諸尊等弘誓力方位及威儀形色執持三摩耶標幟曼荼羅儀軌》,百餘年後又有蘇嚩羅譯出《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秘密法經》,可視為千手像法的廣衍。(圖一)不空曾依據七世紀「伽梵達摩本」增加悉檀梵字對翻,並在原咒章句下附加聖眾與八部鬼神名相。至此,大悲觀音的義理(藉「伽梵達摩本」明之)與行法(由念誦儀軌中見之)堪稱完備。今天流通的《千手經》便是以「伽梵達摩本」正文與不空附加的名相註為底本,再添入元、明之際補充的咒語解釋、「真言四十二手」和「大悲出相」所共同組成的。
二 大悲觀音信仰的弘傳實況
(一) 晚唐密宗的變遷
開元三大士所開創的密宗世界在唐武宗的會昌法難之後衰敗不堪,失去了宮廷的支持,正邪諸師相繼傳法,密宗在民間廣為流行,與漢地顯教及民間宗教相互影響,使得密宗的學理和實踐都蘊釀轉型。上乘者參禪宗法味,中乘者得教下精髓,下乘者則流於祈福攘災、神通炫世;知其味者能入圓滿之教,昧於外相者則冤枉功德,為世人詬病。晚唐密宗大德智慧輪宣導「以陀羅尼為佛法根本」的觀念,並泐碑流通,意圖提昇真言陀羅尼的重要性,釀成特殊陀羅尼信仰的新契機。這種將純正密宗的某一尊或某一經典加以各別重視、弘揚的方法,在宋、遼時代成為佛教界的新氣象。大悲咒也得到良好的發展與僧俗的重視,許多保留至今的石窟雕像與繙絹佛畫(圖二)都成為千手觀音信仰一路走來的回憶錄。
「別尊陀羅尼法」這種義理與瑜伽禪觀的整合,對於保存密宗精華及將密宗推向平民化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是密宗在中國社會得以流傳至今的主要關鍵。包括:準提法、千手觀音法、穢跡金剛法、尊勝佛母法等等,都是晚唐以後盛行於民間的重要漢密法門;他們的修持概念及方法都與東密、藏密有顯著差異,突顯了「顯密理事圓融」與「生起圓滿次第互攝」的特性,這或多或少得力於禪宗的養份。事實上,晚唐以後禪宗與淨土宗的強勢發展,也促成別尊陀羅尼與之結合的歷史條件。尤其準提法與華嚴學的組合、觀音法與天台學的相互倚重,都配合著淨土往生的終極意義,這兩脈殊勝的發展幾乎主導了近千年來的觀音信仰;以臺灣早期的佛教來說,除了它們二者之外,也找不到更精緻的成分了!而部分密宗行者因缺乏強有力的教義訓練及嚴謹的修學次第指導,也引生不少弊病,使功利主義傾向淹沒解脫證道的初心,在感應靈驗的境界中妄自尊大,以盲引盲;大悲觀音在民間也不免被曲解而俗化。
(二) 宋代法智大師編製《大悲懺本》
五代十國朝祚短暫,國不和睦,人心低靡,道德墮落,但是蜀國的藝術發達與吳越國、閩國的尊信佛教卻是這個黑暗時期的明燈。吳越忠懿王便是親事永明延壽與天台德韶的帝王,他感於佛學在唐武宗毀佛後的衰頹,遠從高麗求取散佚佛典,提供豐碩的資源,緇素得以咀嚼精研,也替中國近世佛教打定基礎。吳越佛教的成果就在降宋(978)後,拱手讓予趙氏王朝。
北宋初年是天台宗復興與蛻變的時代,知禮大師繼承天台宗在錢塘地區的傳統勢力,又得到皇帝與官僚們的賞識,通過山家山外之爭,鞏固也完善了他的天台學體系。他與慈雲遵氏仿傚智者大師《法華懺儀》的結構而編寫數種懺本,做為止觀實踐的依止;知禮本人更是親身躬行,講懺禮拜三十八年。行懺壇儀比教判弘經更容易被一般人接受,《大悲懺本》正是天台系懺本當中最為流行而且影響力最廣者。不過,《大悲懺本》「嚴飾道場」所規定的壇場本尊並非限於千手觀音像,只要是一般顯密觀音皆宜,甚至於安奉本師釋迦牟尼佛或其它菩薩亦可;或許當時江南的環境並不普遍流通多首多臂的觀音像,大悲咒的盛行並不表示非雕造千手像不可,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今天。
(三) 宋、元密宗的大悲觀音特色
宋太祖對佛教採取保護措施,並派遣勤行等一百餘人西行印度求法,搜集梵本,禮敬梵僧。此時的印度佛教已經以密宗為主,因此梵本也多是密典。太平興國五年(980),天息災、施護、法天等密宗大師自天竺來,於太平興國寺西設譯經院,譯出密典一百二十部,計二百餘卷,將前代未譯完整的《金剛頂經》再行補譯,使根本密典得以健全,其中又以天息災所譯的《大乘莊嚴寶王經》在民間產生普遍影響。此經主角--六字咒王「四臂觀音」(圖三),形像簡鍊而精緻,全身都是能引發行者菩提心與菩薩行的象徵性圖像;與《千手經》造像的繁複完整相對照,四臂觀音也可說是千手觀音法的簡約式樣。
流通在藏地的千手像(圖四)無論是「國王傳軌」、「蓮華傳軌」或伏藏所傳,都與甚深的瑜伽禪觀有密切關係,都是大悲觀音因應藏族瑜伽士所示現的禪定法相,其特徵圍繞著十一面、四臂與千手等相關因素,其咒音也與十一面觀音咒較接近,短咒則在六字大明咒尾加上氣音,可見《大乘莊嚴寶王經》與早期漢地流行一時的《十一面觀音經》都是藏傳千手觀音法的重要組成。
敦煌三窟是一個融合顯密大悲觀音信仰的元代窟,其中兩鋪千手觀音壁畫也是屬於藏密系統的表現,配合著五方佛與八菩薩結構,所蘊藏的深意與廣度都說明著別尊陀羅尼信仰的成熟與嚴謹。另一類「三大士像」,以觀音(形像或顯或密)為中尊,文殊(或雙手或多手)、普賢(或勢至或金剛手)為左右尊,分別代表修學佛法的正遍知見、真修實證與深廣行願,也配合氣、脈、明點的瑜伽功法;這是大悲觀音融攝華嚴學後的精緻簡化,應可歸屬於華嚴密教的範疇,也與藏傳的「三種姓尊」相通,代表五方佛的心證。「三大士像」廣為佛門喜愛,西藏以四臂觀音、黃文殊和金剛手配合開解行者心輪、頂輪、臍輪的纏結,明代部分佛寺以千手觀音、千缽文殊和普賢為殿堂主題,而臺灣萬華龍山寺及林口竹林山寺則分別以顯密觀音搭配青獅文殊和白象普賢。
(四) 蜀地大悲觀音信仰的獨特發展
四川的佛教發展遠自南北朝時代就已經興盛不衰,當中原毀佛戰亂時,又因地處邊陲,並未直接受害,具有豐富的佛教傳統。蜀地雕板印刷術向來發達,連中國第一部藏經「開寶藏」都是選在益州(即今四川成都)開雕刊行,晚唐所刻印的密宗陀羅尼經咒也是十分精巧的。
晚唐四川石窟的造像題材以淨土信仰及密宗本尊的比例較高,尤其是多臂觀音與觀經變相合為雙窟的情形最特殊,極具地區特色。當時有上師柳本尊傳播瑜伽教法,雖說是唐密的質變,但卻開創另一個造像高峰,菩薩像做為龕室主尊的比例升高。其中北山石窟出現了「數珠手觀音」、「日月觀音」、「寶缽觀音」、「柳葉觀音」、「如意觀音」等等,(圖五)很明顯是《千手經》大悲四十手的各別變現,可視為將密宗千手像簡化與漢化的代表作,這風氣或許正是啟發後代人創繪「大悲出相」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南宋淳熙六年至淳祐年間(1179-1249),又有趙智鳳瑜伽士在當地教化,大足寶頂山摩崖也雕造一尊大悲千手觀音像,靈感事蹟頻傳。此一前一後,可說是蜀地大悲信仰圖像的精彩之作。明、清雖然續有雕作,但式樣已經改變,呈現藏傳千手像因素的影響,顯然有著地緣聯繫,也與元代密宗的大量傳播有著時間上的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