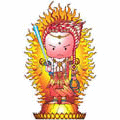他把自縊也看作一種做人的方式,成為知識分子的標本。
今年五月間,我在網上讀到《中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談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自殺的事: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在紅衛兵兩天三夜不間斷的抄家和凌辱後,時年五十八歲的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於上海江蘇路的家中雙雙自縊。為防踢倒凳子的聲音吵醒鄰居,他們事先在地上鋪了一床棉被。
凳子倒下雖沒有聲音,但「從無聲處聽驚雷」,我被這段文字震得肝膽俱痛,久久回不過神來。
鋪上被子的用意不外二者,一是怕驚醒鄰居會來營救,一是純粹怕吵醒他們的睡眠。如屬前者,是為己,出於私心;如屬後者,是為人,出於「不為他人造成不便」的體諒心,是文明人最應有的修為。傅雷當時的用意是什麼,我希望找到答案。
三十年來,外界一直傳說傅氏夫婦是服毒自盡的。此說原出自傅家保母周菊娣之口,大家都認為可靠。但上海作家葉永烈經過實地訪查,於去年撰成《傅雷畫傳》一書,明確公布他們是上吊。葉永烈找到的證據包括:上海市公安部門所存傅雷夫婦死亡的原始檔案。訪問第一個到現場的管區警員左安民。訪問驗屍的法醫蔣培祖。至此,傅氏夫婦是自縊已無可疑。
保母周菊娣當時嚇得不敢進屋,等傅雷遺體被放下,她進屋看到他臉上泛紫色,以為是服毒。傅雷愛種花,家裡放了一些殺蟲的DDT。
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在國外,傅敏在北京,他留一封遺書給同在上海的妻兄朱人秀,委任後事,都是細瑣的「財務問題」,包括一、代付九月分房租五五•二九元。二、沈仲章託代修手錶一隻,請交還。三、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四、姑母傅儀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三百七十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五、現鈔五三•三○元,作為我們的火葬費。
走得乾乾淨淨,不希望負欠任何人,拖累任何人,事事為別人著想,連火葬費都自行打點好。這樣的人,上吊時不願踢倒凳子吵醒鄰居,還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警員左安民告訴葉永烈:「當時,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戶中有兩百多戶被抄家。」又說:「那時候,自殺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大家自顧不暇,誰都無力顧到別人,是則傅雷在凳子下面放棉被,只是不想驚擾鄰居的清夢如是而已。
一個文明人到死都不忘文明的規範。對那些規範「從一而終」,才算真正有教養。
一九七九年傅雷「平反」,一九八一年《傅雷家書》在大陸出版,迄今已賣了一百五十萬冊以上。他對兒子諄諄教誨的,不僅在讀書、學藝,更在做人。藉著這些,傅雷自己也成了知識分子的標本。
一個文明開化的人,自然不會亂丟垃圾,不會橫闖直衝的開車,不會賣假貨害人,更不會利用職權貪贓賣爵。
教育和文明本應是正相關。但今天在台灣廣受街談巷議和千夫所指的人,哪一個不是出身有名的大學?
那就把傅雷自殺時凳下墊棉被的故事列入教科書吧!搶救國文的同時也搶救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