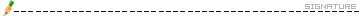每聽到釣客落海未能獲救的消息,我總會淒然的想著,難道釣客都只顧著眼前的浮標及眼前水面下的獵物,對善變的潮流及天候都不在意嗎?
許多人站在離岸的礁岩、斜滑的消波塊上,沒有穿釘鞋與救生衣的甩竿,將餌拋向遠遠的海域,而站立的地方又沒有可供攀附的固定物,稍有不慎就可能整個人被湧浪捲入海中,或摔到礁石、消波塊縫隙裡。
三十多年前我還懵懂時,基隆大沙灣內綿延著數百公尺的金色沙灘,靠中間部分,填築一道六、七十公尺長,直達深海的石塊群,它們未經排列的隨意置放著,倒也成了現成的人工魚礁。
一個初夏的午後,我右手握著釣竿,左手提著由奶粉罐做成的提桶,一步一跨的到了離岸最遠的石塊上,由於日光的照射及雨水的沖刷,那裡的藻類未能附著,顯得有光澤又不濕滑,成了許多人喜歡的垂釣位置。當時我一人,就在岩石下方垂釣,那兒水深將近五公尺。
我站在數尺見方、乾淨又微圓弧形的岩石上,魚群索餌的次數奇高。當我沉浸在豐收的喜悅時,一艘負責接駁商船人員的交通船,從岩石前方不遠的海域駛過,船身激起數道湧浪,撲捲而來。
我釣獲的滿滿一桶臭肚仔,因此被打翻在岩石夾縫中。
我不甘心四散開來的魚即將流失,本能地伸手撈起數條,才驚覺已是滿潮時刻。數十公尺長,直伸入海而突於水面的礁岩,現在除了我站立的石塊,就只剩下露出尖角的數塊石頭。
這一驚非同小可,我竟失去對漲潮風險的評估。由於當時年紀小,在慌亂中更見慌亂的我,赤足踩向一處長滿滑溜水草的石塊上,一下子整個人側傾水中,左大腿硬是狠狠地卡在岩縫中。
起先我不以為意,還以雙手支撐著上身,強行抽出大腿,沒想到非但無法從岩縫中脫身,還因久撐無力,整個身體掉進海中。
我在水裡死命亂踢,瘋狂揮舉雙手,猛拍著海水,只想不讓身體下沉。當時遠遠的岸邊有戲水人群、有準備漁具要出海的漁民,就是沒人注意到我。
幸好在湧浪過後,海面恢復了原來的平靜,我在陣陣喘息及連喝數口海水後,終於踏上原先站立的石塊。
爬回原先的釣點,才發現大腿內側已被石塊尖端劃破了一道兩寸餘長的大傷口,正湧著濃濃鮮血,在陽光照射下更顯得鮮紫的紅,而且迅速凝結成帶狀布於大腿上。
當時不知所措的我著急著,卻見一個熟識的伯伯,划著舢舨接近困頓心焦的我,將我接回岸邊。
當年醫藥貧乏,為了那兩寸多長、半寸寬的傷口,我僅在藥房買了抗生素和消毒藥水,在沒有縫合的情況下,讓它慢慢痊癒,卻留下既長又寬的疤痕。這個疤痕,在往後的日子裡,成了不時提醒我勿到危險海域垂釣的警告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