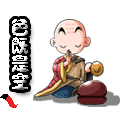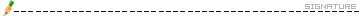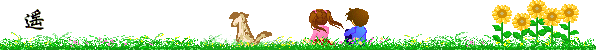◎石忠耀、宋玲玲
這個冬天南方很冷,陰霾密佈,薄霧籠罩,淅淅瀝瀝的小雨一直下個不停。
在南粵這個數十年難遇的寒冷冬天裡,何澤霖大德悄無聲息地走了。他走得很突然,也很坦然。帶著對西方極樂世界的無限嚮往,帶著眾多善信男女的尊崇與感激,帶著親朋好友的諄諄囑托,在綿綿不絕的佛號聲中安祥地走了。
我們是在驅車前往廣州的路上得知這一噩耗的。電話是從香港六合園打來,伴隨著風聲雨聲和悠揚綿長的念佛聲。當時車內的一位法師和幾個學友聞此消息,有的悲戚不已,有的唏噓感慨,有的長時間靜默不語。而我們怎麼也不相信這是事實,感覺他離去的過程太快太突然!
因為就在一個月以前,得知他生病的消息,我急忙趕到香港去看望他,沒想到他並不在醫院裡,由於擔心我找不到去他家的路(事無巨細,他總是為別人想得很周合)他還親自跑到元朗來接我,並精神抖擻地領我到他前年剛剛搬去、位於新界名為「六合園」的山村老宅裡,參觀他和夫人幾個月來在屋前屋後種的那些蔬菜瓜果。一路談笑風生,精神鑼鑠,我關心他的身體健康,他祇是輕描淡寫地說了聲「沒有事的」,反過來十分關心地詢問我所拍攝的電視連續劇《百年虛雲》的進展情況。我們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他的言談舉止全然沒有一絲病態。我離開時他仍像以往一樣,忘不了送我一本經書。一位慈祥健康,樂觀豁達的老人,相隔不過一月有餘,怎麼會說離開就離開了呢?
說人生苦短也好,說生命無常也罷,總之何澤霖大德真真切切地在這個冬天離開了那些深愛他的人們,一路佛歌,乘鶴西去。想起那一次在六合園,我曾經問他:「您住到這深山老宅裡來,樟木頭那邊印贈經書怎麼辦?」他說:「我該退休了!護持佛法自有後來人。」這也許就是老人對我們最後的告別。
澤公是二○○四年一月十六日上午七點十五分往生的,他離去的過程平靜而又富於傳奇。他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在自己預知的時間裡離開人間的。
一月十日,凌晨三點,臥病在床的澤公突然警醒,急忙喚夫人和晚年一直照顧老人的義女春艷到床前吩咐道:「我的神識剛才出去了,我見到了阿彌陀佛。」春艷「撲通」一下跪倒在地:「恭喜爸爸!」澤公繼續說道:「請打電話通知覺仁師、親證師、法光師,到時候為我做三時系念,念佛一周」。說完他又吩咐拿來紙和筆,親筆寫下:「從今起,早7:30到7:30分為我助念,限20人,每天準備食物,此會通知,不是我的意思。」(乃另有聲音告知)。
家裡人開始不明白他為甚麼要求準備二十人的飯食,由於澤公晚年居住的六合園地處偏僻,遠離市區,購物及餐飲均不方便。奇妙的是,那天清晨,聞知澤公臥病在床的香港、新加坡信眾相約到六合園看望澤公並為其助念,他們恰好在七點半以前陸續到達,恰好來了二十人!
眾人驚訝澤公預知時至,更加敬佩大德的修為及證悟,不敢懈怠,連忙輪流助念,晝夜不停的佛號聲在六合園的上空整整彌漫了一周。自澤公留下遺書恰好一周以後。一月十六日上午七時十五分,享年七十九歲的澤公在他六合園的家中安詳離去,從此了生脫死,往生蓮池。
國學大師南懷謹先生聞訊親擬訃文文告,昭示海內外。眾多寺院舉行追薦法會。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副會長永惺長老率香港佛教聯合會同仁,中國佛協咨議委員會副主席佛源長老率雲門寺四眾弟子,淨空老法師率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同仁,香港覺仁長老,願炯法師及眾多僧俗大眾送來了挽聯、花圈。人們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對這位終其一生,播種佛法慧命的大德表示了由衷的贊嘆和懷念。
在最後幾天恭送澤公遠去的日子裡,在一次又一次為澤公舉行的蒙山施食,三時系念等法會中。我們親眼目睹了眾多海內外高僧大德,成百上千的善信男女對澤公的深情厚誼。震撼之餘、我又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在我們的記憶中,澤公像一位慈父:永遠和言悅色,永遠平等待人。他那種愛到深處才自然流露出來的眼神、對於任何一位認識他或是不認識他的人都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因此,我們總能見到不少人親近他,感激他。我們還知道他從來不知疲倦,從來粗茶淡飯,從來祇為別人著想。但除此之外、他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蹟,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這樣一位平凡普通的老人,何以讓如此眾多的僧俗大眾敬仰側目?
我們帶者這種疑惑深入探究。對澤公了解愈多,我們便愈發汗顏!祇有這時候我們才開始體會「平常心是道」的含義;才能理解南懷謹先生何以在挽聯中如此評價澤公:畢世護法無雙士、生往蓮池又一尊。
澤公是我們認識的最為平凡,最為默默無聞但又無比崇高的一位老人;是我們知道的最為虔誠、最無私心、而又最不普通的一位佛教善知識!
澤公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出生於澳門,母親旱逝,他由奶奶一手撫養,由於自幼在教會學校讀書的緣故,澤公早年曾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徙。一九五二年他移居香港,為了維持生計,他捨棄了教師這一職業,和妻子林茜英一起,打小工,織毛衣,含辛茹苦,日積月累,漸漸發展到自己開辦了工廠。年輕時的艱難磨礪,造就了他惜福、樂善好施的本性。
由於經常去大嶼山看望已削髮為尼的姑姑的緣故,澤公自一九五四年閱始接觸佛教,從此便難以割捨,他不僅很快皈依佛門,而且發願將此身心奉獻給佛陀。
一九七九年,澤公利用他們夫婦胼手胝足,歷經十幾年奮鬥,省吃儉用才得以購置位於北角大廈的第一套房子,自行創辦了香港佛教圖書館,免費向佛教徒借閱、贈送圖書。後來他又將圖書館連同這套物業一並贈送給佛教界,成為佛教的公共財產。二十多年過去了,圖書館運轉依舊,至今仍是香港信眾修學佛法的重要活動場所。
八十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機會,澤公到湛江旅游,見到一位年邁的出家人在水塘邊挑水,澤公上前頂禮法帥,並問有甚麼可以幫到他的。出家人甚麼話也不敢說,挑著水徑直往茅棚走。第一次接觸大陸出家人的澤公,不明箇中緣由,跟隨出家人來到茅棚裡,發現這間茅棚破爛不堪,空徙四壁,甚至連一尊佛像都沒有。澤公將隨身帶來的幾本經書送給出家人,出家人如獲至實,老淚縱橫!原來經過文革之後,大陸佛教破壞殆盡,佛像經書蕩然無存。如今雖然撥亂反正,恢復落實宗教自由政策,但佛經典籍的乏饋一時難以解決。了解到這些情況之後,澤公將位於東莞樟木頭的工廠的事務全部交給夫人管理,投人全部身心在樟木頭設立辦事處,向大陸各寺院印贈經書。
他這一做就是近三十年。
他每天往返於香港和東莞樟木頭,用其瘦弱的身體,背負沉重的經書!從香港佛教圖書館搬上廣九列車、在深圳羅湖下車後跟隨擁擠不堪的人群過關,出關後又轉火車到樟木頭,再坐汽車到辦事處……每一個來回都異常艱難,但澤公幾十年如一日、像螞蟻搬家一樣,不知疲倦地來回奔走。等書運抵樟木頭後,他又和工作人員一起,小心翼翼地將一本本書包裝好,附上他親筆寫的信函分發到全國各地急需的寺院,隨著時間的推移,來信求書求物的人越來越多,小到一本《禪門日誦》大到洋洋數百本一套的《大藏經》。澤公背負的擔子越來越重,但他堅持每信必復,有求必應、在工作人員的印象中他從未拒絕過任何人的請求。就這樣背書、印書、送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
沒有人做過統計,這二十幾年來,澤公到底贈送過多少本佛經典籍!人們祇知道,有一年,他僅念佛機就贈送了一百多萬只!也沒有人計算澤公印贈經書到底花費了多少資金,身邊的工作人員祇知道每天僅郵寄費就要花掉兩、三百元。每天兩、三百元乘以二十年、已經是一個龐大的數字,更何況印刷、運輸這些更為不菲的開銷!
改革開放,恢復落實宗教自由政策二十多年以後的今天,對於許多金碧輝煌的大陸寺院而言,裝禎精美的各類佛經典籍俯拾即是,已不足為奇,但時光倒退到二十年以前,澤公送出的每一本書就如雪中送炭一樣珍貴。許多人因澤公的一本書而生起正念;許多寺院因澤公的一套書而恢復寺院秩序!從剛剛出家的小沙彌到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從初入佛門的居士到享譽海內外的趙樸初大德,成千上萬的人從澤公贈送的經書中獲益。
稍有年歲的出家人大多知道何澤霖這個名字,但多半祇聞其名,未見其人。
澤公沒有絲毫名利的觀念,他將自己全部的財產乃至身心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佛教事業!
澤公算是個有錢的人。乘改革開放的東風,澤公和夫人在樟木頭的針織廠曾經財源滾滾,鼎盛時僱用員工一千多人,二十多年來少說也有數千萬盈利。
但接觸過澤公的人覺得他又像個沒有錢的人。他一家生活始終異常節儉:出門坐公交車,吃飯是素食,一件衣服穿了十幾年不肯丟棄,家裡不裝空調,一臺電風扇用了數年還在客廳裡運轉。……
澤公將工廠所有的盈利毫不吝惜地用在印贈經書和供養三寶上!他將價值四、五百萬港幣的住房贈送給佛教界、幾十年如一日地供養數十名出家人、將數千萬的錢財用於印贈經書,扶危濟困,而他自己呢?有一次竟然拿不出幾萬港幣用以支付住院費……
毛澤東先生曾經說過:「一個人做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倣好事,不做壞事。」澤公就是這樣一個平凡的人,他一輩子所做的祇是鎖碎而平凡的事,澤公又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他的偉大正如南懷謹先生所說:「古德有云,勇猛精進易,長遠行持難,但何澤霖居士,卻能忍辱精進,肩負播種慧命的工作,先後長達三十年之久……故能德臻洪範,為來者之效法爾,願賢達察正焉!」
在綿綿細雨中,裝載澤公的靈車從香港世界殯儀館駛出,一路緩緩西行。那些認識和不認識澤公的善信男女從四面八方趕來,在風中雨中,在綿延不絕的念佛聲中,扶靈恭送澤公最後一程,沒有悲傷,沒有哭泣;祇有感激,祇有期盼!此情此景令大地日月為之動容!
二月八日下午三時,遵行香港的法律,經過幾千度高科技高溫火化和粉碎之後,人們欣喜地看到了澤公淡彩色的靈骨中,呈現出數百片粉紅色如同蓮花的靈骨片。親人們將彩色靈骨片連同澤公的音容笑貌珍藏起來,而將骨灰,遵照澤公生前的遺願、撒向香港與澳門交界的大海裡。遙望西天,我們和眾人一樣衷心祈願:願何澤霖大德不捨眾生、乘願再來!
這個冬天南方很冷,陰霾密佈,薄霧籠罩,淅淅瀝瀝的小雨一直下個不停。
在南粵這個數十年難遇的寒冷冬天裡,何澤霖大德悄無聲息地走了。他走得很突然,也很坦然。帶著對西方極樂世界的無限嚮往,帶著眾多善信男女的尊崇與感激,帶著親朋好友的諄諄囑托,在綿綿不絕的佛號聲中安祥地走了。
我們是在驅車前往廣州的路上得知這一噩耗的。電話是從香港六合園打來,伴隨著風聲雨聲和悠揚綿長的念佛聲。當時車內的一位法師和幾個學友聞此消息,有的悲戚不已,有的唏噓感慨,有的長時間靜默不語。而我們怎麼也不相信這是事實,感覺他離去的過程太快太突然!
因為就在一個月以前,得知他生病的消息,我急忙趕到香港去看望他,沒想到他並不在醫院裡,由於擔心我找不到去他家的路(事無巨細,他總是為別人想得很周合)他還親自跑到元朗來接我,並精神抖擻地領我到他前年剛剛搬去、位於新界名為「六合園」的山村老宅裡,參觀他和夫人幾個月來在屋前屋後種的那些蔬菜瓜果。一路談笑風生,精神鑼鑠,我關心他的身體健康,他祇是輕描淡寫地說了聲「沒有事的」,反過來十分關心地詢問我所拍攝的電視連續劇《百年虛雲》的進展情況。我們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他的言談舉止全然沒有一絲病態。我離開時他仍像以往一樣,忘不了送我一本經書。一位慈祥健康,樂觀豁達的老人,相隔不過一月有餘,怎麼會說離開就離開了呢?
說人生苦短也好,說生命無常也罷,總之何澤霖大德真真切切地在這個冬天離開了那些深愛他的人們,一路佛歌,乘鶴西去。想起那一次在六合園,我曾經問他:「您住到這深山老宅裡來,樟木頭那邊印贈經書怎麼辦?」他說:「我該退休了!護持佛法自有後來人。」這也許就是老人對我們最後的告別。
澤公是二○○四年一月十六日上午七點十五分往生的,他離去的過程平靜而又富於傳奇。他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在自己預知的時間裡離開人間的。
一月十日,凌晨三點,臥病在床的澤公突然警醒,急忙喚夫人和晚年一直照顧老人的義女春艷到床前吩咐道:「我的神識剛才出去了,我見到了阿彌陀佛。」春艷「撲通」一下跪倒在地:「恭喜爸爸!」澤公繼續說道:「請打電話通知覺仁師、親證師、法光師,到時候為我做三時系念,念佛一周」。說完他又吩咐拿來紙和筆,親筆寫下:「從今起,早7:30到7:30分為我助念,限20人,每天準備食物,此會通知,不是我的意思。」(乃另有聲音告知)。
家裡人開始不明白他為甚麼要求準備二十人的飯食,由於澤公晚年居住的六合園地處偏僻,遠離市區,購物及餐飲均不方便。奇妙的是,那天清晨,聞知澤公臥病在床的香港、新加坡信眾相約到六合園看望澤公並為其助念,他們恰好在七點半以前陸續到達,恰好來了二十人!
眾人驚訝澤公預知時至,更加敬佩大德的修為及證悟,不敢懈怠,連忙輪流助念,晝夜不停的佛號聲在六合園的上空整整彌漫了一周。自澤公留下遺書恰好一周以後。一月十六日上午七時十五分,享年七十九歲的澤公在他六合園的家中安詳離去,從此了生脫死,往生蓮池。
國學大師南懷謹先生聞訊親擬訃文文告,昭示海內外。眾多寺院舉行追薦法會。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副會長永惺長老率香港佛教聯合會同仁,中國佛協咨議委員會副主席佛源長老率雲門寺四眾弟子,淨空老法師率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同仁,香港覺仁長老,願炯法師及眾多僧俗大眾送來了挽聯、花圈。人們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對這位終其一生,播種佛法慧命的大德表示了由衷的贊嘆和懷念。
在最後幾天恭送澤公遠去的日子裡,在一次又一次為澤公舉行的蒙山施食,三時系念等法會中。我們親眼目睹了眾多海內外高僧大德,成百上千的善信男女對澤公的深情厚誼。震撼之餘、我又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在我們的記憶中,澤公像一位慈父:永遠和言悅色,永遠平等待人。他那種愛到深處才自然流露出來的眼神、對於任何一位認識他或是不認識他的人都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因此,我們總能見到不少人親近他,感激他。我們還知道他從來不知疲倦,從來粗茶淡飯,從來祇為別人著想。但除此之外、他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蹟,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這樣一位平凡普通的老人,何以讓如此眾多的僧俗大眾敬仰側目?
我們帶者這種疑惑深入探究。對澤公了解愈多,我們便愈發汗顏!祇有這時候我們才開始體會「平常心是道」的含義;才能理解南懷謹先生何以在挽聯中如此評價澤公:畢世護法無雙士、生往蓮池又一尊。
澤公是我們認識的最為平凡,最為默默無聞但又無比崇高的一位老人;是我們知道的最為虔誠、最無私心、而又最不普通的一位佛教善知識!
澤公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出生於澳門,母親旱逝,他由奶奶一手撫養,由於自幼在教會學校讀書的緣故,澤公早年曾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徙。一九五二年他移居香港,為了維持生計,他捨棄了教師這一職業,和妻子林茜英一起,打小工,織毛衣,含辛茹苦,日積月累,漸漸發展到自己開辦了工廠。年輕時的艱難磨礪,造就了他惜福、樂善好施的本性。
由於經常去大嶼山看望已削髮為尼的姑姑的緣故,澤公自一九五四年閱始接觸佛教,從此便難以割捨,他不僅很快皈依佛門,而且發願將此身心奉獻給佛陀。
一九七九年,澤公利用他們夫婦胼手胝足,歷經十幾年奮鬥,省吃儉用才得以購置位於北角大廈的第一套房子,自行創辦了香港佛教圖書館,免費向佛教徒借閱、贈送圖書。後來他又將圖書館連同這套物業一並贈送給佛教界,成為佛教的公共財產。二十多年過去了,圖書館運轉依舊,至今仍是香港信眾修學佛法的重要活動場所。
八十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機會,澤公到湛江旅游,見到一位年邁的出家人在水塘邊挑水,澤公上前頂禮法帥,並問有甚麼可以幫到他的。出家人甚麼話也不敢說,挑著水徑直往茅棚走。第一次接觸大陸出家人的澤公,不明箇中緣由,跟隨出家人來到茅棚裡,發現這間茅棚破爛不堪,空徙四壁,甚至連一尊佛像都沒有。澤公將隨身帶來的幾本經書送給出家人,出家人如獲至實,老淚縱橫!原來經過文革之後,大陸佛教破壞殆盡,佛像經書蕩然無存。如今雖然撥亂反正,恢復落實宗教自由政策,但佛經典籍的乏饋一時難以解決。了解到這些情況之後,澤公將位於東莞樟木頭的工廠的事務全部交給夫人管理,投人全部身心在樟木頭設立辦事處,向大陸各寺院印贈經書。
他這一做就是近三十年。
他每天往返於香港和東莞樟木頭,用其瘦弱的身體,背負沉重的經書!從香港佛教圖書館搬上廣九列車、在深圳羅湖下車後跟隨擁擠不堪的人群過關,出關後又轉火車到樟木頭,再坐汽車到辦事處……每一個來回都異常艱難,但澤公幾十年如一日、像螞蟻搬家一樣,不知疲倦地來回奔走。等書運抵樟木頭後,他又和工作人員一起,小心翼翼地將一本本書包裝好,附上他親筆寫的信函分發到全國各地急需的寺院,隨著時間的推移,來信求書求物的人越來越多,小到一本《禪門日誦》大到洋洋數百本一套的《大藏經》。澤公背負的擔子越來越重,但他堅持每信必復,有求必應、在工作人員的印象中他從未拒絕過任何人的請求。就這樣背書、印書、送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
沒有人做過統計,這二十幾年來,澤公到底贈送過多少本佛經典籍!人們祇知道,有一年,他僅念佛機就贈送了一百多萬只!也沒有人計算澤公印贈經書到底花費了多少資金,身邊的工作人員祇知道每天僅郵寄費就要花掉兩、三百元。每天兩、三百元乘以二十年、已經是一個龐大的數字,更何況印刷、運輸這些更為不菲的開銷!
改革開放,恢復落實宗教自由政策二十多年以後的今天,對於許多金碧輝煌的大陸寺院而言,裝禎精美的各類佛經典籍俯拾即是,已不足為奇,但時光倒退到二十年以前,澤公送出的每一本書就如雪中送炭一樣珍貴。許多人因澤公的一本書而生起正念;許多寺院因澤公的一套書而恢復寺院秩序!從剛剛出家的小沙彌到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從初入佛門的居士到享譽海內外的趙樸初大德,成千上萬的人從澤公贈送的經書中獲益。
稍有年歲的出家人大多知道何澤霖這個名字,但多半祇聞其名,未見其人。
澤公沒有絲毫名利的觀念,他將自己全部的財產乃至身心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佛教事業!
澤公算是個有錢的人。乘改革開放的東風,澤公和夫人在樟木頭的針織廠曾經財源滾滾,鼎盛時僱用員工一千多人,二十多年來少說也有數千萬盈利。
但接觸過澤公的人覺得他又像個沒有錢的人。他一家生活始終異常節儉:出門坐公交車,吃飯是素食,一件衣服穿了十幾年不肯丟棄,家裡不裝空調,一臺電風扇用了數年還在客廳裡運轉。……
澤公將工廠所有的盈利毫不吝惜地用在印贈經書和供養三寶上!他將價值四、五百萬港幣的住房贈送給佛教界、幾十年如一日地供養數十名出家人、將數千萬的錢財用於印贈經書,扶危濟困,而他自己呢?有一次竟然拿不出幾萬港幣用以支付住院費……
毛澤東先生曾經說過:「一個人做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倣好事,不做壞事。」澤公就是這樣一個平凡的人,他一輩子所做的祇是鎖碎而平凡的事,澤公又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他的偉大正如南懷謹先生所說:「古德有云,勇猛精進易,長遠行持難,但何澤霖居士,卻能忍辱精進,肩負播種慧命的工作,先後長達三十年之久……故能德臻洪範,為來者之效法爾,願賢達察正焉!」
在綿綿細雨中,裝載澤公的靈車從香港世界殯儀館駛出,一路緩緩西行。那些認識和不認識澤公的善信男女從四面八方趕來,在風中雨中,在綿延不絕的念佛聲中,扶靈恭送澤公最後一程,沒有悲傷,沒有哭泣;祇有感激,祇有期盼!此情此景令大地日月為之動容!
二月八日下午三時,遵行香港的法律,經過幾千度高科技高溫火化和粉碎之後,人們欣喜地看到了澤公淡彩色的靈骨中,呈現出數百片粉紅色如同蓮花的靈骨片。親人們將彩色靈骨片連同澤公的音容笑貌珍藏起來,而將骨灰,遵照澤公生前的遺願、撒向香港與澳門交界的大海裡。遙望西天,我們和眾人一樣衷心祈願:願何澤霖大德不捨眾生、乘願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