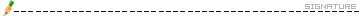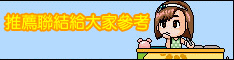張居正
戚繼光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神宗皇帝的“太師張太岳先生”,中極殿大學士、太傅、太師,大明朝自李善長之後兩百多年來首位生受三公封號的文臣張居正,病重不治,離開了人世。
張府緊掩的門縫中終於傳出了撕心裂肺的嚎叫。那一刻,從紫禁城到王朝的每個府縣衙門,整個大明帝國好像劇震了一下,所有人都覺得腳下猛地踩了個空。於是他們都屏住了呼吸,億萬道目光同時投向了那一片縞素的帝都上空。
那裡烏雲密布,低得幾乎壓到了城牆。滿目混沌,誰也不知道雲層的深處隱藏著些什麽,甚至相對的兩人都看不清對方的臉色究竟是哀是喜。除了浩大的哭聲,靜得可怕,但耳力好的人似乎能在號啕因換氣而停頓的瞬間聽到骨節格格作響的聲音,像是有人在摩拳擦掌活動手腕。
張居正是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音了。彌留時,他耳邊只縈回著他教導了十幾年的學生,二十歲的皇帝那悲淒而誠摯的話:
“先生功大,朕無可爲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
張居正終年僅五十八歲,《明史》未載他所患何病,據他自己在書信中說是因爲痔瘡,多年誤治,訪得名醫割治後卻消耗太大:“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於不起”,纏綿多時還是“不起”了。
但時人王世貞,文壇“後七子”的領袖兼史家,卻在《嘉靖以來首輔傳》中明言,奪了張居正的命的並不是區區痔瘡,或者說,痔瘡不過是表面的病症,真正的病因是由於他吃多了壯陽藥,藥性太過燥烈,又服用寒劑下火,因此發而爲痔。幾十年後,有個文人,沈德符,根據他在京城多年的見聞寫了筆記《萬曆野獲編》,說得更加詳細,不僅認定張居正確因濫服壯陽藥耗竭元氣而亡,還指出張居正所服之藥爲膃肭臍。
膃肭臍,就是今天常見的高檔滋補品海狗腎。以“腎”爲名的中藥一般指的是雄性動物的外生殖器,也就是常說的“鞭”之類。中醫講究以形補形,很多動物的臟器都是大補的“血肉有情之品”,如“以臟補臟”、“以骨補骨”,“腎”、“鞭”之類的藥物自然具有很好的壯陽效果。而諸多“腎”、“鞭”如黃狗腎、鹿鞭中,海狗腎便是藥力很霸道的一種。且不提海狗之腎,只是海狗之油——脂肪,便有奇效,冬天手腳龜裂塗之即愈,且來年不復發,因此《綱目拾遺》雲“其性熱烈可知”。服此物後房中之效如何當然只有張居正自己知道,但據沈德符所載,張居正“嚴冬不能戴貂帽”——天天服食壯陽藥自然暖和,只是苦了百官,再冷的天也只能跟著“太師張太岳先生”光著腦袋捱凍。還有一本明人筆記《五雜俎》,云張居正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也符合服用燥熱之藥過多的症狀。
海狗的原動物有兩種,一種是真正的海狗,另一種則是海豹,我國古代本草記載的膃肭臍來源兩者都有,但一般還是指海豹。無論海狗還是海豹,都生活於寒帶或溫帶海洋中,分佈的緯度較高,大部分在北太平洋,我國只有在渤海灣內沿海出產,其他地方只是偶爾見到。因此自古便是難得之物,假貨也很多,用沈德符的話說是“百中無一真者”。
張居正自然不必擔心吃到假藥,何況孝敬此藥的人更是可靠之極。沈德符言之鑿鑿:此妙物“蓋薊帥戚繼光所歲獻。”
還有一些資料則記載了戚繼光所獻的妙物不僅僅限此,居然還包括了試藥的工具,如王世貞便說“(戚)時時購千金姬”送予張居正!
媚藥?千金姬?歲獻?時時購?——戚繼光?!
不敢相信,是嗎?
也許有人說,王世貞與張居正很有點不對眼,他的記載可能多些油醋;但他同時卻是戚繼光的好友,如果真是一盤子虛烏有的污水,何苦連累戚繼光呢?
且不提千金姬、膃肭臍,翻翻張居正自己的書牘,也白紙黑字寫著戚繼光送禮的記錄;還有那次張居正回鄉葬父,戚繼光派了一整隊鳥銃手作爲儀仗是世人共睹的;而且誰都知道,首輔張先生家的大門永遠對戚繼光敞開,即使夜再深,也沒有一個護衛敢阻攔傳送書函的邊關騎士。
夠了吧,這足以說明,戚繼光與首輔張先生的關係非比尋常。
於是,後世不少史家寫到此節,深深皺起了眉頭。
其中有不少人沈默許久後,長長歎了口氣,閉上眼睛,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是嫉妒者的誣衊;或者,自己根本沒看到過這些資料。
因爲誰都知道,戚繼光是個不可輕易塗抹的英雄。
戚繼光的抗倭功業彪炳千秋,閩浙綿延千里的海岸線上,至今隨處可見紀念他的碑刻雕像廟宇,海潮升時,似乎還能聽到四百多年前那群亡命武士絕望的驚呼:“戚老虎來了!”很多地方甚至把他與關羽、岳飛合祀。
當然,戚繼光絲毫無愧於這些崇拜,但感恩的人們卻不自覺地冷落了當年與戚繼光並肩抗倭的另一位英雄,俞大猷。
俞大猷與戚繼光多年的上司,最後官至兵部尚書的譚綸曾評價過當時幾位名將的軍事才能,在指出了俞的一些不足後話鋒一轉,如此下了結論:“然此(指戚繼光等人)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意思是俞大猷能擔起比戚繼光等人更重的擔子。俞大猷還是個傳奇人物,據說劍術天下無敵,還單挑過少林寺,寫過一本“武林秘笈”《劍經》。
俞大猷一生也是身經百戰,但他最大的特點是官運奇差,幾十年間,屢屢奪職、降級、奪蔭,甚至下獄幾乎處死。如果爲他的一生畫一條軌迹,明顯就是波浪狀,憑著軍功高了一點,又驀地下來,倔強地上去,又驀地下來,如此力量銷解,總掀不起滔天駭浪,因此功業自然難及戚繼光,以至於後世被很多人遺忘。
似乎每個上司看俞大猷總是不順眼,每次立了大功,不是“嚴嵩抑其功不敘,但賚銀五十兩而已”,便是“功爲趙文華、胡宗憲所攘,不敘”;失利時,上司把屎盤子順手扣來任你俞大猷武功再高也躲不過:“坐失律,謫充爲事官”、“劾大猷縱賊,帝怒”、“委罪大猷縱賊以自解”……
原因也簡單,俞大猷爲人正直,“以古賢豪自期”,學不會逢迎討好,又臭又硬,誰看了都不順眼。
嘉靖四十一年,倭寇大舉進犯福建,攻佔興化。明廷急委俞大猷爲福建總兵,戚繼光任副職,前往圍剿。兩人聯手誰能一擋,倭寇大潰。但論功時,戚繼光功居首位,取代俞大猷爲總兵,大猷卻只得了些賞銀。
報功奏章怎麽寫,很大程度決定于上司的一支筆,如此看來戚繼光與領導處得比俞大猷好多了。
細究戚繼光一生,在所有位上與同僚上司下屬都相處甚好。他的上級胡宗憲、譚綸、劉應節、梁夢龍,監軍汪道昆、趙大河等人,大都與他有深厚的交情,至少不會掣肘,如此情形,俞大猷自不能與之爭功。
與上司套交情,奧妙無窮,少不了銅臭齷齪見不得人之事,但俞大猷從未因此鄙夷戚繼光,更沒有嫉恨過他,一生始終是戚繼光的知己至交。因爲他明白,無論戚繼光用什麽手段來爭取上司同僚的支援,目的與他一樣,都是爲了大明江山,爲了天下蒼生。他由衷地爲戚繼光能在如此融洽的環境下獲得大展拳腳的機會感到高興。憑他歷經滄桑的老眼,他定能發現自己與戚繼光肝膽相照。
戚繼光少年時寫的詩句,便是他們共同的心聲:
“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但若想四海波濤真正平息,僅僅擁有譚綸一級的支援是遠遠不夠的。
戚繼光對大明王朝的弊病洞若觀火,他曾言:“(邊防)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他極其渴望能放開手腳報效國家。
於是,順理成章,戚繼光家鄉出產的海狗腎送到了張居正府上。
很快,戚繼光的背後有了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強硬靠山。
南方倭患大致已平,戚繼光北上鎮守薊州,防備韃靼。張居正盡可能爲戚繼光創造條件統籌全局,把他轄區內職位相當的高級將領全部調往別鎮;並接受譚綸的建議,令該區文官不得干預軍務;誰爲難戚繼光,他便不動聲色地將其人遷調至別處;至於財政後勤,更不須戚繼光操心。
戚繼光也不負張居正信任,“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明史》)
張居正在世時,戚繼光得到了大明朝允許武將所能得到的最高職務與榮譽。
這都是那些海狗腎之功嗎?
明末清初史家談遷在《國榷》中寫下了這麽一句話:“非戚將軍附江陵(張居正)也,江陵自重將軍耳。”張居正在書信中也說:“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爲希有。”海狗腎雖然珍奇,但若要比禮物貴重,一個不擾民、不刻兵的武將怎能是他人對手?張居正爲何獨獨如此厚待於他呢?
原因也很簡單,張居正也同樣“但願海波平”。如何評價張居正,幾百年來便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可誰也不能否認他對於天下大治的殷切願望。
但無論是戚附張,還是張重戚,在世人眼裡,戚繼光此舉終是有虧,反正如此結爲一體,便是私黨,絕不是光明正大的路數!所以《明史》將其與俞大猷相比時便下了個“操行不如”的結論。
誰都把戚繼光視作張居正的親信,然而他們有沒有細思,張居正的事業,原本就建立在私人來往的基礎上呢?
關於張居正的施政手段,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有段精闢的論述:“他採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親信如此如此向皇帝提出建議。這些建議送到內閣票擬,他就得以名正言順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復,”“爲了鼓舞親信,他有時還在函件上對他們的升遷作出暗示。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個特殊的行政機構,以補助正常行政機構之不及。”
“正常行政機構之不及”,指的是什麽呢?
那就是張居正尷尬的身份。
朱元璋創明後,爲集皇權,廢了沿襲幾千年的宰相,並以淩遲酷刑嚴令後世不得重設。內閣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秘書兼顧問,終明一朝僅是五品,只是後來皇帝偷懶,才慢慢權重起來,根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宰相,根據朱明祖宗家法絕不允許任何臣僚擁有統轄百官的權力,權勢越大,離合法性越遠。
所以張居正做不成堂皇的大臣,只能走權臣一路。
既做權臣,便不得不以手腕弄權,用領會自己意圖的親信來履行王朝的程式,由此推行自己的政策:考成法、一條鞭法、度田清丈等等。
如此做法自然是上不得桌面的,所以黃仁宇接著說:“這在旁人看來,就是上下其手;以氣節自負的人,自更不願向他低頭,以免於趨附權勢的譏訕。”
對於更“以氣節自負的人”的人,除了不低頭,還得毅然攻擊,像禦史劉台,便莊嚴彈劾張居正“儼然以相自處”,真把自個當成宰相了!
生前身後,有無數君子彈劾過張居正,他們總看不慣這位張先生的作爲。
不僅僅是權臣身份的問題,這位張先生還有其他一些正人所難容的行徑。
他居然是勾結閹人上的台!
張居正是與大太監馮保合力扳倒內閣首輔高拱取而代之的。高拱也很有才幹,但他看不起閹人,這很符合傳統士人道德,閹人是不能秉大權的,前朝王振、劉瑾之禍便是前車之鑒。張居正卻有自信,利用太監開路而反過來又能控制他們。從日後的政局看,他的確做到了。馮保集司禮掌印、提督東廠爲一身,又得到神宗生母李太后的信任,但張居正還是能夠掌握局面,他曾自得地說:“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咨于餘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幹一事”,“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
但你越是表白,君子們越是懷疑你們的關係。被一悶棍打下台,當日就雇著牛車被逐回老家的高拱恨極了張居正與太監,他在遺著《病榻遺言》中詳述了張居正不光彩的勾當,說張居正與馮保結拜爲兄弟,逢迎諂媚無所不爲,馮保的心腹沒一天不去張府,三人整天嘀嘀咕咕,簡直是合穿一條褲子。
除了費盡心機取得太監頭目的支援,張居正還討好太后。神宗有兩位太后,一位是先帝的正宮皇后,另一位則是生母李后。按皇家制度,新天子即位時在爲兩位太后上封號時應區分高下,生母應該比先皇皇后略低。馮保使個眼色,張居正心領神會,擬了詔書,兩宮從此並駕齊驅。李后感激,從此“傾心委倚”。
無論如何,這些都不像是正人的行徑。
如此上臺的張居正,自己屁股不乾淨,竟然以周公霍光自命,來行使宰相大權,是可忍,孰不可忍?
奏!植黨營私、擅改祖制、作威作福!
但有太后、宦官撐腰的張居正已經是穩如泰山,再多的奏章也動搖不了根基。
相反,他那不合法的命令卻一日比一日的不可抗拒,力度也越來越強,傳令下去,即便前方有大山擋道,也得立時化做齏粉。用王世貞的話說是:“張居正發令,即便是萬里之外,早晨收到晚上就已經奉行,如疾雷迅風,所向披靡。”
爲了這個效果,張居正顧不上自身小小的名節了。
但對於一個自幼熟讀聖賢書的儒家學子,張居正邁出與宦官交接的第一步定是需要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的,正如戚繼光送出海狗腎一樣。
戚繼光家教極嚴,其父戚景通爲官嚴正清廉,從不奉承權貴,有次甚至因拒絕遵循官場陋規送點小禮而丟了官。可以想像,以孝聞名的戚繼光在採購禮品時心情的痛苦。
但最終,高傲的張居正在宦官面前謙遜地彎下了腰,戚繼光則恭恭敬敬用火漆封好了一份份禮盒。
他們問心無愧。
因爲他們已經發現,若想實現自己的抱負,天下之大,只有此路還可一試。如此危機四伏的時代,絕不是靠夫子尋常的教誨便可救得的,張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不足以弭天下之患。”
張居正、戚繼光都是能大破常格的磊落奇偉之士,所以他們成就了一番事業。
戚繼光的“海波平”,不過只是張居正規劃中的一個局部。張居正的事業全面取得了明顯的成功:
“(張居正)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十年來海內肅清……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一時治績炳然。(《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
彈劾張居正的奏章一天天少了下去。
但君子們還是悻悻然地等待著。
萬曆五年九月十三日,一個七十四歲的老人死了。
這個無職無位的老人的死,在大明帝國掀起了軒然大波。
因爲他是首輔張居正的父親。
按著規矩上門表示慰問後,君子們正襟端坐,等著張居正做一件必須做的事。-丁憂。
所謂丁憂,是所有官員必須遵守的制度。至親逝世,如父母,自聞喪之日起,不計閏月,必須辭職守制二十七個月。
君子們有些幸災樂禍,我們趕不走你,你自己老父不爭氣,要拖你下臺,天意啊!
奪情!居然要奪情!
奪情,指的是皇帝特別指定,不許辭職。皇帝挽留、太后挽留、親信挽留,都可以理解,問題是,你張居正竟然也含含糊糊,準備答應奪情了?!
爲圖自身富貴,置生父後事于不顧,禽獸啊!爲子不孝,爲臣豈能盡忠?
彈劾張居正的奏章又滿天飛舞起來。“忘親貪位”、“厚顔就列”,措詞無比強烈。難怪,從前的一切還可勉強理解爲逆取順守,現在饒是你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了,丁憂事關孝道,你已經觸到倫理綱常的底線了。
張居正陷入了有生以來最爲嚴重的危機之中。他何嘗不想丁憂守制,但形勢逼著他不能離開一日,何況漫長的二十七個月!考成法已經上了軌道,一條鞭法與清丈法卻正是要緊關頭,一步不實便前功盡棄全盤皆輸啊,他實在離不得呢。
或者,還有一件事深深刺痛了他。我這還沒走呢,你們就向我的副手道賀了,那小子居然還受了禮?好勢利!難道我鐵定得走嗎?這大明的家,照樣我來當。
於是他默默接受了奪情的建議。
這下君子們忍受多時的火山終於大噴發了。雪片般的奏章不算,還一撥撥來到張居正府上,勸其萬萬不能有違聖教。苦口婆心,聲淚俱下。
小皇帝站出來爲他的先生出氣了。一翻面皮,準備用廷杖伺候彈劾張居正的大小君子們。
廷杖已經高高舉起,一干大臣連忙跑去張居正家求情。張居正的強脾氣也已經發作,托辭不見。有人急了,不顧一切奔到內室孝闈,找到了張居正。
“聖怒太嚴重,說不得。”張居正冷冷道。
“即使聖怒,也是爲的先生。”
張居正再忍不住,勃然下拜,命人拿刀來,架在自己脖子上,厲聲道:“皇上硬要留我,大家卻拼命趕我走,你們殺了我吧!”
衆人失色,明白事態已經不可挽回。
廷杖狠狠落下,血肉橫飛。紫禁城上空,彌漫開來刺鼻的血腥味。
奪情一事對張居正刺激甚大,《明史》載“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也許,張居正從君子們拼命以綱常教條阻止自己奪情一事看出他們的迂腐和不可共事,從而産生了一種道德幻滅感,從此行事更辣手,有誰敢反對他,朝聞夕報,同時自身也更講究享受了,排場越來越大。很可能,就是奪情之後,張居正才服用起戚繼光送來的海狗腎的。
既然看穿了君子們的礙事,張居正一不作二不休,下了一道更得罪人的命令:禁毀天下書院,不許士人聚集遊食,撓害地方。
沒有張屠夫,也不用吃帶毛豬,轟開你們這些滿口仁義道德的酸措大,隨你們說我“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吧,我張居正一樣要把事業做下去。
從此,他與親信的關係更加緊密了。回鄉葬父時,他生怕短期的離職引起戚繼光不安,特地通知他自己很快會回來的,你只管好好幹,不必擔心。
戚繼光則派了一隊鳥銃手爲張居正開路,以此表明他對首輔的理解與支援。
大明王朝繼續沿著張居正設計的軌道運轉。
但張居正在把君子們壓得敢怒不敢言的的同時,也注定了自己的下場。
張居正一死,君子們便準備動手了,那些被張居正的考成法捆得喘不過氣來或是被清丈法削瘦了的大小官吏更是迫不及待,無論正邪現在都是同仇敵愾。
張居正死後,只過了半年,終於有一道彈劾馮保的奏章送到了神宗面前,皇帝不覺脫口而出:“我等這道奏疏已經多時了。”聲音冷得滲人。神宗的目光,利箭般射向了張先生的故鄉江陵。
次年三月,詔奪張居正上柱國太師,八月再詔奪文忠公諡。
再次年四月,詔令查抄張居正家產。
應該說,正是多年來張居正對小皇帝管制得太嚴格,暗暗在神宗心中埋下了厭惡的根子,那些人才能在張居正死後慢慢窺測方向揣摩出聖上的心理,才引發出新一輪的彈劾風暴。
從小到大,神宗始終蜷縮在張居正高大的身影裡。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母后說的:“要是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麽辦?”
甚至十八歲時,因爲一次酒後小小的過失,母后居然還責令自己跪了三個時辰,甚至用《漢書·霍光傳》威脅要行廢立——當代霍光是誰?張先生!
這麽多年,你張居正篡了朕的權!
皇上聖明,天理迴圈啊!
當張居正的抄家單子擺在御案上時,年輕的皇帝同樣有了道德幻滅感。
你張先生的家底倒是豐厚啊,金二千四百餘兩,銀十六萬兩,房産一萬餘兩。他們還說你回鄉時居然坐三十二人擡的轎子,前軒後寢,旁有兩廡,一路每餐水陸珍饈上百樣還說沒下箸處,也太過份了吧。
你還記得嗎,朕當皇帝的第一個春節,連民間都大擺宴席賀歲,你卻只叫我添了幾樣水果,口口聲聲節省爲民!
還有,你張先生節制朕對宮中嬪妃的賞賜,而自己卻納了兩位絕色女子爲妾——據說還是戚繼光送的!
多年的道德約束,隨著張居正的徹底被清算而轟然倒塌。
看來沒有束縛的神宗皇帝從此將是一身輕鬆了。他很快有了向道德代言人,文臣君子們挑戰的需要。因爲寵愛有別,他想廢長立幼,立鄭貴妃之子爲太子。廷臣察出苗頭,大義凜然,硬是抵住了至尊的壓力,抱成一團持久作戰,直到逼著神宗立了長子爲儲才罷休。
他們的理由充分得很,聖人教導我們,對兒女不能偏愛,倫理綱常、長幼有序是我們帝國的立國根本······緊箍咒般日夜在朝堂上念叨。
沮喪的神宗終於發現了道德的威力,也發現了張居正的失敗,正是由於他輕視了這股傳承千年的道德力量,沒有向它妥協,這才使得君子們成爲了朕的同盟軍。否則,朕還真動不了張先生。
與傳統道德的較量中,張居正還能取得暫時的勝利,而他這個學生卻沒有那般魄力,於是大徹大悟的神宗採取了另一種方式來表示抗議。
消極怠工。幾乎二十年不上朝。
張居正死後二十年,兩京缺少尚書三人、侍郎十人、科道九十四人,天下缺巡撫三人、布政監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最嚴重時,整個帝國官員缺額達一半以上。廷臣請選補,不理,對所有空缺與官員調遷,不聞不問。連臣僚表示抗議的辭職報告也不理會,你自己脫下官服封了官印走了便是······
用一封奏疏的話說是:“陛下萬事不理。”
甚至你破口罵他,當時暴跳如雷,但冷靜下來,他照樣當作看不見。
神宗不上當,朕罰了你,宰了你,倒是成全了你的名聲,你正求之不得。
經過張居正事件後,神宗已經清楚,大部分的爭論、告訐、彈劾都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哦,不,是“訕君賣直”。他想起了當年爲彈劾張居正而前赴後繼伏身於廷杖下的那一大群人臉上痛苦而滿意的神情。
他寧願百無聊賴地坐在深宮中與小太監們擲銀爲戲。
他不再計較身後的評論,因爲他終於明白,在君子們強大的道德體系內,只有平庸的人才能得到好名聲,就像成祖以下,史家們一致恭維的好皇帝只有膽怯而溫和的曾叔祖孝宗一人(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張居正理應得到懲罰。
誰叫你“大破常格”的呢?
這就是後人評你的能治國不能服人,“工于謀國,拙於謀身”嗎?
如此收場你張先生也許早在意料中吧,你不是說過,己身不復爲己有,甘願充當鋪地的席子,任人踐踏甚至尿溺嗎?
那就如你所願吧:
“(張居正)假丈量田土,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破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敬修,子張順、張書,都著永遠戍邊。”
抄家官員還在途中,張宅早已經被當地縣令——當初最奉承張居正的地方官——封門,打開看時,已經餓死了十餘人。
拷問時,長子敬修不堪忍受,自殺。
有點遺憾,張居正家產,不到嚴嵩二十分之一。
“先生功大,朕無可爲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
且慢,看顧先放一邊,有件事還得說個明白:
“你家老爺與戚帥相結,凡有書問,雖夜中開門遞進,意欲何爲?”
是啊,如此將“相”和,莫非謀反?
不是都說戚繼光是頭猛獸,天下只有張居正能夠駕馭嗎?
戚繼光算是幸運的,如此險惡風波襲來,不過是罷職歸田養老。
對於神宗的寬宏,戚繼光無比感激,認爲是“聖明獨鑒孤臣,眷未衰也。”
但出人意料的是,這位時時購千金姬、歲獻海狗腎的大帥,回鄉後居然窮得連給自己買藥治病的錢都沒有!
董承詔《戚大將軍孟諸公小傳》云:“(戚繼光)四提將印,佩玉三十餘年,野無成田,囊無宿鏹,唯集書數千卷而已。”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缺錢買藥的戚繼光突然病發逝世。
他好歹保住了聲名。
張居正的名聲官職,要到天啓年間才被追復。奔走呼籲爲張居正恢復名譽的,卻是一位當年奪情之爭時被杖責八十的青年進士鄒元標。
四十多年後,面對不可收拾的危局,白髮蒼蒼的鄒元標終於理解了張居正。
但這世間已再無張居正。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