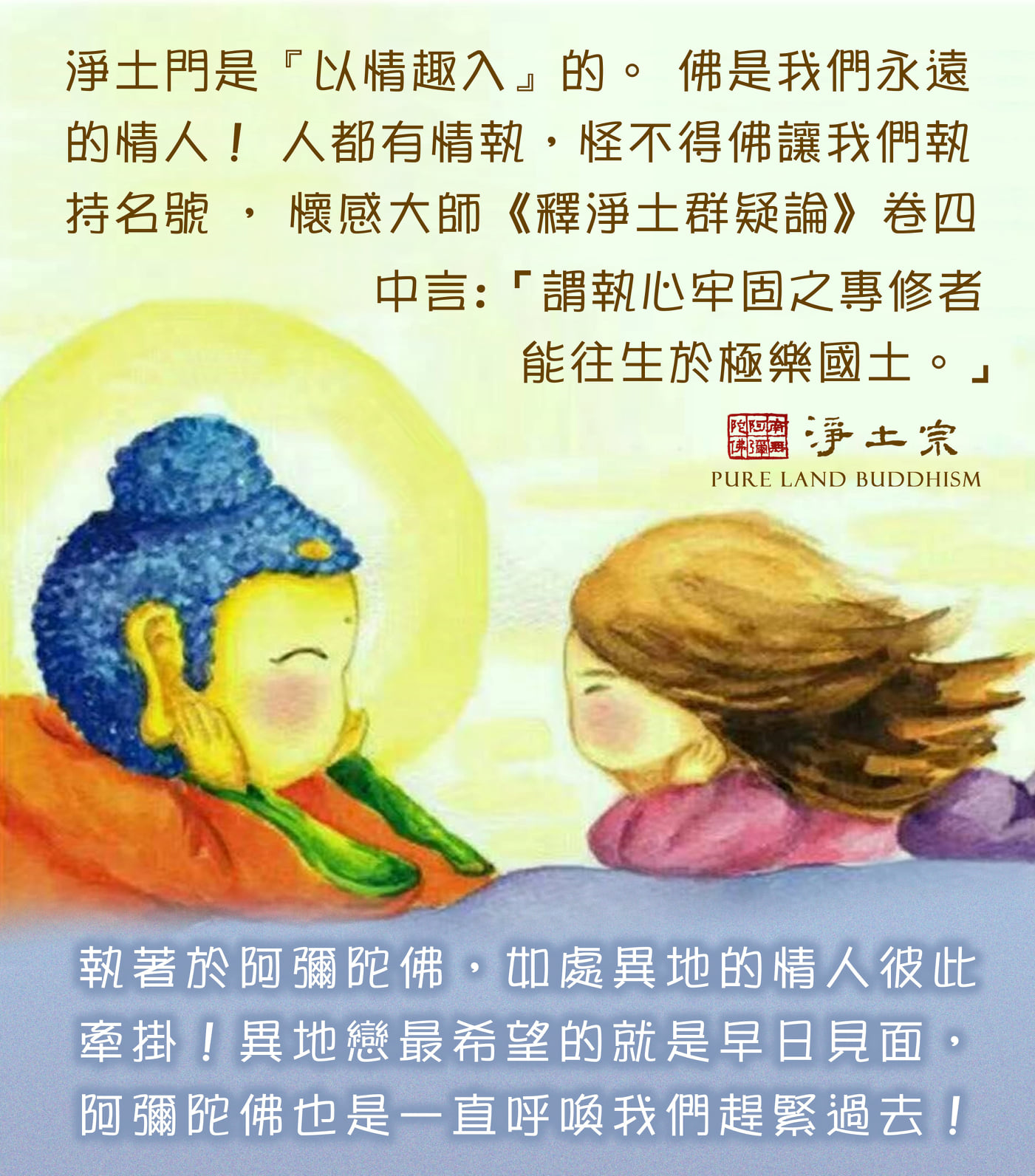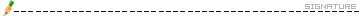回想起來,我的童年應該是比同年紀的德國孩子要舒服的多。我是德國人,五歲的時候,正值二次大戰,爸爸在蘇聯境內陣亡了,六歲的時候,我唯一的哥哥也陣亡了,我和我的母親相依為命。在二次大戰期間,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我的鄰居玩伴們,幾乎都失去了爸爸,即使爸爸或大哥哥還活著,也都是在前線打仗。
我還記得在我八歲的時候,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本來店裡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現在東西越來越少。我記得有一次媽媽帶我去一家百貨公司,裡面幾乎都是空的,連玩具都少得不得了。
可是我們家似乎一直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每三天,就有人送食物來,鄰居都羨慕我們,他們很難買到牛奶和肉,我和我母親卻從來不缺乏牛奶和肉,我甚至一直吃到巧克力糖,我知道鄰居早以吃不到蛋糕了,我們卻過一陣子就有人送蛋糕來,具我記憶所知,媽媽從不需要上街買菜。
我六歲進小學,念的是柏林城裡最好的小學,每天早上,有一個小兵開車送我去,放學時也有小兵接我回來。我雖然小,也知道我們的情況非常特殊,我問我母親為什麼政府如此的照顧我們,他說:『傻小子,難道你不知道你爸爸和哥哥都替國家犧牲了性命?政府當然會對我們好的。』我可不太相信媽媽的話,理由很簡單,我的同學也失去了爸爸和哥哥,他們為什麼沒有人送食物來?也沒有小兵開車送他們上學。
到後來砲聲越來越清晰。媽媽偷偷告訴我,俄國軍已經逼近。有一天,媽媽告訴我,柏林城所有的學校都已經關閉,事實上我上課的小學只有一半教室可以用。我記得最後一次上課,正好碰到空襲,我們在地下室躲了兩個小時,出來的時候,發現附近到處大火,我們都無心上課,只等家人來接送我們回去。
砲聲聽起來越來越近,媽媽也越來越焦慮。我當時還是小孩,還不懂什麼是害怕,看到外面軍隊調動,還有些興奮,可是連我這個小孩子都看得出來,我們德國軍隊是輸定了。看到軍人疲憊不堪的表情,我也很難過。
有一天下午,媽媽忽然告訴我,街上出奇地安靜,一個軍人都看不見,本來我們家門口附近永遠有一個兵在站崗,現在也不見了。更奇怪的是,砲聲也停了,我問媽媽為什麼砲聲停住了,媽媽告訴我大概俄國軍隊馬上就要進城了。
當天晚上,我睡的很熟,因為外面靜到極點,大概早上九點,媽媽把我叫醒,他替我穿好衣服,然後叫我做一件我當時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他叫我趕快逃離柏林,越快越好,媽媽告訴我該沿一條大路向北走,最好快跑,媽媽說,如果我快步走,大約兩個小時,就可以逃到鄉下,到了鄉下,我應該設法讓一個家庭收容我,媽媽一再強調我必須忘掉爸爸媽媽,不要再回來。當時外面一片漆黑,我當然不肯,大哭起來,可是媽媽最後還是說服了我,他準備了一瓶熱牛奶和兩塊麵包,他說我應該將食物吃掉以後,將熱水瓶丟掉,一定要裝得很可憐的樣子。他送我一個十字架的項鍊掛在脖子上,同時,又塞了一張紙在我的衣服口袋裡。
媽媽和我緊緊擁抱以後,還是趕我走。我走到街上,回頭看媽媽,發現他正在擦眼淚,可是他很快的關上了門,我知道非走不可了。我念的學校很注重體能訓練,所以我可以快步走很長的路,大約天亮的時候,我聽到砲聲再度大作,可是大概一個小時以後,砲聲忽然全部都停了,我知道俄國軍隊一定進城了,我可以想像得到俄國坦克進城的景象,我當然最擔心的事我媽媽。
鄉下總算到了,我已經累的再也走不動了,我找了一家農舍,發現馬槽大門開著,那時天才亮,鄉下人還沒有出來,我就進入了馬槽,馬槽裡面有一匹馬和一頭牛,牠們對我這個小孩子的入侵者根本不在意,我看上了馬槽裡的一堆稻草,倒上去就睡著了。
醒來以後,我發現我躺在一張舒適的床上,一位老太太大概一直坐在我身旁。看見我醒來,向窗外大聲地叫她的丈夫回來,這對慈祥的老夫婦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說我父親哥哥都去世,俄國軍隊快進城了,媽媽帶我逃離,因為難民人數相當多,我和媽媽失去了聯絡,媽媽曾告訴我,萬一走散了,應該盡量到鄉下去,那裡總會有好心的農人會收容我的,所以我就往鄉下走來。
老夫婦立刻告訴我,我可以留下來,他們有三個兒子,兩個都已經打死了,一個仍在波蘭,前些日子仍有信來。他們好像很喜歡我,替我弄了一些熱的東西吃,吃了以後替我洗了澡,然後叫我再上床去睡覺。我放心了,也默默地告訴媽媽,希望她也能放心。
老夫婦年紀都相當大了,田裡的粗工都不能做,可是仍在田裡種些菜,我也幫他們的忙。他們都信仰基督教,主日一定會去教堂,我也跟著去,老夫婦告訴我,我媽媽塞進我衣物的一張紙,是我的領洗証明,這又令我困惑了,媽媽雖然常常去教堂,卻不帶我去,理由是我太小。可是我同年紀的朋友們卻都常進教堂,我知道媽媽會祈禱,可是從來不教我祈禱,現在要我離開家,為什麼要讓我知道其實我已經領洗,我領洗這件事顯然是個秘密。
有一天,我和老先生一起在田裡工作,忽然聽到附近教堂裡傳出鐘聲,老先生立刻停下工作,他告訴我歐戰一定已經結束了,我們全家人都到教堂慶祝,整個村莊的人都來了,我發現一個年輕的男人都沒有出現,顯然我們國家將年輕男人幾乎都徵召去作戰了。
到這時候,我已經叫他們爸爸媽媽,他們正式到法院登記收養了我,我也就有了養父養母。我的養父養母最大的願望就是要看到我波蘭的二哥安全歸來。
二哥終於回來了,我永遠記得他出現在家門口引起的興奮,養母抱著他又哭又笑。他問我的來歷以後,對我非常和氣。養母立刻到廚房裡張羅吃的東西,雖然不是什麼山珍海味,我的二哥仍將菜吃的一滴不剩,他說他這兩年來,每天都想吃媽媽做的菜。
二哥安定下來以後,開始告訴我們納粹黨徒在波蘭殺害猶太人的罪刑,二哥談這件事時,養父有時叫我離開,大概因為我是小孩子,不應該聽這些殘忍的事情。可是我仍知道了我們德國人如何制度化地殺害了無數的猶太人。
有一天,二哥告訴我,有一個猶太小孩被抓去洗澡,他知道這就是他要被毒氣殺害的意思,這個小孩子講德國話,他問:『我是個小孩,我沒有犯了什麼錯,為什麼我要死?』說到這裡,二哥非常難過,眼淚流了出來,我覺得他認為犯了一個很大的罪,因為他曾被迫參加了這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二哥對我影響至甚,我從此痛恨納粹黨人在第二次大戰的罪行,也對於各種族、各宗教之間的隔閡非常不以為然。二哥改信天主教,而且一不作,二不休,進入了山上的一座隱修院,已苦修來度其一生。隱修士不僅不吃肉,也不互相講話,而且是永遠不離開隱修院的,我們全家都參加了他入會的儀式,在葛雷果聖歌中,二哥穿了白色的修士衣服走了出來,由於他的帽子幾乎遮住了他的臉,我差一點兒認不出他來,我那時候只有九歲。二哥是我們家唯一能種田的人,但養父母仍然一直鼓勵他去度這苦修的生活,他們知道二哥深深認為人類罪孽深重,而要以苦修來替世人贖罪。
而我呢?我進了小學,而且表現很好,功課永遠第一名,我似乎也有一些領導才能,因此我組織了一個學生社團,宗旨是促進不同種族和不同宗教間的信任與諒解。我們發現附近有回教徒,就去參加他們的禮拜,我們多數是基督徒,可是一再邀請猶太教的教士來演講,也參加了他們的儀式。我希望當年被納粹黨徒的種族仇恨再也不能發生了。
我一直掛記著我的生母,我的老家畫入了東柏林,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在我二十歲的那一年,進入了東柏林,發現我的老家已經不在了,當局造了一棟新的公寓,虧得我找到了一家雜貨店,雜貨店的老闆記得我媽媽。柏林陷落以後,我媽媽仍然活著,後來就搬走了。我有點悵然,可是知道媽媽沒死於砲火,也放心不少。
由於我的成績好,輕而易舉地得到獎學金,進入了哥廷根大學唸生物系,我有全額獎學金,可惜我養父在我大一的時候就去世了。畢業以後,我回到了鄉下,在一所中學教生物,也結了婚,有一個小女兒,養母和我們一起住。
我太太和我有同樣的觀點,我們都有宗教信仰,也推行不同種族之間的共融。
有一天晚上,我在看電視,電視上有一個尋人節目,我偶然會看這種節目,因為我希望看到我媽媽找我的消息,這一天,我竟然看到了,雖然我媽媽老了很多,我仍然認得出她來,而且她的名字也完全正確。她已病重說她要跟我見最後一面。
我立刻趕去,當時我已二十八歲,離開她時,我只有八歲,媽媽當然認不出我來,可是我帶了十字架項鍊,也帶了領洗證明,我也可以說出許多小時候有趣的故事,媽媽知道她終於找到她的兒子。
我告訴媽媽這二十年的經過,媽媽在病榻之上仔細地聽,可是她似乎最關心的是我對納粹黨的看法,我告訴她,我痛恨納粹的行為。她問我有無宗教信仰,我告訴她我們全家都信教,女兒一生出來就領了洗,每主日都去做禮拜。
媽媽最後問我一句話:「孩子,你是不是一個好人?」我告訴媽媽,我雖然不是聖人,但總應該是個好人。媽媽聽了以後,滿臉寬慰的表情,她說:「孩子,我放心了,我可以安心地走了,因為我的祈禱終於應驗了。」
我是一頭霧水,我不懂為什麼媽媽當年要拋棄我,現在有一再地關心我是不是一個好人。我就直截了當地問她,為什麼當年要我離開家?
媽媽叫我坐下,她說她要告訴我一個大的秘密,她說:「我不是你的媽媽,你的爸爸也不是你的爸爸。」
我當然大吃一驚,可是我看過我的領洗證明,領洗證明上清清楚楚地註明我的父母是誰。連出生的醫院都註明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問媽媽:「我明明是妳生的,怎麼說不是我的媽媽?那我的父母是誰?」
媽媽的回答更使我吃驚了,她說:「你沒有父母,你是複製的。」
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我學過生物,知道青蛙可以複製,高等動物的複製,我從未聽過。
我問:「我是從誰的細胞複製成的?」
媽媽叫我心理上必須有所準備,因為事實真相會使我很難接受,媽媽告訴我,我是由希特勒的細胞複製而成的,從生物的觀點來看,我是另一個希特勒。
媽媽告訴我,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希特勒就想複製他自己,他知道哥廷根大學的勒狄維克教授曾經複製過青蛙,因此強迫勒狄維克教授複製一個希特勒,否則會對他家人不利,勒狄維克教授不敢不從,卻果真成功了。當然他們需要一個女性來懷這個胎兒,希特勒找到了我的爸爸媽媽,大概是我的爸爸媽媽非常單純,跟政治毫無關連,媽媽身體也健康,因此我的媽媽被迫懷了我。
希特勒常常派人來看我成長,他下令我絕對不可以有任何宗教信仰,這就是媽媽不敢帶我上教堂的原因,可是我的爸媽以極快又極秘密的方式替我領了洗。在我爸爸最後一次上前線以前,他拜託媽媽一件事,那就是一定要將我變成一個好人,好讓希特勒的心願不能得逞。
我們家門口一直有一個兵在監視我們,當媽媽發現那個兵撤退以後,她知道我必須逃離納粹的監視。因為希特勒失敗了,可是那些死忠的納粹黨徒很可能認為我是他們唯一的希望,這樣,我的命運就悲慘了。她更怕蘇聯軍隊已知道了我的存在,所以她決定將我趕出家門,她有信心我會被好心的農人家庭收容,我也會在好的環境中成長。我離開了以後,媽媽說每天晚上祈禱中都不曾忘過我,她本來搬到一個小鎮去住,後來他開始和老朋友聯絡,大家也都問起我,可是好像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來歷,她放心了,因為當初知道我來歷的人本來就不多,現在這些人一定都已經死掉了。所以她決定再和我聯絡。
媽媽說她可以安心地走了, 因為她要在天堂裡告訴我爸爸,我是一個好人,這是爸爸最大的願望。
媽媽告訴我這個故事以後,顯得很疲憊,醫生告訴我,媽媽病重,唯一記掛的就是我,現在她看到了我,大概就不會活多久了。他叫我不要離開,果真媽媽不久就進入彌留狀態了,大概兩個小時以後,媽媽忽然醒了,她叫我*近她,用很微弱的聲音對我說:「孩子,千萬不要留小鬍子。」說完以後,媽媽笑得好可愛,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幾分鐘後,媽媽去世了。
我將媽媽安葬以後,到哥廷根大學去找勒狄維克教授,其實我曾經上過他的課,這位教授看到我,一副非常愧疚的表情,他說他的確複製了希特勒,可是完全出於被逼。他知道我的生活和想法以後,陷入於沉思之中,他說我絕不是希特勒想要製造的分身。
勒狄維克教授告訴我,他知道希特勒是不能複製另一個希特勒的,希特勒之所以是希特勒,主要是他有特殊的想法,他恨猶太人,他要征服全世界,也想讓純種的亞利安民族統治全世界,這種瘋狂的想法,並不能由一個單細胞所移植。
勒狄維克教授還告訴我一個驚人的秘密,他仍然保有希特勒的細胞,他問我要不要由他做一個實驗,以證明我的DNA和希特勒的DNA是完全一樣的。
我拒絕了,我不要人家檢查我的DNA是不是希特勒的DNA,我不是希特勒,我是我,希特勒心中充滿仇恨,我從來沒有,希特勒有極為病態的種族偏見,我卻一直致力於不同種族之間的諒解。
希特勒想要複製一個他自己,他當然想控制我,他錯了,他甚至不能控制他自己的命運,如何能控制我的命運?
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收音機播出葛雷果聖歌動人的音樂,我想起了在隱修院的二哥,我忽然了解了,我和希特勒最大的不同,恐怕是我有這個肯替世人犧牲一切的二哥,而希特勒沒有這個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