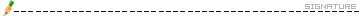歷史用以增進人文情趣及情操
【文/黃延齡】
英國的著名學者羅素(Bertrand Russell),不僅擁有深厚的數理科學涵養,在哲學和歷史的領域,也有非常卓越的成就。他在〈歷史學作為一種藝術〉裡說:
我並不認為歷史書,是為歷史學家們寫的。
我一直認為歷史知識,是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必須擁有的基本成份。
我們並不會認為,詩歌只應由詩人朗誦,也不會認為,音樂只讓作曲家們聆聽。
同樣地,歷史也不應只為歷史家們所知。……人的興趣被他短暫的生死所限制,一旦目光短淺、缺乏遠見,他的希望和要求就會變得狹隘。
而且,凡是適用於個人的,也同樣適用於整個社會。
那些只有很短歷史的社會,呈現單薄與孤獨的印象,常讓歐洲人十分難以理解。
這些社會中的人,不覺得自己是許多世代歷史的繼承人,因此他們打算傳給後代子孫的東西,是枯燥無味且缺乏感情的。
歷史使人認識到:人類的事務沒有終點,並未達致靜態上的盡善盡美,也還沒有至高無上的智慧。
不管我們的智慧到達什麼程度,與可能達到的智慧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
無論我們抱持怎樣的信念,甚至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信念,多半都不可能永垂不朽;如果我們設想他們體現了永恆的真理,那麼未來就可能會嘲笑我們。
羅素認為歷史豐富我們的生命、拓展我們的視野,足以令人虛懷若谷、氣度恢宏,是受教育者必備的養分。
因此,若有歷史學者恃才傲物,充滿讀書人的酸腐氣,充其量只是會一些記誦之學,根本完全談不上真懂歷史。
前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James B. Conant),擁有化學博士的頭銜,在《科學與常識》一書中亦說:
歷史家的著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感到那些歷史是真實的記述,否則我們去讀讀小說就好了。
一讀歷史,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想像,當凱撒渡過盧比河時,我們彷彿就站在他的身邊。
真的,只要歷史增加我們的知識,讓我們了解人類不同環境中的生活方式,我就心滿意足了。
十七世紀的大學者約翰•賽爾敦(John Selden)曾有一句名言:「歷史研究可以增長我們的年歲,彷彿我們從開天闢地以來,就已經活著似的。」
這一句話說出了為什麼,歷史研究應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
羅素與康南特這兩位科學人,都給歷史知識極高的評價,也都提到歷史的深厚經驗,是拓展生命深度和廣度的泉源。
現存的一切制度、習俗、宗教、藝術,都有其歷史淵源,具備「正常」求知欲和好奇心的人,通常會有「溯本追源」的理性需求。
另外,台灣話說:「吃水果,拜樹頭。」
凡是懂得「飲水思源」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享受既有的成果時,才能懷著一顆感恩的心。
懷古念舊的歷史情懷,自是不可忽略的情感需求。
至於,從「現在」回顧「過去」的經驗和智慧,反省歷史中人性的價值和理想,把這種反思拿來創造「未來」,更是人類文化進步的原動力,斷不可失去這種人文關懷。
這些人文情趣及情操的培養,都有賴「正確的」歷史見解及反思,是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養分。
滿足探索根源的理性與感情
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時期,不同地區的人類文明,無不曾思索過這兩個問題:
(1)宇宙是怎麼形成的?
(2)人類是怎麼誕生的?
中國、印度、猶太、希臘的創世神話,雖然各有各的答案,但對歷史根源的探索精神,卻是幾千年來歷久彌新。
人們對事物起源的求知欲,不僅止於宇宙及人類的開端,更擴及生活上的每個細節。
為什麼要過新年?情人節怎麼來的?為什麼要拜祖先?衣服是誰發明的?
當然,所有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開始的源頭,亦有整個發展的脈絡。
因此,從廣義上來說,探求任何事件發生的原因,都是在找其歷史的根源。
每一本歷史著作的內容,也都有探索根源的成分。
正確清楚地談論歷史的來龍去脈,不用說給人博學多聞的印象,就算親朋好友茶餘飯後的閒聊,也能增添清談的高雅情趣。
大陸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創造一股收視長紅的熱潮,培養出許多講述歷史的名嘴,就是歷史情節始末的趣味,足以吸引觀眾的結果。
不過,若能針對重要現象及人們關注的問題,譬如民主政治的根源和發展、祭拜祖先的淵源及意義、天文曆法的起源和觀念,就更能增進知性與感性的樂趣了。
宮布利希(Ernst Hans Josef Combrich)在《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裡,就把一周七天的來龍去脈,交代得相當詳盡而且有趣:
巴比倫人和亞述人把太陽、月亮和星星當作神來祈禱,幾百年來他們在溫暖、明朗的夜晚,觀察著星星的運行。這些頭腦清醒的聰明人,發現星星運轉的軌跡很規律,很快就認出蒼穹中似乎固定不動,每晚出現在同一位置的星星。
他們為星空中的那些「圖像」取名字,就像我們今天稱的「大熊星座」一樣。
他們認為地球是固定的圓盤,星空是一個空心的球體,像一只碗罩在地球上方,並且每天轉動一次。
這麼一來,對於當時並非固定不動,不僅鬆動地安置在那上面,還會到處「亂跑」的星體,他們一定感到非常訝異。
今天我們都知道,這些是和地球一起繞太陽轉的星星,稱之為「行星」。
但是古代的巴比倫人和亞述人並不可能知道,於是他們認為其中必有某種神秘的魔法。
他們給這些星星取了獨特的名字,並且一直翹首望著他們,企圖藉由這些星星的位置預測未來,這就稱之為「占星術」。
當時的人們以為,某些行星帶來幸運,某些行星帶來不幸。
火星表示戰爭,金星表示愛情。
人們為每位行星之神,奉獻一個日子,加上太陽和月亮,恰好是七個,這就產生了星期制度。
我們今天也還在說太陽日(Sunday,星期日)和月亮日(Monday,星期一)。
當時人們所知的五個行星是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
在某些語言裡,已經無法辨識這些行星的名字,但從其他一些今天還在說的語言中,仍然可以看出這種關聯。
我相信「年輕人」透過宮布利希的介紹,對「理所當然」的一周七天制,必然有「原來如此」豁然開朗的領悟。這種知識若拿來日常生活閒談,亦可以增添許多知性的樂趣。總是勝過盡聊些低俗趣味的八卦話題,亦勝於乾坐在沙發上吃洋芋片,面對著冰冷冷的電視機。
霍布斯鮑姆主編《被發明的傳統》,雖說揭穿了某些傳統的「人工面貌」,指出他們是刻意創造出來的東西,卻也「正本清源」地說明這些傳統的來龍去脈。
崔佛•路普(Hugh Trevor-Roper)談到〈蘇格蘭的高地傳統〉,花格子呢的蘇格蘭短裙,在1707年與英格蘭合併之前,原被視為野蠻風俗的象徵,是無賴、懶惰、掠奪及勒索成性的高地人的標誌;
到了通過聯合法案之後,經過一位英格蘭人的創新,花格子呢才成為蘇格蘭人的民俗標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象徵著對合併的抗議。
蘇格蘭改良的傳統服飾,象徵新的民族精神,讓1726年前尚無人知的蘇格蘭裙,很快地出現在高地各處;
英國國會曾於1746年禁止這類服飾,在法案中直接使用「蘇格蘭裙」這個字眼,可見它被塑造得極為成功。
霍布斯鮑姆研究〈1870至1914年歐洲大量創造的傳統〉,
這段期間由於選舉制度的群眾政治,各國統治者和中產階級的觀察家一再發現,社會架構和秩序的維繫含有「非理性」的成分,而且大部分都和群眾政治有關。
人為發明的「政治傳統」,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法國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在1880年推動一年一度紀念巴黎公社的活動,旨在對抗第三共和馴服工人運動的企圖。
共和政府則吸納法國大革命的成果,使其成為官方體制化的思想,最重要的莫過於1880年確立的「巴士底獄紀念日」。
這個節日綜合各項慶典活動,等於一年一度地宣示:法國自1789年起,就是一個民族國家,全國的男女老少,都會參加各項活動。
1890年5月1日的國際勞工運動,原是短時間內的自發行為,主要訴求在於爭取每日八小時的工作制,由此設計而來的罷工、示威活動。
但自1893年開始,恩格斯以Feier(德文,節慶的意思)來稱呼這一天,表示「五一」帶有節日的意味,加上象徵春天來臨的五朔節,歪打正著地和勞動節意義結合,「五一勞動節」很快地就成了價值不斐的年度節日和儀式。
這些隱含政治因素的節日慶典,在我們了解其「被發明」的根源後,將更明白其創造的目的和意義,「選擇」投入相關活動的立場時,不至於淪為非理性的群氓。
從這個觀點來看事物的根源,除了增添歷史知識的情趣外,往往還有透視現實意義的價值。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175817
古代中國很講「慎終追遠」的情感,對老祖宗的行誼和傳統,猶如「重土安遷」般堅守不渝。
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祖先而不忘本,風俗道德自然歸向淳厚。
然而,古老傳統的思想、風俗、習慣,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入侵,加上近百年政治、社會的發展,顯然已經消磨殆盡。
傳統的舊制度和舊思想,固然有些不合時宜、扼殺創新的地方,必須除之而後快;
然而,某些根深柢固的「優良文化」,原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命脈,若在顛覆傳統的過程中,連同封建餘毒被從根拔起,就會傷害現存生活的文化根基。
若要復興優秀的中國文化,就必須從歷史的脈絡裡,喚醒人們思古之幽情。
拿祭祖這個中國特色的傳統來說,假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追溯其根源、了解其涵義,反而把祭祖當成一種迷信,就很難激起「慎終追遠」的情感。
祭祖最原始的根源,可以推溯到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德國尼安德人和中國山頂洞人遺址的葬法和隨葬物,就已經反映著靈魂不滅的觀念。
靈魂不滅是鬼魂崇拜的基礎,祭祖則是鬼魂崇拜的具體表現。
《禮記•祭法》云:「人死曰鬼。」
從大量的甲骨文研究中顯示,商代已有天神、地祇、人鬼的宗教信仰,並且建立十分龐大的祭祖制度,甚至對祖先的崇拜壓倒了天神崇拜。
畢竟(觀念上)祖先的鬼魂離我們最近,他們死後具備非凡的超能力,更能直接影響子孫的禍福。
西周時,從王室到一般庶民百姓,都在祭祀著自己的祖先,但祭祀的對象和規模有著嚴格的限制。
庶民百姓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建造祖廟,只能在自己的家中設供進行祭祖的活動。
隨著周朝人文精神的發揚,主張「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子,從人道主義的精神反對人牲殉葬,卻反而提倡對祖先的祭祀。
他將祭祀祖先的精神,闡釋為報恩的孝道。
《論語•為政篇》裡記載:
孟懿子問孝,
子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若能了解這種祭祖的內涵,是對父母盡孝道的倫理基礎,更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就能增添幾分「慎終追遠」的情感了。
這種維繫家庭倫理的孝道精神,正是工業化社會以後最缺乏的道德,也常是當前社會問題的根源。復興慎終追遠的情感,不僅有助於中國文化的發揚,亦不啻促進和諧社會的一帖處方。
提升人文關懷的價值與理想
1764年4月至1765年5月,英國偉大的歷史家吉朋暢遊義大利,他到處探訪名勝古蹟,懷千年之往事、發思古之幽情,對羅馬這座永恆之城,更是流連忘返。
「我踏上羅馬廣場的廢墟,走過每一塊值得留戀的土地。
在羅慕洛站立之處、圖利(即西塞羅)演說之處,或者凱撒倒下之處,這些景象全都來到我的眼前。」
吉朋回憶道:「1764年10月15日,當我坐在卡皮托山崗的廢墟,獨自沉思冥想的時候,朱彼特神廟裡赤腳的托缽僧人,傳來唱著晚禱的歌聲。這時突然有個想法湧上我的心頭,就是撰寫這座名城衰亡的歷史。」
古羅馬曾經燦爛輝煌的遺址,讓吉朋從思古的幽情中,感慨偉大文明的勝敗興衰,從而想找出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
《羅馬帝國衰亡史》這部宏偉著作,雖然強調「蠻族的入侵」和「基督教的勝利」,是導致帝國滅亡的主要因素;
皇帝奢侈糜爛、殘忍蠻橫,帝國不斷向外侵略擴張、富裕繁榮導致人心腐化,全都與帝國衰頹息息相關。
這是基於歷史「垂訓鑑戒」的作用,突顯人類進步或退化的反思。
且聽他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怎麼說:
如果讓一個人說出,世界歷史上的那個時代,人類過著最幸福、繁榮的生活,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圖密善去世到康茂德繼位的那段時間。
那時廣褒的羅馬帝國,按照仁政和明智的原則,完全處在專制權力的統治下。
這些帝王的一舉一動,總會得到相當的報酬,他們的成就帶來無邊的贊頌,並因自己的美德感到真誠的驕傲。
看到給人民帶來普遍的幸福生活,他們由衷地感到喜悅。……奧古斯都之後令人不齒的幾位後繼者,他們之所以沒有完全被人遺忘,只是由於他們無與倫比的罪惡行徑和進行活動的輝煌舞台。
愚昧殘酷的提比略、狂暴的卡利古拉、軟弱無能的克勞狄烏斯、荒淫殘暴的尼祿、禽獸一般的維特利烏,以及膽小如鼠、令人不齒的圖密善,早就認定只能遺臭萬年!
對帝王這麼深刻的道德評論,自然在於給統治者一個警惕,莫讓個人的貪婪、殘忍、無能、奢靡、腐敗等惡劣行徑,陷百姓於水深火熱的苦楚,也給自己在青史上留下洗刷不掉的臭名。
統治者若能讀此史書,油然而生高貴的情操,亦不啻造就天下蒼生之福祉。
透過資本家壓榨勞工的眼光,馬克思審視整個歷史進程,發現「到目前為止,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這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提出的歷史論點。
批評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思想從仇恨出發,是心理病態的表現;
然而,不可否認地,馬克思對歷史的這種看法,基於鼓勵受壓迫的勞工起身與統治者鬥,背後其實隱含著很深的人道關懷。
馬克思從勞動者的苦難出發,回顧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設想階級壓迫的工具完全消失、不再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從勞動異化中把人性解脫出來,到達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反思歷史獲致的高貴情操。
偉大的歷史學者及歷史著作,從反思歷史油然而生的時代關懷及人文情操,正是其人格和作品的價值所在。
斯特恩(Alfred Stern)在〈歷史哲學:起源與目的〉裡說:「眾所周知,人是通過自己的苦難,來掌握住歷史實在的。歷史通過強加給人的苦難,將自身顯示為當前的實在;這與它以歷史知識為形式,作為撇在身後的陰影完全不同。歷史的實在是被體驗到的歷史。」
人從歷史裡反思自己的苦難,從而產生更高理想的企求,由此提升的人文關懷,更化為歷史創作的動機。聖•奧古斯丁撰寫《上帝之城》,原因是西哥德人洗劫羅馬。
這些游牧部落的勝利,進入羅馬城後的暴行,讓奧古斯丁反思,羅馬究竟犯了什麼罪,竟應遭受如此殘酷的命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部分是在拿破崙的隆隆炮聲中構思的。
關於歷史穩定性的觀念,關於偉大政治家是世界精神管理者的觀念,這一切都同黑格爾與耶拿戰役和對拿破崙的經驗緊密地聯繫,這種經驗既是令人沮喪的,也是高尚的。
二十世紀最激勵人心的歷史著作,莫過於斯賓格勒出版的《西方的沒落》。
這是一次世界大戰後,反省西方歷史文明的結果。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亦是受到兩次大戰的影響,試圖從歷史裡找到西方文明的一條出路。
這些極高人文關懷的情操,即是從反思歷史裡汲取了思想的養分,然後創作出另一種「歷史的反思」(歷史知識),提供讀者培養人文情操的養分,同樣是歷史學家責無旁貸的責任。
人文素養的情趣及情操,自非歷史學壟斷的禁臠。
舉凡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社會科學,都在追求人生的意義及美善,同樣有提升人文素養的功效。
文學、藝術令人領悟、感動者,必然反應了活生生的人性,使其昇華到更精緻的境界。
哲學和宗教若是完全跳脫人性,純粹是形上思辨及神秘體驗,這種真理僅存於「某些人」的邏輯、意志裡,或者在根本見不到的神身上,就會容易淪為抽象虛幻;
哲學和宗教唯有落實在人生裡,才能使人覺得真切有味。
至於社會科學取材的內容,廣義而言就是歷史。不論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都研究著人類的活動,多少涉及過去的流變,歷史學才有被其瓜分的危機。
即使探索宇宙、地球和萬物奧秘的「自然科學」,以及用來征服自然、利用厚生的「工業技術」,卻也必須站在「人」的角度思考,才能彰顯科學及技術的價值及意義。
某個手機廣告就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然而,「工業化」以後的價值傾向,往往過於強調功利主義,以至於產生了重科技而輕人文的弊端。
科技發展亦常常忽略「人性」的考量,甚至使「拜金主義」操縱了、扭曲了人性,這是工業化社會面臨的最大的文化困境。
要讓科技真與人性結合,創造出更正面的科技價值,就必須讓科技人有人文的關懷。
休謨(David Hume)在《人性論》上說:「一切科學多少都與人性有關。任何科學不論似乎多麼遠離人性,總會以不同的途徑回到人性。即使數學、自然哲學和自然宗教,都在某種程度上依靠於人。因為他們都處在人類的認知下,根據人的能力和感官來判斷。」
歷史是一門人性的科學,統攝了一切的人文現象。
基於事實、見解卓越、發人深省的歷史研究(這是歷史學家必須專心致力的地方),不僅可以提升讀者的人文關懷,更可以幫助洞悉人性的本質,不論什麼階層、什麼領域、什麼學科的知識份子,這都是人生必備的基本素養。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53期】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175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