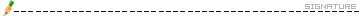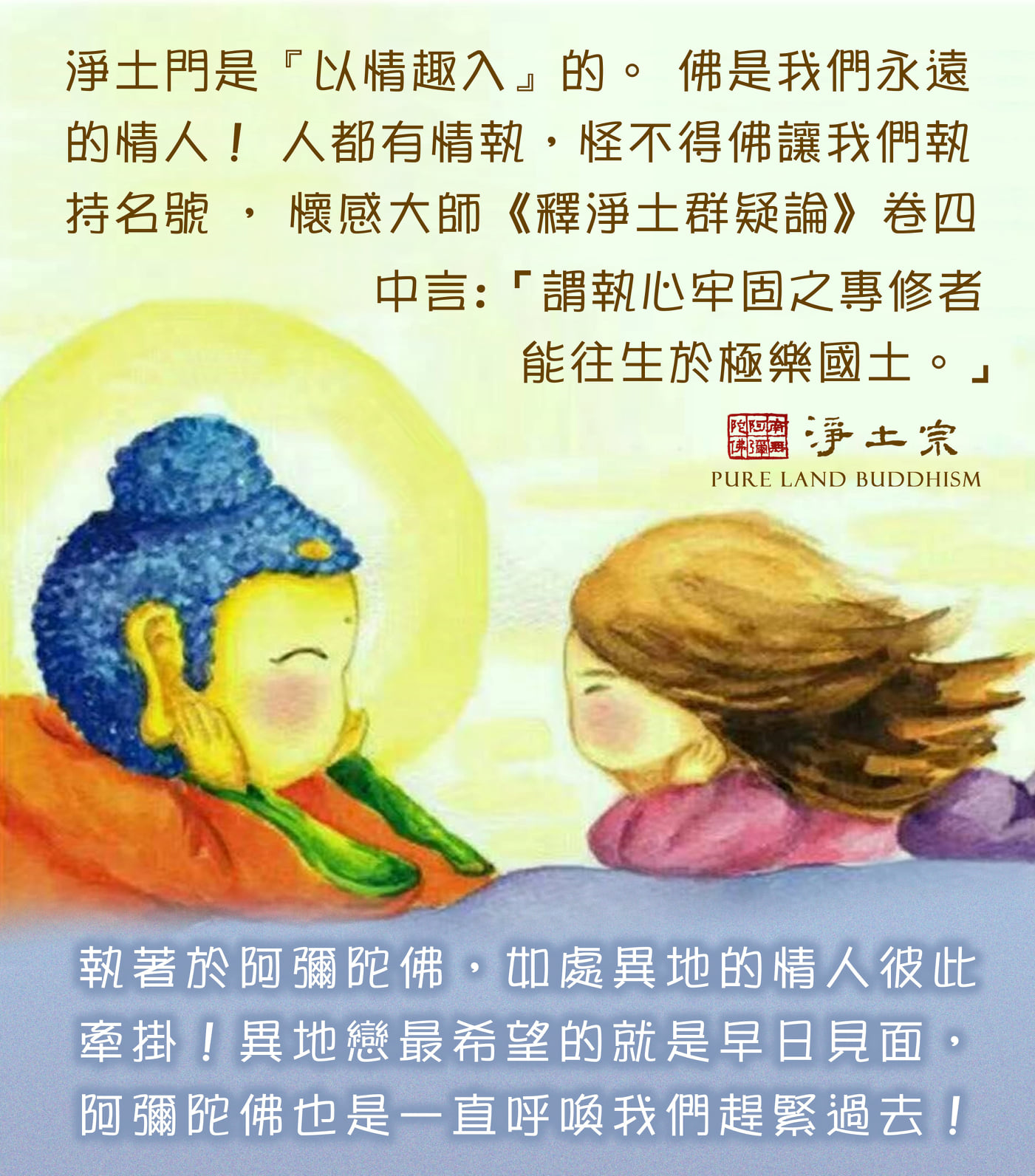書肆是古代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民間買賣圖書的場所。唐代形成了以長安、洛陽等城市為中心的圖書貿易場所,圖書經營品種增加。但書價偏高、抄寫週期長成為寫本的最大缺點。傭書人經濟狀況差異懸殊。探究唐代書肆的經營之道對於今天的圖書出版仍有許多借鑑意義。
書肆,又稱書坊、書林、書舖、書堂、書棚等,是古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民間用來圖書貿易的場所。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繁榮時期。單就圖書業而言,一方面,寫本書籍風行天下,達到「寫本時代」的鼎盛時期;另一方面,雕版印刷術開始在民間圖書市場應用開來。因而,唐代圖書業呈現「寫本」與「印本」混雜,「寫本時代」向「印本時代」過渡的特點。對這一時期書肆的研究,不僅能為我們研究古代圖書史提供一個參考的坐標,而且對於我們從民間書肆的角度重新審視和體會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特徵,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擬透過傳世文獻,並結合現今所得見的敦煌吐魯番遺書,從唐代圖書貿易中心等幾個方面入手,來探究唐代的書肆及圖書業,希求達到管窺全貌的目的。
唐代的圖書貿易中心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時期,書肆也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達到了一個新階段,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幾個規模較大的書業中心:
(一)長安 唐代長安的商品貿易主要集中在城中的東、西二市。市場內商品貿易活躍,各種商行眾多,僅東市就有「街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會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十二行,四千餘家,官私財物,金銀絹藥總燒盡」。這次大火所燒毀的四千餘家只是東市的部分商店,可見東市商業店肆之多。至於西市,《唐兩京城坊考》載:「南北盡兩坊之地,市內有西市局。」原註:「隸太府寺。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西市店肆稠密,比東市更加繁華。
長安的書肆也集中在東、西二市。新舊《唐書》中多有「市書」、「書肆」的記載。如《舊唐書•徐文遠傳》:「江陵陷,(徐文遠)被擄於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事,文遠日閱書於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新唐書•呂向傳》:「(呂向)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發然,也號『連錦書』,疆志於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還有雕版印刷的書籍也在東、西二市中出售。如敦煌藏經洞出土的編號為S.P.1《上都東市大刁家太郎》雕印曆日就是在東市印售的。伯希和2675號《新集備急灸經》寫本,書題下有「京中李家於東市印」,是據「京中李家」印本抄寫而來的。長安書肆為何多集中在東市,而不是在更為繁華的西市?這可能與東市沒有西市擁擠,環境比西市安靜,書肆主要消費群體如王公貴族、文人學士等多聚居於此,更適合圖書文教商品銷售的因素有關。
(二)洛陽 唐代洛陽共有三個市:「北市、南市在北郭、南郭的中心,北市占一坊之地,南市占兩坊之地。西市自西郭的西南角,也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別臨近漕渠、運渠和通濟渠,交通便利,商業比較發展。」以南市為例「隋曰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說明當時洛陽南市商行眾多,商品交易頻繁,書肆也很發達。
(三)益州 四川地區物產豐富,盛產紙張。如《舊唐書•經籍志》載:「開元時,甲乙丙丁(經史子集)四部書,各為一庫,置知書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可見其生產紙張的質量和規模。加上四川地區少遭兵燹,社會安定,人文薈萃,文化發達,書肆及圖書貿易也相應發達興盛起來。唐代書法家柳中郢之子柳玭在《柳氏家訓•序》說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餘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曉」。還說「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這說明柳玭隨僖宗逃到四川時曾在書肆中有過閱書的經歷。又如,1944年在成都東門外望江樓附近一唐墓中發現唐代雕印單頁《陀羅尼經咒》,就是由當地卞家刻印的。
(四)其他地區 唐代的圖書產業及流通範圍都比以前有所擴大。不僅內地的大城市有書肆,就是在邊遠地區也有了書肆。唐晚期文學家皮日休,賦詩回憶青少年時代的讀書生活:「乃將耒與耜,並換槧與鉛。閱彼圖籍肆,致之千百篇。攜將入蘇嶺,不就無出緣。」皮日休是襄陽人,可見在當時的襄陽,也有了稍具規模的書肆。不然,皮日休無法買到「千百篇」的書卷。
圖書經營品種
上文已略加考證了唐代的書業中心以及圖書的流通情況,那麼唐代書肆主要經銷的品種有哪些呢?由於古籍文獻對此記載大多語焉不詳,因而這裡略作考述。
(一)儒家經典、科舉考試用書 唐代在隋朝科舉制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繼承與發展,在進士科外又增加秀才、明經、明法諸史等科。科考用書也成為書肆的必備圖書。如《太平廣記》中的〈李娃傳〉寫到李娃救治滎陽生後,一日:「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其百慮以志學。」「墳典之肆」即為書肆。為了讓滎陽生重溫舊業,再進考場,李娃替他買了大量的科考必讀書、參考書。又如,李家皇室視道家老子為本家始祖,常常鼓勵人們讀《道德經》等道家經典,玄宗時,貢舉人要加試《老子策》等。所以,書肆中應該也有此類書籍,以備人們不時之需。
(二)語言文字類圖書 唐代,作詩成為社會風尚遍及各個階層。唐代名家詩集等一般都通過書肆售賣,廣為流通深受讀者喜愛。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詩人元稹為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作序時寫道:「《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喻〉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侯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又自註說:「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餘雜詩,賣於書肆之中也。」此外,作詩及文章所需的語文工具書,如《詩韻》、《玉篇》等也是書肆的暢銷品種。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刻本《大唐刊謬補闕切韻》就有伯希和2014、2015、4747、5531四個編號,說明這類工具書在當地的盛行。
(三)宗教類圖書 為了滿足廣大佛教僧尼信眾誦經、供經的需求,書肆組織大量人力抄、刻佛經,以便售賣。斯坦因5444號唐人寫本《金剛經》殘本,末尾寫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字樣,又有「天佑二年(905年)歲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十二歲老人手寫此經,流傳信士」,說明此經是根據四川成都過家書肆的印本抄寫的。而這類據印本抄寫的《金剛經》寫本,在法圖、英國等地所藏的敦煌遺書中均有發現。
(四)曆日、占卜等雜書類 古時,掌握時令,不違農時,是農業生產十分緊要的事情,農民迫切需要曆書指導農業生產活動,這就刺激了書肆對曆書的生產與流通。如東川節度使馮宿在給文宗的奏章中就有「劍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的話語。英國不列顛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歷》(S.P.10)就是在成都雕印後,售賣流傳到敦煌的。可見,當時書肆生產的曆日在四川、淮南、敦煌等地十分暢銷。另外書肆出售的熱門讀物還有相宅、算命、占夢之類。前文所引的《柳氏家訓》中就記載了柳玭在成都書肆中親眼看到相宅、算命等雜書的出售,而且數量不次於字典、小學之類的書,在市場上擁有大量的顧客。
(五)傳奇小說類 傳奇是唐代流行的短篇文言小說,是我國古代小說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其題材多取自現實生活,涉及愛情、歷史、政治、豪俠、神怪等諸多方面,深受文人和識字市民的喜愛。因此在書肆裡也出售傳奇、志怪等小說。唐代呂溫寫有《上官昭容書樓歌》:「……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並作序云:「貞元十四年(799年),友人崔仁亮於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有昭容列名書縫處,因用感慨而作是歌。」《研神記》是魏晉南北朝時的一部志怪小說,在唐依然流行不衰同時也透露了洛陽南市的書肆中也賣舊書。
(六)書法字帖 唐代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鼎盛時期,皇親貴族、文人學士等都對書法藝術備加推崇,而練字所用的名家字帖也是書肆不可或缺的品種。歐陽通「潭州臨湘人,父詢以書名著於時。通蚤孤,母徐氏教以父書,俱其家學不振,於是每遺通錢紿雲:『質汝父書蹟之直。』通遂刻意臨訪,不數年乃繼詢名,號大小歐陽體」。歐陽詢是唐代著名書法家。從文中可知,他的書法字帖也在書肆中出售,這樣歐陽通才能在其父死後將他的書法字帖買回。
(七)醫學書籍 如前文所提到的伯希和2675號《新集備急灸經一卷》就是據「京中李家」書肆的刻本抄寫而來的。該經卷按書中序言所說就是將流行於當時各家灸經匯集成卷,以供原缺醫少藥的偏遠州縣救急治病所用。文中還畫有正面人形穴位圖,讀者可以根據書中文字描述並對照穴位圖使用,起到了很好的圖示作用。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159081
寫本圖書價格
一般而言,「寫本時代」的圖書全靠人力抄寫而成,與雕版印書比較而言,存在複製性較差、抄寫週期長的缺點,必然導致價格的偏高。王建《贈崔杞駙馬》:「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貪,金埒減添栽藥池,玉鞭平與賣書人」,將「玉鞭」等價交換書籍,足證此書的價格之高。前文所述的李娃為滎陽生買的書「計費百金」,除說明所買圖書數量之多,也可知唐時書價著實不低。
宋代的《宣和書譜》記載吳彩鸞和丈夫文簫在南昌等地傭書時就有「簫拙於生,彩鸞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為糊口計」。《唐韻》共5卷,此價為平均每卷1000錢。吳彩鸞為唐文宗時期著名的女傭書人。關於此人在北宋歐陽修《歸田錄》等文獻中都有記載,說明當時確有其人。雖說她的活動多被後人神化,但一部《唐韻》賣5000錢則可能為事實,而這書價也不菲。據《新唐書•食貨志》載:「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令其著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弘文館校書郎、正字萬六千……」可知,會昌年間的百官月俸祿(祿米除外),最高的太師、太傅月俸二百萬;最低的主簙、中郎將月俸二千八百五十錢;校書郎、正字的月俸萬六千錢。由此折算,校書郎的月俸只能買三部《唐韻》,可見其售價之高。
那在敦煌,書價又是一種什麼情況呢?伯希和2912v號《施捨經疏及寫經施銀帳》給我們提供了當時敦煌的寫經價目:「寫大般若經一部,施銀盤子三枚(共三十五兩),麥一百碩,粟五十碩,粉四斤,右施上件物寫經。謹請炫和上收當賀賣,充寫經直。紙筆墨自供之。謹疏。四月八日弟子康秀華」,銀器是晚唐以後在敦煌市場上流通的一種特殊貨幣。從此件文書反映的情況來看,銀盤等用來支付寫經的費用。北京圖書館藏潛15號文書(北6460號)題記:「敬寫大般涅槃經一部,三十吊;妙華經一部,十吊;大方廣經一部,三吊;藥師經一部,一吊。」一吊為1000文,這與《宣和書譜》中記載的吳彩鸞所售《唐韻》的價格相仿。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紙價並不高。據潘吉星先生介紹,二十世紀初斯坦因在敦煌一個寺院中發現的唐代帳薄中記有:「〔正月〕十四日,出錢一百文,買白紙二帖(帖別五十文),糊燈籠三十八個,並補貼燈籠用……〔十一月〕十三日,……出錢六十文,買紙一貼,供文歷用……十二月一日,……出錢一百二十文,買紙兩帖(貼別三十五文)、筆兩管(管別十五文),抄文歷用。」從文書中看,當時紙的價格在35文、50文及60文不等。與當時書價對比來看,唐時的紙價並不算高,而書價主要高在抄寫的工價上。
當然,書肆面對一些經常光顧,但又一時手緊的老主顧時,也可以允許他們賒帳買書。張籍在〈送楊少尹赴鳳翔〉詩中就描寫了他給書肆還帳的情景:「往日詩名動長安,首首人家巷裡看。西學已行秦博士,南宮新拜漢郎官。得錢只了還書舖,借宅常時事藥欄。今去岐州生計薄,移居偏近隴頭寒。」
唐代的傭書人
隨著社會對書籍需求量的增加,漢代時就已出現了職業傭書人。如東漢的班超早年就因「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即為官府僱傭下的抄書人。傭書是圖書發行事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對圖書出版業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終唐一代,是我國「寫本時代」的頂峰時期,與此相適應的佣書業也發展到了極盛階段:「當承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傭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其所命。每昏暮,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其升沈,以備於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著十有二三幅。每日斷長補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歲之內,萬有餘眾」, 這些職業傭書人「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槧求工。道既多門,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遊,且託桑榆之蔭。傭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 。可見,他們多為具備一定文化水平而又為生活所迫的普通百姓或一時落魄的文人學士。唐代書業貿易的發達、各類圖書的廣泛流布是與這些傭書人的付出密不可分的。那麼,寫本圖書價格之高的唐代,傭書人的經濟狀況如何?
總體而言,民間傭書人的經濟狀況差異懸殊。經濟收入的好壞與各人的書法水平、出資人的經濟實力等因素有關。一些名氣較大、書法高超、容貌優美的佣書人所獲得的報酬就十分可觀。東漢時已經出現傭書致富的典型:安帝時,王溥「家貧無資,不得仕,乃挾竹簡,揺筆洛陽市傭書。為人美形貌,又多文辭。憱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吳彩鸞所抄的《唐韻》就能「市五千錢」。而一般情況下,大多數傭書人的佣書收入僅能維持基本生活,解決衣食之需。有過「傭書販舂」經歷的李商隱,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躬奉板輿,以引丹旐。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祔故丘,便同逋孩。人生窮困,聞見所無。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數東甸,傭書販舂。」《太平廣記》中所記的喬龜年「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歷中,每為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但由於傭書收入少,喬自己也抱怨說;「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所得資助,不足以濟。」
唐詩中也多有對傭書人的描寫。白居易的〈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就描寫了一對傭書夫婦的艱辛生活:「……西捨有貧者,匹夫佩匹婦。布裙行賃舂,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再如竇群在〈初入諫司喜家室至〉詩中也對傭書的艱辛有所描寫:「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
有些傭書人甚至連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北京圖書館藏宿字99號敦煌遺書(北8374號)《達摩論》在卷尾寫有一詩:「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誰家無懶漢,回面不相看」;斯坦因692號〈秦婦吟〉亦云:「今日寫書了,合有五升麥。高代(貸)不可得,還是自身災。」
此外,也有一些傭書人從事傭書活動完全是出於個人宗教信仰,而不以盈利為目的。如唐人王紹宗,「少勤學,遍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拒之。寓居寺中,以清淨自守」。
唐代社會對圖書需求的激增以及經濟利益的驅使,又導致書肆同行之間競爭加劇。宋人王讜在《唐語林》中就有這樣記載:「僖宗入蜀(880年),太史曆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差互朔晦。貨者各徵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濟,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表面上看兩家書肆是因為曆日在朔望、節候上的差異而爭執見官,實質卻是兩家書肆對當地曆日市場主宰權、占有權的爭奪。試想,一家節候不準的曆日,肯定無人問津。英國不列顛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具注曆日》(S.P.6 ),除將曆日、節氣等內容印刷在上外,還增加了「十二生肖圖」、「五姓安置門戶井灶圖」等,就已經超出單純的曆日範圍,屬於相宅、算命之類,是一部綜合性、多功能的曆書。這樣的曆書推入市場後,肯定會受到顧客的歡迎。
以上這些,都是唐代書肆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為求得自身生存發展而採取的一些經營手法。研究這時期的書肆經營之道,不僅能為我們打開另一扇研究古代圖書市場的窗戶,而且對於我們現代企業的市場經營理念也有一定的啟發借鑑意義。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50期】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159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