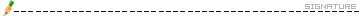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文/徐梓(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啟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也是影響最大的一種。《三字經》之所以歷久風行,影響所及,幾乎家喻戶曉,人盡皆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它內容豐富,知識性強。《三字經》篇幅不長,全篇僅1044個字,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容。明朝的呂坤,把它當作增廣見聞的讀物。清人紫巢氏,在為《三字經注解備要》作序的時候,稱它是「一部袖裡《通鑑綱目》」。民國時期的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對比,認為它雖然「字有重複,辭無藻采」,但「啟人知識過之」。(《重訂三字經》題辭)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也說:「《三字經》以一千餘字,歷舉中國文化義理歷史典籍,實一小型百科全書。」(《朱子新探索》第672頁,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三字經》深得人們喜愛的另外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齊,隔句押韻,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兒童喜聞樂道;並且,它的前後句自然連貫,語義順暢,淺顯明白,通俗易懂,絲毫沒有生拼硬湊的痕跡。
宋代之前啟蒙讀物主要用四言寫成
在宋代之前,中國傳統的啟蒙讀物,主要是用四言寫成的。從殘存的遺文和王國維等學者的考證來看,中國最早的啟蒙識字讀本,如《史籀篇》、《倉頡篇》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體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為淺近可讀的一段,歌頌漢朝的功德:「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穀孰成。聖賢並進,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寫成的。被人們視為「稷下學宮之學則」的《弟子職》、成書於六朝時期的《千字文》、唐代廣泛使用的《開蒙要訓》、成於唐而風行於宋的《蒙求》、介紹姓氏的《百家姓》、傳播歷史知識的《十七史蒙求》、闡釋理學概念的《性理字訓》、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在《三字經》出現之後,一些重要的啟蒙讀物如《龍文鞭影》,還是用四言編寫成的。可以說,四字句是傳統啟蒙讀物最主要的編寫形式。
用三言這樣短小的句子來表達意思,而且通篇如此,還要押韻,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張志公先生所說:「用簡短(三、四個字)而整齊的韻語,好處在便於記誦,但是往往有兩個缺點,一是容易寫得艱深難讀或者牽強硬湊,一是容易寫得貧乏呆板。」(《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第23頁)四言相對於三言,雖然只多了一個字,除了增加編寫的難度之外,對於成人來說沒有什麼不同,但對於兒童特別是低幼兒童來說,則意味著負擔的減輕,意味著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啟蒙讀物的沿革
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編寫的啟蒙讀物,雖然以《三字經》最負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說的那樣,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三字經》的出現也是淵源有自,是中國傳統啟蒙教育長期積累和發展的結果。
在《禮記•曲禮》中,有諸如「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之類短小整齊而又押韻的語句;在《列女傳》中,也有諸如「將入門,問孰存」之類的語句。這些語句,教習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規範,不虛玄,不高妙,是切近的灑掃應對之類的具體事情,適合蒙童的理解能力,體現了小學「只是教之以事」的特點。朱熹認為,這些短小而押韻的語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朱子語類》卷7)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朱熹把這些內容收錄在《小學》中。我們注意到,因為時代久遠,又沒有別的證據,朱熹在作這樣的判斷時,審慎地用的是一種不肯定的疑似口氣。如果朱熹的說法可信的話,那麼,早在《禮記》成書的戰國及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誦讀的讀本了。
在現今依然流傳、由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史游編寫的《急就篇》,其主體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學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內容都是用七言編寫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鄧萬歲,秦妙房,郝利親,馮漢強」開始,而以「姓名迄,請言物」轉入介紹「諸物」名稱。這一部分長達134句,在全書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積,前後句沒有什麼聯繫,沒有什麼意義。這種編寫形式,主要是中國人姓名的特點決定的,編寫者並沒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編寫啟蒙讀本的意思。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159073
在追溯《三字經》的淵源時,朱熹的《女已誌銘》也受到個別研究者的關注。朱熹的《女已誌銘》無序文,全部銘文只有86個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葬,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晦庵集》卷93)陳榮捷在提出這則材料的時候,雖然表明「吾人不敢謂朱子為陳淳《啟蒙》之前驅」,但又說:「陳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襲前人。假如必須先例,則可取諸其師朱子也。」雖然說「更不敢謂朱子為《三字經》之先例」,但強調「其女雖非幼稚,究尚未學,故此文乃為初學而設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頁),而且反覆強調朱熹與啟蒙教育的關係。
的確,朱熹非常注重啟蒙教育,不僅曾編有《小學》和《易學啟蒙》,而且編寫了《童蒙須知》、《訓蒙詩百首》,他的《訓子帖》、《白鹿洞揭示》、《敬齋箴》、《滄州諭學者》、《論定董陳學則》、《朱子讀書法》、《孝經刊誤》等,舊時也曾用作啟蒙讀物。他有關傳統小學的論述,不僅確立了啟蒙教育的使命,而且為傳統社會後期啟蒙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奠定了基調。然而,將這篇為他女兒的墓誌而作的銘文,看作是「為初學而設」,看作是為童幼而作,則顯然過於牽強。銘是刻於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來稱述生平功德,使傳揚於後世。作為一種文體,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齊的形式寫成,如《大學》所載的著名的商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朱熹為自己早逝的女兒寫的墓誌銘,從內容來看,是為了使其生平懿德傳揚於後世,從形式而言,則合乎「銘」的文體,與啟蒙教育沒有什麼聯繫。
朱熹的學生陳淳,倒是實實在在地為啟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編寫了一部適合兒童的讀本。他編寫的《啟蒙初誦》,全篇完好無損地一直保存到現在。陳淳最初編寫時,依照傳統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為《訓蒙雅言》(《四庫全書》本此篇序言稱《訓童雅言》)。作者曾自敘其撰著經過:「予得子今三歲,近略學語,將以教之,而無其書。因集《易》、《書》、《詩》、《禮》、《語》、《孟》、《孝經》中明白切要,四字為句,協之以韻,名曰《訓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雖然說輯錄的主要是儒家經典中的語句,但都經過了作者較大幅度的改編。如述及孔子的部分這樣說:「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下學上達,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進禮退義,溫良恭儉,若聖與仁,為之不厭。宗廟便便,鄉黨恂恂,私覿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不正不坐,不時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從心所欲,無可不可。」
《訓蒙雅言》編成之後,作者「又以其未能長語也,則以三字先之,名曰《啟蒙初誦》,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後來被熊大年收錄在《養蒙大訓》中,並被改名為《經學啟蒙》。《啟蒙初誦》以三字句寫成:
天地性,人為貴,無不善,萬物備。
仁義實,禮智端,聖與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遠,君子儒,必自反。
學為己,明人倫,君臣義,父子親。
夫婦別,男女正,長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憤忘食,樂忘憂。
訥于言,敏於行,言忠信,行篤敬。
思毋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入則孝,出則弟,敬無失,恭有禮。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莊。
口容止,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
視思明,停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視,坐毋箕,立毋跛。
惡旨酒,好善言,食無飽,居無安。
進以禮,退以義,不聲色,不貨利。
通道篤,執德弘,見不善,如探湯。
不遷怒,不貳過,毋意必,毋固我。
道積躬,德潤身,敬日躋,新又新。
祖堯舜,憲文武,如周公,學孔子。
禮三百,儀三千,溫而厲,恭而安。
存其心,養其性,終始一,睿作聖。
這篇讀物主要講的是儒家的倫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複,可知它主要是作為教授倫理道德而編寫的,識字的目的並不突出。比起《三字經》來,內容也過於單一,由於主要是集儒家經書中的語句,儘管作者特別注意選擇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較古奧難懂。儘管如此,《三字經》對它的繼承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論,二者開篇都談論人性,並且觀點也完全相同。
從《三字訓》到《三字經》
在《三字經》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經出現。與朱熹(1130∼1200)同時的項安世(1129∼1208)曾說:「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禮記》之《曲禮》、《管子》之《弟子職》、史游之《急就篇》,其文體皆可見。」(《項氏家說》卷7)可見《三字訓》與《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樣,當時已經廣泛地運用於啟蒙教育。可惜《三字訓》現在已經佚失,我們不知道它的詳細內容。由項安世的述說可知,為了便於兒童的記誦,它整齊押韻;從書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寫成,而且,這樣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編寫形式相關聯。陳東原先生說《三字經》「當係元初人就《三字訓》改作」,只是一種推測,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實,但無論是編寫形式還是命名方式上,它無疑對《三字經》有重要的影響。
《三字經》是中國啟蒙教育傳統的結晶,它的出現,是傳統啟蒙教育長期積累的結果,從形式到內容,都有先例可循,就連它的名稱,也顯然是取法《三字訓》的結果。正因為植根於這樣豐厚的傳統,它才得以厚積薄發,成為傳統啟蒙教材最具標誌性和代表性的讀本。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50期】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159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