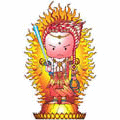再看一遍電影“悲慘世界”,取證“不再逃了!” (本篇電影欣賞心得轉自東山講堂通訊,作者:DY) 本期通訊電影欣賞,我們選了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原著LES MISERABLES 改編的電影,中譯“悲慘世界”或“孤星淚”。 片中主角一是:尚伐尚(由連恩˙尼遜LIAN NEISON飾演),他是個小偷,因為受善友的啟發而改邪歸正,後來作到受人尊敬的市長;但這樣的包裝,並無法使他不繼續帶著市長的身、囚犯的心繼續逃亡。如此恐懼害怕,躲躲藏藏,卻因為自己後來的一念善,扭轉了自心的恐懼。 一是夏維特(由喬福瑞˙偌西 GEOFFREY RUSH飾演),他是個看守所的獄吏,以執法嚴厲出名,當上警長後,因懲罰犯人的心無法理清,內心受到罪惡感壓力的反彈,而“寧死不屈”。 這個故事令我們產生許多幻相,從尚年輕時偷了麵包開始,引發這一連串的後果。因此我們有疑惑…為什麼人會起偷心?為什麼人會這麼嚴厲苛刻的待人? 一八一五年,這個時代的人心,對“貧富不均的不合理性”,調發了整體社會的成見偏見。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給自己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化”的生存之道,作為互動的標準。 於是窮人看到富人的奢迷,反應是:你們可享受朱門酒肉樂,而我卻快要餓死了,反正拿你些麵包也不犯死罪,再怎麼處罰總比現在餓死好吧!更何況你們富人橫行斂財弄來的富貴,也不見得光明正大,我拿你的也是替天行道。 富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就苛以嚴刑峻法,提防窮人來搶。 尚在監獄裡飽嚐煎熬後,發現這樣的逼迫太苦了,非逃不行。當他一心想出離苦的時候,就碰到了善人寬恕心的啟發。善友之善是因為能體現自利利他的身教言教,這樣美好的感覺,使尚決心不要做那個“只能藏在黑暗裡”的惡人,而要做個像善友一樣能惠利他人的人。因為心量的轉變擴大,不再只糾纏自己的小是小非,又發願服務更多的人,心地就更加光明善良起來,使命也跟著擴大,於是維果市的市長一職非他莫屬。他清楚的知道好好發揚善友之善,能寬恕能包容,就能令自己快樂,更能令市民快樂。 可是這樣的善還有“夾帶”,因為那個逃避“為自己的罪負責到底”的心還沒有建立;除非不再逃亡了,否則無論逃到哪裡,這個“前業未消”的恐怖罣礙心仍在作祟,走到哪將帶到哪。然而一次次的逃亡護身,就一次次的把心又帶回到囚犯的境界,為了自身的安適,不願再生起服務市民的願時,力感也跟著衰現,立刻就從市長之尊掉到囚犯之身,過去的苦惱全部回籠,尚又開始在逃亡的逼迫無暇裡求生,重拾地獄之苦。 直到心念一轉,記起當年善友的善時,他曉得再逃也沒有用,還不如老老實實回頭去面對心裡最恐怖擔心的事--死亡或坐監的苦,因為這樣的苦非得自己承擔不行,別人無法代受。 當我們的惡念不能停止的時候,很難去相信“作善獲福、為惡受殃”的真理,決不相信我只要能真誠的起善意,就定會有善的回應。佛陀慈悲的告訴我們,“不作諸業不得果報”,尚不斷的逃亡脫罪,甚至想“我努力的作到了市長總該沒事了吧!”但眼巴巴的看著夏還是緊追不放,這說明了什麼?偷竊者心裡的另一股力量在告訴他,他永遠得防著別人把他當小偷看!因此無論作善作惡,功不抵過,必然要自造自受。 警長為什麼最後要走上自殺一途?正是自己努力在當時小理小法的妄執上起了迴作力,自己制定的酷吏法,在執法的時候怎可掛一漏萬?否則罪可大了,罰了別人我就沒罪!但突然發現這個要護卻護不住的法,都要被自己破壞時,這麼嚴峻的心面臨了大考,能不處罰自己嗎? 無論我們做了什麼好事或壞事,我們都會盯著自己,用各種方法,即使自欺也行,要求自己為所作的事情負責到底,這一念不能不去計較,因為“我的使命”絕不可破壞。 當警長的計較心一起,就得死盯著囚犯不放:“一個囚犯若找到理由脫罪,我的法就要破產!警長還能當下去嗎?但市長卻可以這麼逍遙法外,自由自在,不受罪惡感的束縛!好像從來沒有當過小偷似的,難道他是來告訴我,只要他當上了市長大人,就可不計舊惡了?這是不對的!我從沒做過違紀犯法的事,卻要這麼緊迫盯人,我哪來的錯?” 憍慢邪見、嫉妒嗔恨心的造作,把人心帶往地獄,警長要為自己的“信念”負責到底,不願掉轉方向,就非得作地獄之行,那正是把己意己力膨脹、把小理小法當真理對待的果報。 當尚決心不再逃亡,一心面對“業果”的時候, 夏拿槍對著尚問:“你有機會殺我,為什麼不殺?” 尚答:“我無權殺任何人。” 夏問:“你是不是恨死我了?” 尚答:“我根本不恨你。” 夏問:“你是不是害怕再回到監獄裡去?”尚不吭聲,點點頭。 夏再說:“記著!我這一生從沒做過違法的事。” 夏解開尚的手銬,再把自己銬住,投河自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執著,正把自己帶進與真實對著幹的立場,然而“我只要懲罰了自己,就可將功抵罪了?”酷吏的心從此就沒了嗎?。 尚以為過不了這一關,但因勇敢誠實地打開心,面對真實,使得結果有了轉機。那正是以更大的善願化解惡業,功不可抵過,唯有願力方可令罪惡消弭,真理無有傷害,但把心量擴大,苦也減少了。 他們倆都為佛陀的真理“知死有生,作善獲福,為惡受殃,修道得道”作證,也就是修什麼道,得什麼道果。修偷竊法的道,得小偷的果;修酷獄法的道,得酷吏的果;修佛門正法的道,也必然得成佛的果。 我們看電影會習慣性的把人物劇情,分別成好事壞事、好人壞人,都想作一個評審員或者裁判官。於是惡人善人就以我的思維準則被定了性,電影的好壞於焉出籠,當“我認為怎麼怎麼樣”時,一切事務的真理性就因“己意己力”的障礙給摒棄了!就像囚犯與警長背後要說明的真相,叫我給覆藏起來了。“我與真理有緣或者無緣”,端視我是否思量善事或者惡事。佛陀的身教言教啟發我們了解“萬法由心造”、“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思量惡事化為地獄”。 一切世間的苦行苦受,本就是在為佛陀的真理(世間皆苦、自造自受、有慚有愧、離苦得樂)作證,如果這個心,只能處在罪惡感和委屈感的逼迫下,鬆不了油門、踩不住煞車、調轉不了車頭的話,是沒有辦法“離苦得樂”的,也就難免要見到“悲慘世界”,而不是“歡喜世界”了。
再看一遍電影“悲慘世界”,取證“不再逃了!”
(本篇電影欣賞心得轉自東山講堂通訊,作者:DY)
本期通訊電影欣賞,我們選了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原著LES MISERABLES 改編的電影,中譯“悲慘世界”或“孤星淚”。
片中主角一是:尚伐尚(由連恩˙尼遜LIAN NEISON飾演),他是個小偷,因為受善友的啟發而改邪歸正,後來作到受人尊敬的市長;但這樣的包裝,並無法使他不繼續帶著市長的身、囚犯的心繼續逃亡。如此恐懼害怕,躲躲藏藏,卻因為自己後來的一念善,扭轉了自心的恐懼。
一是夏維特(由喬福瑞˙偌西 GEOFFREY RUSH飾演),他是個看守所的獄吏,以執法嚴厲出名,當上警長後,因懲罰犯人的心無法理清,內心受到罪惡感壓力的反彈,而“寧死不屈”。
這個故事令我們產生許多幻相,從尚年輕時偷了麵包開始,引發這一連串的後果。因此我們有疑惑…為什麼人會起偷心?為什麼人會這麼嚴厲苛刻的待人?
一八一五年,這個時代的人心,對“貧富不均的不合理性”,調發了整體社會的成見偏見。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給自己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化”的生存之道,作為互動的標準。
於是窮人看到富人的奢迷,反應是:你們可享受朱門酒肉樂,而我卻快要餓死了,反正拿你些麵包也不犯死罪,再怎麼處罰總比現在餓死好吧!更何況你們富人橫行斂財弄來的富貴,也不見得光明正大,我拿你的也是替天行道。
富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就苛以嚴刑峻法,提防窮人來搶。
尚在監獄裡飽嚐煎熬後,發現這樣的逼迫太苦了,非逃不行。當他一心想出離苦的時候,就碰到了善人寬恕心的啟發。善友之善是因為能體現自利利他的身教言教,這樣美好的感覺,使尚決心不要做那個“只能藏在黑暗裡”的惡人,而要做個像善友一樣能惠利他人的人。因為心量的轉變擴大,不再只糾纏自己的小是小非,又發願服務更多的人,心地就更加光明善良起來,使命也跟著擴大,於是維果市的市長一職非他莫屬。他清楚的知道好好發揚善友之善,能寬恕能包容,就能令自己快樂,更能令市民快樂。
可是這樣的善還有“夾帶”,因為那個逃避“為自己的罪負責到底”的心還沒有建立;除非不再逃亡了,否則無論逃到哪裡,這個“前業未消”的恐怖罣礙心仍在作祟,走到哪將帶到哪。然而一次次的逃亡護身,就一次次的把心又帶回到囚犯的境界,為了自身的安適,不願再生起服務市民的願時,力感也跟著衰現,立刻就從市長之尊掉到囚犯之身,過去的苦惱全部回籠,尚又開始在逃亡的逼迫無暇裡求生,重拾地獄之苦。
直到心念一轉,記起當年善友的善時,他曉得再逃也沒有用,還不如老老實實回頭去面對心裡最恐怖擔心的事--死亡或坐監的苦,因為這樣的苦非得自己承擔不行,別人無法代受。
當我們的惡念不能停止的時候,很難去相信“作善獲福、為惡受殃”的真理,決不相信我只要能真誠的起善意,就定會有善的回應。佛陀慈悲的告訴我們,“不作諸業不得果報”,尚不斷的逃亡脫罪,甚至想“我努力的作到了市長總該沒事了吧!”但眼巴巴的看著夏還是緊追不放,這說明了什麼?偷竊者心裡的另一股力量在告訴他,他永遠得防著別人把他當小偷看!因此無論作善作惡,功不抵過,必然要自造自受。
警長為什麼最後要走上自殺一途?正是自己努力在當時小理小法的妄執上起了迴作力,自己制定的酷吏法,在執法的時候怎可掛一漏萬?否則罪可大了,罰了別人我就沒罪!但突然發現這個要護卻護不住的法,都要被自己破壞時,這麼嚴峻的心面臨了大考,能不處罰自己嗎?
無論我們做了什麼好事或壞事,我們都會盯著自己,用各種方法,即使自欺也行,要求自己為所作的事情負責到底,這一念不能不去計較,因為“我的使命”絕不可破壞。
當警長的計較心一起,就得死盯著囚犯不放:“一個囚犯若找到理由脫罪,我的法就要破產!警長還能當下去嗎?但市長卻可以這麼逍遙法外,自由自在,不受罪惡感的束縛!好像從來沒有當過小偷似的,難道他是來告訴我,只要他當上了市長大人,就可不計舊惡了?這是不對的!我從沒做過違紀犯法的事,卻要這麼緊迫盯人,我哪來的錯?”
憍慢邪見、嫉妒嗔恨心的造作,把人心帶往地獄,警長要為自己的“信念”負責到底,不願掉轉方向,就非得作地獄之行,那正是把己意己力膨脹、把小理小法當真理對待的果報。
當尚決心不再逃亡,一心面對“業果”的時候,
夏拿槍對著尚問:“你有機會殺我,為什麼不殺?”
尚答:“我無權殺任何人。”
夏問:“你是不是恨死我了?”
尚答:“我根本不恨你。”
夏問:“你是不是害怕再回到監獄裡去?”尚不吭聲,點點頭。
夏再說:“記著!我這一生從沒做過違法的事。”
夏解開尚的手銬,再把自己銬住,投河自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執著,正把自己帶進與真實對著幹的立場,然而“我只要懲罰了自己,就可將功抵罪了?”酷吏的心從此就沒了嗎?。
尚以為過不了這一關,但因勇敢誠實地打開心,面對真實,使得結果有了轉機。那正是以更大的善願化解惡業,功不可抵過,唯有願力方可令罪惡消弭,真理無有傷害,但把心量擴大,苦也減少了。
他們倆都為佛陀的真理“知死有生,作善獲福,為惡受殃,修道得道”作證,也就是修什麼道,得什麼道果。修偷竊法的道,得小偷的果;修酷獄法的道,得酷吏的果;修佛門正法的道,也必然得成佛的果。
我們看電影會習慣性的把人物劇情,分別成好事壞事、好人壞人,都想作一個評審員或者裁判官。於是惡人善人就以我的思維準則被定了性,電影的好壞於焉出籠,當“我認為怎麼怎麼樣”時,一切事務的真理性就因“己意己力”的障礙給摒棄了!就像囚犯與警長背後要說明的真相,叫我給覆藏起來了。“我與真理有緣或者無緣”,端視我是否思量善事或者惡事。佛陀的身教言教啟發我們了解“萬法由心造”、“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思量惡事化為地獄”。
一切世間的苦行苦受,本就是在為佛陀的真理(世間皆苦、自造自受、有慚有愧、離苦得樂)作證,如果這個心,只能處在罪惡感和委屈感的逼迫下,鬆不了油門、踩不住煞車、調轉不了車頭的話,是沒有辦法“離苦得樂”的,也就難免要見到“悲慘世界”,而不是“歡喜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