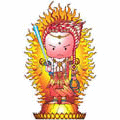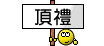頂果欽哲法王曾這樣稱許讚嘆創巴仁波切:
「他(創巴仁波切)是所有曼達拉之主;在外相的層次,他具體展現了三寶;
在內在的層次,他具體展現了三根;
在祕密的層次,他具體展現了三身,即證悟身。」
創巴仁波切著作
《自由的迷思》
登 極
一
父母是非常慈愛的,
而我太年少未能體會。
高原的崇山與深谷美麗無比,
未曾見過低地的我,何其愚昧。
二
努力汲取心靈的滋養,
淬礪智慧的劍鋒,
我尋得永恆的父母
令我再也難忘。
三
無人左右我的思想,
我顯露本我的自性
現出少年王子的風儀。
此皆唯一上師之賜。
四
我為利他之行而忙碌。
般若,穿透所有障礙,
將王子變成年老而睿智,
對任何人都無所畏懼。
五
躍舞太虛,
雲采為衣,
掌中握月,擷日為食,
星辰是我的扈從。
六
赤裸的孩子美麗且尊嚴。
紅花開滿天空。
可笑那不成樣的舞者,
隨著無人吹奏的喇叭起舞。
七
在紅寶石砌的宮殿裡,
聽著種子字的念誦,
幻想的舞蹈賞心悅目,
現象的迷人姑娘們。
八
無佩劍的戰士,
騎著彩虹,
充耳是超凡喜悅的無盡笑聲。
毒蛇變為甘露。
九
以火為飲,以水為衣,
緊抓著風的鬃毛,
吐納著泥土,
我是三界之君王。
一、自由的迷思
幻想與真實
若要將佛法根植在美國國土上,首先必須瞭解佛教的基本教義並學習基本的禪修方法。許多人將佛教當成可以拯救他們的一種新教派,可使他們處理世間事猶如在花園中摘花。但是我們若想從樹上摘花,必得先培育樹根與枝幹,也是就是說,必須先從自己的恐懼、挫折、失望與苦惱——人生的痛苦面——下手。
有人抱怨佛教是一極端沈鬱的宗教,因為佛教強調痛苦與悲慘;而通常宗教界愛讚美、歌唱、迷醉與極樂。不過尊照佛陀教示,我們必須先看清實際的人生經驗,必須瞭解苦的真諦以及不滿足的實相——我們不能當做沒這回事,而只顧研究人生榮耀與快樂的部分。如果我們只想找樂土、尋金銀島,這種追尋只會帶來更多的痛苦,我們也不可能以此種方式到達樂土、成就正覺。因此,佛教各宗派皆同意我們必須以面對生活真實情況為開端,不能先開始作夢。作夢只是暫時的逃避,不可能帶給我們真正的解脫。
在佛教裡,我們以禪修表示自己面對現實的意願。禪修並非為了追求迷醉、精神上的幸福或寧靜,也不是為了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而是為了創造一個空間,使我們得以在其中顯露並解除我們神經質的遊戲、自欺,以及隱藏的恐懼與希望。我們藉由什麼都不做的簡單訓練提供空間。事實上,什麼都不做大非易事。首先,我們從幾乎什麼都不做開始,然後逐漸求進步。禪修是先將自己心中的毛病翻攪起來,然後善加利用的修習方法。像處理糞便似的,我們不將毛病扔掉了事,而將之撒在花園中,使之增加我們的富饒。
在禪修時,我們既不可把心抓緊,也不能完全任由它去。如果我們試圖控制心,心的能量就會反彈回來;如果我們完全放任它,心則會變得狂野、混亂。因此,我們要將心鬆開,同時又對之有所規範,而佛教傳統上使用的方法非常簡單:感知身體的動作、呼吸以及自身狀況——這是所有教派通用之法。最根本的修行即住於當下,那是目的,也是方法;確切存在於當下一刻,既不壓抑也不放縱,而是如實覺知自己的存在。譬如呼吸只是自然的身體活動,並沒有精神上的內涵,我們僅留意它的自然運作即可——這就是所謂的修「止」(shamatha)。我們以修止開始步上小乘(hinayana)之道或窄道,這並非表示小乘的方法是簡化或狹隘的,反而因為心是如此複雜、詭異,時刻貪求各種逸樂,因此將心導入無岔路的紀律之途是唯一良策。小乘像是一輛不急駛的車,它平穩前進,絕無誤入歧途之虞,我們逃脫無門,身在車中無法下車——同時小乘這輛車也是沒有倒檔的。這種狹窄的單純同時帶來對生命情境的開放態度,因為既然明知無法脫身,我們唯有讓自己在現場安住下來。
於是,我們認知到自己的本來面目,而不再試著隱藏自己的問題與煩擾。禪修不該使你忘記在辦公室裡的承諾,事實上,在禪坐時你一直沒有與日常生活失去關聯。禪修是將我們的神經質提升至表面而非沈埋到心底,因為那使我們明瞭人生是可以經營的。我想有人會以為只要逃離日常生活的紛紛擾擾,他們就能在山中或海邊專心沈思冥想,殊不知逃離我們生活中的俗務,就如同捨棄夾在兩片麵包中間真正富營養的食物一樣——當你點三明治的時候,你不會只要兩片麵包,中間夾的那塊美味可口的東西,才是菁華所在。
對感情、生活現況及其週遭空間有了更真切的體認之後,可以為我們開展更全面的覺知。此時溫暖的慈悲心會油然而生——那是一種在基本上接受自我,而同時保留批判之聰慧的態度。我們可以同時欣賞人生喜樂與痛苦的兩面,因之處理情緒不再是大不了的事;我們如實了知情緒的存在,不加壓抑也不沈溺其中。因此,對細節確切的覺察,使複雜的整體情境得以展現,如同大河蜿蜒入海,紀律的窄小正所以導向覺知的全面開放。靜坐不單是以特定的姿勢坐在那裡專注於某些簡單步驟,我們同時也對產生這些步驟的環境敞開心智,此時,環境成為提醒者,不斷地提供訊息、教示與洞察力。
因此,在我們縱性於特異的技巧、能量的遊戲、感官知覺的遊戲與宗教象徵的幻象遊戲之前,我們首先須從基本上整理自己的心。我們必須在開上利益眾生的高速公路——大乘之道——之前,先練習走簡單的窄路——小乘之道;而唯有待我們在高速公路上走得平穩順暢之後,才能盤算如何到田野中奔躍一番——修習金剛乘或密續教法。以小乘的簡約為基礎,我們方能欣賞大乘的壯麗與密續的璀璨光采;因此,在我們想要登天之前,必須先踏實在地上,認真地對治我們的毛病。整個佛教的修行方法,目的就在開發我們超覺的知見,使能得見事物的本貌——不將事物放大或夢想成我們所希望的樣子。
失望
一旦我們走上許諾救贖、奇跡與解脫的精神之路,我們就被「靈性的金鎖鏈」(golden chain of spirituality)所繫縛。這條鑲嵌寶石、雕鏤精緻的鎖鏈,佩戴起來或許光采亮麗,但是我們卻被它牢牢拴住;如果有人以為佩戴鎖鏈只是裝飾而不必受其拘束,那是自欺之說。一個人若以充實自我為修行的出發點,那是修行上的唯物主義——一條自毀而非創造之路。
我們聽到的所有許諾都純是誘惑——我們期望佛法可以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有妙計高招讓我們用以解決自己的沮喪、瞋恚以及性的困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們開始明白根本不會發生這種事!我們失望地發現,沒有救主或修行法術的神奇力量可以依靠,反而必須靠著自己的努力來對付自己與自身的痛苦;我們也不得放棄所有期望,瞭解了不能憑自己的先入之見,繼續癡心妄想。
讓自己感到失望是件好事,那代表「我」與「我之成就」的降服。我們但願能看見自己得成正覺,看著弟子們為之慶祝、禮讚、向我們擲花,甚而天顯異象、地動山搖、諸天歡唱等等——但這種事永不會發生。若從自我的觀點來看:開悟是死亡之極致——自我之死亡、「我」與「我所」之死亡、觀看者之死亡,而且那是絕對的、終極的失望。修行之道是痛苦的,那是不斷地剝除面具,一層又一層地剝開,其中也包含著一而再的侮辱。
如此一連串的失望使我們放棄了野心。我們跌得越來越低,直到跌落地面、直到我們像大地一般清醒實在,我們成為低中之最低、小中之最小,猶如一顆沙粒,極為簡單,毫無期盼。在我們落地之後,夢想與享樂的衝動無處容身了,此時我們終於可以開始修行。我們學習如泡一杯好茶、如何安步直行而不東倒西歪,我們的生活態度變得簡單、直接,而任何我們聽到的開示、讀過的書籍,都變得可以應用,那成為對我們的肯定與鼓勵,我們正該像一粒沙般地努力——不抱期望,全無夢想。
我們聽過許多允諾,醉心於各種奇妙處所的描述,曾見過無數夢境,但是以一粒沙的觀點看來,這些我們全不在乎了——我們只不過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而已!而在此同時,我們的境況卻是非常開闊、非常美麗且大有可為的。事實上,那是既難得又充滿啟發的境界。如果你只是一粒沙,整個宇宙全部的空間都是你的,因為你既礙不著什麼,也擠不著什麼般地一無所有;你面對無垠的開闊,你是宇宙的君王——因為你是一粒沙。我們的啟示來自於沒有任何自我野心的失望,世界呈現出異常的單純,同時也極為尊貴、開放。
痛苦
我們以發問、以懷疑自己的虛偽開始我們的修行之道,期間會有不斷地對於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以及什麼是快樂、什麼是痛苦的迷惘。在人生的歷程中,我們時時刻刻、年復一年經驗這種迷惘,我們不停地發問,以致最後問題發酸、腐敗,它們變成了痛苦。當問題變得更具體,而答案卻更模糊時,痛苦也跟著增加。
當我們年紀漸長,終究會開始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們或許會說:「何者不是生命的意義?一切都是生命!」這種說法未免太過狡猾、過分聰明——問題依然存在。我們可以說生命的意義是存在的,但是為何而存在?我們活著是為了成就什麼嗎?有人說生命的意義是為了達成更高目標而付出心力:來往於地球與月球之間,或是達到證悟;成為了不起的教授、科學家、神秘學家以改善世界、清除地球的污染。或許那即是生命的意義——我們應努力以完成某項工作,我們應發掘智慧並與他人分享;或者,我們應建立更好的政治秩序,加強民主以期人人平等,使每個人都能在共同的責任限度之內享有充分自由;或許我們應將人類的文明提升至最高點,使我們的世界成為一個具有智慧、靈性、知識與極度科技發展的美妙仙境,在那裡有豐富的食物、優雅的住所、親切的同伴;我們應該變得有格調、富足又快樂,沒有爭吵、戰爭或貧窮,有高明的飽學之士,他們知道所有問題的解答——從水母怎樣開始形成直到宇宙如何運作……。
我全然沒有嘲弄這種心態的意思,但是,我們考慮過死亡的意義嗎?生命的反面即是死亡,我們曾否想過?連提到「死」都是痛苦的。如果你請你十五歲的孩子寫他的遺囑,人們會認為這簡直荒謬透頂,因為沒人會那樣做。我們拒絕承認死亡的存在,然而,我們最高的理想、我們對於生命意義的探討、人類文明的巔峰……,所有一切都是不切實際的——如果我們不去考慮由出生、受苦以至死亡的過程。
出生、痛苦與死亡,時刻都在發生。出生是進入一個全新的情境,緊接著是一分心曠神怡之感、一種清新,就像看清晨的太陽升起一般。鳥兒們睡醒開始歌唱,空氣清爽,我們開始瞥見樹與遠山朦朧的輪廓;當太陽出現之後,世界逐漸清晰地呈現出來。我們看見太陽越來越紅,最後成為耀眼的白色光華;我們渴望抓住黎明,抓住日出那一刻,使太陽不要完全升起,讓我們保有對光輝的展望。儘管我們希望如此,但卻無法辦到——從未有人做到過。我們雖奮力想要保持新境況,而終究什麼也掌握不住,直到死期來臨。在我們死時,死後與來生當中有一段間隔,然而那段間隔也充滿下意識的各種絮語——諸如究竟該怎麼做之類的問題;然後新的機緣會合,我們再次投生。我們一再、一再地重複著這種過程。
就此觀點來看,在你生小孩的時候,如果你當真要抓住生命,就不應該在嬰兒出生時去剪斷臍帶——但是你必須剪。「出生」,是嬰兒與母親分離的宣告,不是你見證孩子的死亡,就是孩子見證你的死亡。或許這是對生命非常冷酷的看法,然而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我們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出生、痛苦與死亡的一項表白。
在佛教傳統中,痛苦共分為三類:行苦、壞苦與苦苦。「行苦」是不如意、別離與寂寞等一般性的苦。我們很孤獨,我們無法再長出臍帶,也不能說我們的出生:「那只是預演。」那已是既成的事實。因此,只要有不連續與不安存在,痛苦就無可避免。
「行苦」是瞋恚導致的普遍挫折感,這與你是個有禮或粗鹵、快樂或不快樂的人全不相干。只要我們想抓住自己的存在,我們就會繃緊全身的肌肉來保護自己,這就引起不舒服,因而使我們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稍有不便。即使我們能夠自給自足,擁有大量的錢財、食物,有住所與同伴,仍免不了有這些小東西從中作梗,它們在我們不斷地保護與遮掩之下,仍然露出破綻。我們必須時時警戒以免出錯,但我們並不確定究竟怕出什麼錯;似乎有一種普遍性的共識:有某件事我們必須保密、某件事絕不能搞砸、某件難以言諭的事——那是非邏輯的,但對我們仍構成某種威脅。
因此基本上,不論我們多麼快樂,我們仍然謹慎小心並因此感到憤慨。我們並不真正想被揭穿、不真正想面對這東西——不管它是什麼。當然,我們可以試著將這種感覺合理化:「我昨夜沒睡好,所以今天覺得不大對勁;我不想做困難的事,因為我怕做不好。」但是這種自我開脫並不生效。擔心犯錯以致於造成自己的氣憤以及企圖隱藏。我們對於那些不想示人且難以言說的私密部分感到憤怒——「如果我能甩掉這東西的話,我就會輕鬆自在了。」
這種根本的苦以數不盡的形式呈現:失去了一位朋友的苦、必須攻擊一位敵人的苦、賺錢的苦、謀求證件的苦、洗碗盤的苦、擔負責任的苦、感覺有人在背後盯著你的苦、自覺不夠能幹、不夠成功的苦,以及各種人際關係的苦……。
「行苦」之外,另有感受自己正肩負重擔的「壞苦」。有時你感覺很自由,似乎重擔消失了,你不必再繼續支撐下去了。但是這種苦與不苦、神智清明與錯亂之間的一再變換,其本身就是痛苦的;再加上負荷重擔,更是苦不堪言。
最後就是第三類的「苦苦」。你已經缺乏安全感,對自己的地盤沒有把握;此外,便更因擔心自己的處境而胃潰瘍,在趕去醫生那裡治療的時候又撞傷自己的腳趾——抗拒痛苦只會增加其強度。
第三種苦,一個接一個很快地充滿你的生活。首先你感到基本的「行苦」,接著是變換的苦——從苦、不苦又回到苦,然後是「苦苦」——所有生活上的不如意之苦。
你決定去巴黎度假,盤算著可以盡情享樂一翻,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你的法國老友出了意外正住在醫院裡,他的家人都很難過,因此無法照你預期的那樣接待你,你只好改住旅館,可是負擔不起住宿費,你的錢很快就要花光了,於是你決定去黑市換錢但卻上了當;這時,你那出事住院的朋友忽然不喜歡你了,覺得你很討厭,你想回家又走不成,因為天候惡劣,所有的班機都停飛了——你真是絕望透頂。每小時、每秒鐘對你都很重要。你在飛機場來回踱步,你的簽證馬上到期,因此必須盡快離開法國,但最糟糕的是很難向機場官員解釋清楚,因為你不會說法語。
這種狀況是司空見慣的。我們恨不得趕快除掉自己的苦,但卻發現痛苦反而有增無減。痛苦是非常真實的,我們無法裝作很開心、很安全。痛苦是我們經常的伴侶,它們持續不斷——苦苦、行苦、壞苦;我們追求的是永恆、幸福或安全,但實際的生活感受卻充滿了疼痛與苦難。
無我
努力保障自己的幸福並維持與其他事物的關係,即是自我(ego)之過程。不過這分努力純屬徒勞,因為在我們看似堅實的世界裡不斷出現裂隙,有不斷的生死循環與持續的變易。我們對自我的連續與實在感,只不過是一種幻覺,實則並沒有自我、靈魂或阿怛摩(atman)這回事。自我是由一連串混亂產生的,自我的過程實際上包含稍縱即逝的迷惑、瞋恚及貪執——它們都只存在於那一瞬間。既然我們無法抓住眼前這一刻,當然也無法抓住我與我之所有,使它們成為堅實的東西。
自我與其他事物關聯之經驗,其實是短暫的偏見、稍縱即逝的念頭。如果我們快速產生這些飛逝的念頭,即會造成連續、穩固的錯覺;正像看電影一樣,個別的畫面很快地放映,會產生連續動作之幻象。所以,視自我及他物為實有、連續,只不過是我們構想的成見;而一旦有了如是想法,我們就操控自己的思想將之強化,同時唯恐有任何反證——正是這種對真相披露的恐懼,以及對無常的否定禁錮了我們。唯有接受無常,方能使我們有機會死、有空間重生、有可能將生命當成一種創造過程來欣賞。
瞭解「無我」(egolessness)可分二階段。在第一階段,我們須看清自我並非一實體,它是無常的、不斷改變的,是我們的觀念造成它看似實在的。因此,我們的結論是:自我並不存在。不過我們仍然規畫了一個微妙的無我觀念,仍然有一無我的監視者——一位與無我認同並確保其存在之監視者——而第二階段是看穿這種微妙的觀念並將監視者捨棄。因此,真正的無我並不具無我的觀念。在第一階段時,似乎有一個人在看著無我;到了第二階段,此人已不復存在。在第一階段,我們看出沒有固定的實體,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與他物相對的;而在第二階段,我們瞭解:相對觀念需要一個監視者盯著它、肯定它,這又引入另一相對的觀念——監視者與被監視之對象。
若說無我之存在是由於事物不斷變更,這論點未免過於薄弱,因為我們仍然將改變當成某種實存之物。無我並不僅是「因為事物是不連續的,所以我們抓不住任何東西」的觀念;真正的無我是連「不連續」也不存在,意即我們不應執著在「不連續」這一觀念上。事實上,並非「不連續」在運作,我們感到的不連續乃是不安全之產物——它只是個概念而已。任何對於現象背後或現象當中的「一體性」(oneness)觀念也莫不如此。
無我的觀念常被誤用,以致混淆了生、苦與死的真義。問題出在我們一旦有了無我以及生、苦、死的觀念之後,我們很容易自我娛樂或自我辯解地說:痛苦不存在!因為沒有「我」來感受;生與死也不存在!因為沒有人來做見證——這種說法不過是低劣的逃避現實罷了。空性的哲理時常被如下的解釋所扭曲:「沒有人來受苦,所以有誰在乎?如果你覺得苦,那一定是你的幻覺。」這純粹只是說詞、空話。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話,我們也可以這樣想想,但是當我們真正受苦時,仍能無動於衷嗎?當然不能!苦,可是比說說空話強烈得多的。對於無我的真正瞭解超越戲論的,拋開對無我的概念,方能使我們充分體驗苦、生與死,因為那樣才是除去了哲學的填襯。
要點在於我們必須放棄所有標準,所有關於是怎樣、又該怎樣的觀念,然後才有可能直接經驗現象的獨特性與其生動之處。我們會發現有無窮空間讓我們經驗事物、讓經驗產生並消失;運作發生在廣闊的虛空之中,無論是什麼運作——苦與樂、生與死等等——都不互相干擾,它們最豐沛的滋味從而被體驗出來。無論是酸、是甜,它們被如實、完整地品嚐,而沒有為了使之更可愛體面而添加的哲學裝點或情感色彩。
我們從未被生命的陷阱所困,因為時時存有創造的機會與即興創作的挑戰。諷刺的是,當看清並承認無我之後,我們可能發現受苦中含有福祐,無常涵蓋持續或永恆,而無我正蘊藏了實體所必需的土性。然而這種超脫的幸福、持續與存在,絕不是建立在幻想、觀念或恐懼的基礎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