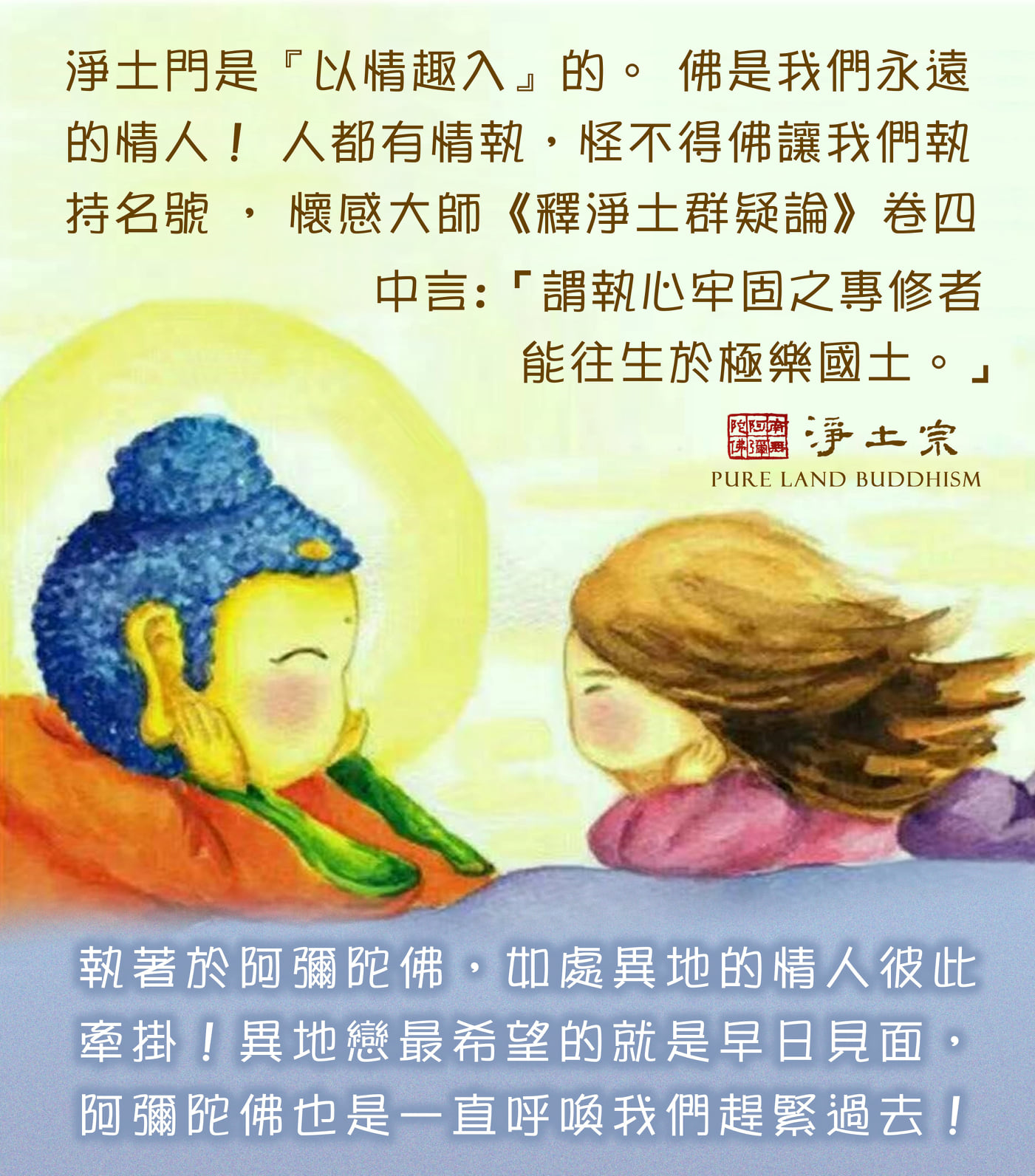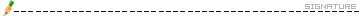作為一個文武兼備﹑曾經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歷史人物﹐曹操必然成為人們持久熱議的對象。有人讚美﹐有人唾罵﹐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只要稍微追溯一下淵源﹐便不難發現﹕關於曹操﹐早期的歷史文獻﹐大多還能比較客觀地進行評價﹐對他讚美有加者﹐不乏其人。到了趙宋時期﹐對於曹操的評價才開始發生嚴重的傾斜﹐亂世奸雄的形象遂成定格。
在西晉歷史學家陳壽(233-297)的《三國志》裏﹐曹操無疑是正面形象。《魏書‧武帝紀》中﹐有兩節文字﹐可以證明這一點。其一是說曹操青少年時期﹐橋(喬)玄﹑何顒能夠不為曹操“任俠放蕩﹐不治行業”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看到他的過人之處。其中橋玄對他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其二是﹐傳末的“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汁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南朝人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對曹操的態度也是比較客觀的。《識鑒》篇記載了橋玄對少年曹操的賞識和寄予厚望﹐文字比上引《魏書‧武帝紀》更加生動﹕“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其中﹐“治世之奸賊”﹐似乎不是好話﹐而實際上也是一種讚賞﹐不然﹐橋玄也不會願意把子孫托付給曹操。當然﹐《容止》篇也記載了曹操這樣一個故事﹕會見匈奴使者﹐曹操覺得自己形象欠佳﹐不足以震懾外國人﹐於是讓崔琰冒充自己﹐他本人手握大刀站在坐榻旁邊。會見結束後﹐讓人問匈奴使者﹕“魏王怎麼樣﹖”匈奴使者回答說﹕“魏王果然非常威嚴﹐但是﹐坐榻旁邊那個手握大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曹操聽後﹐立即派人殺死了匈奴使者。故事中的曹操固然狡猾﹑殘忍﹐但是﹐他這樣做﹐我們可以理解為﹐他是為了國家利益。於他個人品德﹑名譽並無多大損害。
現存文獻中﹐最早對曹操進行明顯詆毀的是《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東吳人的著作《曹瞞傳》。《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了如下一節《曹瞞傳》文字﹕
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餚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谷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谷﹐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顯然﹐這一節出自魏之敵國東吳人之手的文字﹐有污蔑曹操的嫌疑。
但是﹐南北朝隋唐時期﹐人們對於曹操﹐未見有多麼反感的言論﹐倒是有不少對他詩歌才華﹑成就的贊揚聲。例如﹐王僧虔有“魏氏三祖﹐風流可懷”(《宋書》卷十九《樂志》引)﹐鍾嶸有“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詩品》卷下)﹐元稹有“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從這種情況看﹐《曹瞞傳》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曹操形象的大壞﹐大約開始於宋代。蘇軾《志林》卷一“途巷小兒聽說三國語”條﹐引用王彭的話說﹕
途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可見﹐通達如大文豪蘇軾﹐都將曹操斥為小人﹐站在了“擁劉反曹”的立場上。後來﹐到大儒朱熹﹐更是破口大罵曹操是竊賊﹕
因說詩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雲“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雲﹕“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個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論文下》)
朱熹的話﹐無論是對學術界﹐還是對民間輿情﹐一定都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既然朱熹都這樣說了﹐曹操的竊賊高帽自然就如同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再也摘不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