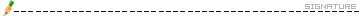為什麼中國古代宮廷樂舞”破陣樂”成為日本雅樂的保留節目?
《破陣樂》考
──兼論雅俗樂的交涉與轉化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沈 冬
摘要
關鍵詞:
引言
在中國音樂的歷史上,雅樂與俗樂的對立是極為鮮明的特徵之一,《新唐書》〈禮樂志〉曰:
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
因為「雅、鄭淆雜」,在官方音樂主事者的眼中,遂有了分別部類的需要,也因而形成了雅俗對立的局面[1],彷彿雅、俗樂是中國音樂裡兩個互不交涉,甚至相互對立的區塊,此疆彼界,畛域分明。承襲此種概念,歷代〈樂志〉更以分門別類的論述方式,連篇累牘地構築了兩者之間的圍牆。雅、俗之辨,不但成為音樂分類的基準,更是高下尊卑的指標[2]。楊蔭瀏先生在《中國音樂史綱》一書的結論裡,列出中國音樂史上的「四種衝突」,其一就是「民間音樂與宮廷音樂的衝突」[3],雅俗之樂,似乎如同「道」與「魔」之間的關係,此消彼長,方死方生,難有共存共榮的可能。
然而,雅、俗二樂真的是如此性質殊異,尊卑分明的兩種音樂嗎?卻也未必,撇開純然主觀名份尊卑的指涉[4],兩者主要的分別,與其說是音樂實質的差異,毋寧在於功能排場的不同,楊蔭瀏先生也提出:
雅俗二字的應用,完全是主觀而相對的。前朝所謂雅樂,後朝斥為俗樂,或前朝的俗樂,被後朝採用為雅樂,這是常有的情形。[5]
迥然不同於兩者在名義上的清楚對立,雅俗之樂的內涵相對地曖昧模糊,甚至雅樂與俗樂之間,始終不乏交互濡染而發生轉化質變的情形,前朝之俚曲,搖身一變,而為今世之古調。針對雅俗之樂的研究,如果一味執守於雅俗義界,嘗試於界定孰為雅樂,孰為俗樂,這種努力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但是,如果坦然接受雅俗之樂內涵的模糊多變,轉而試圖釐清其間交涉轉化的脈絡痕跡,並探索雅俗之樂如何在政治、社會、文化氛圍的影響與推動下,步出了原有的軌道,發生了轉化與質變,可能是更有意義或趣味的課題,也是本文的重點所在。
有唐一代是中國音樂的盛世,新靡絕麗之音,繁手淫聲之技,經由典籍文獻、圖像文物的紀載圖錄,使後人追摹意態,揣想風神,對於大唐帝國的音樂文化油然而生嚮慕之情。《破陣樂》一曲,被譽為唐代「第一樂曲」,擬之於「國歌」「國樂」[6]。此曲最早出現於唐高祖武德3年(620)前後,至晚唐懿宗咸通年間(860-869)仍有紀錄,綿延二百餘年;此曲又曾傳入吐蕃、天竺、日本,並保留樂譜於東鄰日本。《破陣樂》雖僅僅是一首樂曲,但其流傳的時間之長、空間之廣、變衍版本之多,為唐人稱述討論之頻繁,均非他曲所可比擬,因此本文選擇以《破陣樂》為研究對象。
在流傳變衍的各階段之中,《破陣樂》出現了不同的名稱,包括《破陣樂》、《秦王破陣樂》、《神功破陣樂》、《皇帝破陣樂》、《七德舞》、《破陣樂舞》、《小破陣樂》……等,為行文方便,本文一律以《破陣樂》為稱。
以單獨一首樂曲而言,唐代有關《破陣樂》的記載可稱詳盡,當然因為此曲的主角是百戰開基的唐太宗之故,但這些資料相互因襲者既多,音樂的描述也不充分,以致仍有若干疑點無法澄清。針對《破陣樂》的研究,任二北先生《教坊記箋訂》、《唐聲詩》,丘瓊蓀先生《法曲》、王克芬先生《中國舞蹈史》、王小盾先生《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等書均有論及,但以《破陣樂》一曲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文則較為少見,本文除了參考現存研究,並以《通典》、《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等資料為主,試圖釐清《破陣樂》的發展與變化,及其輾轉出入於雅、俗體系中的脈絡與意義。以下文分三節:第一節討論《破陣樂》的流變,共計析論了17個《破陣樂》的版本;第二節分析各個版本《破陣樂》的歌舞樂實況;第三節則討論《破陣樂》流變的意義。
一、《破陣樂》的流變
《破陣樂》的創作並非完成於一時一地,自其萌芽之初,就不斷經歷各種編配、重整,由草莽而趨典雅,由樸拙而趨華麗,逐漸發展成唐朝代表性的樂曲。仔細觀察,可以將《破陣樂》的演進分成以下五個階段:一、創作,二、燕樂化,二、雅樂化,四、法曲化,五、餘波。以下就此五個階段擇要析論:
(一)《破陣樂》的創作
《破陣樂》的創作,約在西元第七世紀前期、高祖武德年間,關於此曲的創作背景,史籍有如下說法:
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屢有征討,世間遂有此樂,(《舊唐書.音樂志一》,杜佑《通典》卷一四六略同)
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據此,任二北先生以為《破陣樂》有兩個可能的起源[7],然而參考《隋唐嘉話》的說法,則知後一說可能更符合情實,《隋唐嘉話》曰: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為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8]
《隋唐嘉話》的作者劉餗為著名史學家劉知幾之子,曾任史官,所著史籍被評為「有法」[9],其說應有相當可信度。但二說本無大太扞格,李世民輔佐其父李淵,南征北討,蕩平群雄,開創了李唐繁華天下,精準地說,《破陣樂》是為了慶祝討平劉武周而創作的作品,廣泛地說,此曲是歌頌太宗討伐群雄功業彪炳的作品。
在隋末唐初的亂局中,劉武周的勢力雄據西北,他倚附突厥,剽悍非常,曾敗齊王元吉,使得元吉棄弁州而逃,高祖武德3年四月(620),秦王李世民與其手下大將宋金剛的一場大戰,「日中八戰,賊皆敗,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10],「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日。」[11]劉武周從此遁入突厥,敗走不還,可以想見戰況慘烈,是李唐建國的一場關鍵性戰役,所以才有「河東士庶歌舞於道」的歡慶場面。當時軍士,或欣喜於殲滅大敵,或有感於秦王神威,因而創作了《秦王破陣樂》之曲。這一首歌曲的原作者是誰,當然已是無可究詰的謎,但它卻自然而然流行開來,所謂「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正說明了此曲最初的性質,猶如街陌謠謳、村坊俚曲,是一首兵卒軍士順口而歌的軍歌,足以使頑廉懦立,鼓舞士氣,這是《破陣樂》的原始版本。
(二)《破陣樂》的燕樂化
何以斷言《破陣樂》為「燕樂」[12]?因為它用於朝會享讌之中,這是《破陣樂》最主要的性質,其歷程始於貞觀元年(627)太宗即位之後。
貞觀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陣之曲》。(《舊唐書.音樂志一》)
及即位,宴會必奏之。(《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這是《破陣樂》進入燕樂之始。由「始奏」、「奏之」等描述來看,彷彿這是一首器樂曲,然而原始版本的《破陣樂》出自士卒之口,流傳行伍之中,分明是一首歌曲;同時,由日後魏徵等人「改製歌辭」(詳下文)的事實看來,也說明此曲原來有辭。然而此處的「始奏」又當如何理解?原版《破陣樂》既是流傳於軍中,本來只是單純質樸的「徒歌」,如今既然進入宮廷,施於燕樂,必須重加整編,配上器樂的伴奏,所謂「始奏」,就是這首重新編配,有歌有樂的《破陣樂》初次演奏,這是《破陣樂》進入燕樂的初期。
及至貞觀七年(633),《破陣樂》進一步擴大編制,成為歌、舞、樂合一的大曲。此事由太宗親自主導,史籍也有詳細的記載:
七年春正月戊子,……是日,上製「破陣樂舞圖」。(《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
以百戰開基之帝王,竟然親自為一首樂曲編舞,其間的意義非同小可,下文將有討論。經過整編的《破陣樂》大曲,由魏徵等人重製歌詞,歌曲中還加上了應和聲,最引人矚目的是場面浩大的舞蹈,由呂才教舞[13],一百二十位「披甲執戟」的舞者,以「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的戰陣形式,「來往擊刺」的肢體動作,表現「秦王破陣」的勇武神威,使觀者踊躍奮發,目眩神搖。
至此,《破陣樂》作為一首燕樂大曲,其主體已告創作完成。以樂曲的發展而言,此時的《破陣樂》如大樹一般,其主幹已然茁壯,此後必將開枝散葉,展現各種發展的面向和可能性,如果我們將這首燕樂大曲稱作「正體」《破陣樂》,此後還將有許多不同的「變體」《破陣樂》出現,其中屬於燕樂系統的有如下數種,以下分別論之:
1.九部伎《破陣樂》
貞觀14年(640)[14],「景雲現,河水清」的祥瑞出現,著名的音樂家張文收因而創作了《景雲河清歌》[15],其中第三部名為《破陣樂》: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采古《朱雁》、《天馬》之義,製《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杜佑《通典》)
所謂《朱雁》、《天馬》,都是與漢武帝有關的樂府歌[16],「朱雁」是天降祥瑞,「天馬」是大展國威。張文收用此二典,不但表達了頌聖之意,也隱含了對於盛世帝國的期許和祝願。《景雲河清歌》分四部:其一《景雲舞》、其二《慶善舞》、其三《破陣舞》、其四《承天舞》。究竟此一《破陣舞》與燕樂大曲《破陣樂》關係如何?異同如何?均無可究詰,但此曲舞者僅四人,以「綾袍,絳褲」為舞衣,即此一端,可知與燕樂大曲的《破陣樂》大不相同。此曲是否為張文收個人獨創?抑或是取用了「正體」《破陣樂》部分或全部的旋律主題?丘瓊蓀先生認為此曲與「法曲」中的《破陣樂》關係密切[17],似以為這是全然另一首曲子,恐也未必。《破陣樂》為盛世帝國的代表,太宗功業威名的寫照,如果張文收另起爐灶創製新曲,是否敢於「剽竊」《破陣》之名?既以《破陣》為名,如果曲調旋律一無關係,不必千年以下,當時必然已引起朝中上下的質疑。何況《讌樂》四部曲中,除了《破陣舞》之外,《慶善舞》也是唐太宗時創製的重要樂舞[18],與《破陣樂》、《上元樂》同被列為唐代「三大舞」;張文收的《讌樂》既取用了太宗時期最重要的兩首樂舞之名,如果說其音樂與原來二曲毫無關係,是很難令人置信的。
2.立部伎《破陣樂》
坐、立部伎是唐代宮廷樂舞編制的一種,早在高祖時,已有坐立部伎的分別,最清楚的例證是1973年陝西三原縣李壽墓石槨內壁發現的線刻樂舞圖。圖中有坐姿、立姿兩組女樂的線刻圖像。李壽是唐高祖李淵堂兄,死於貞觀4年(630),可知唐初已有坐、立部的區分[19],不過,制度的形成還要到唐玄宗時期,所以《新唐書.禮樂志》將坐、立部的設置歸功於唐玄宗:
(玄宗)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新唐書.禮樂志十二》)
以李壽墓線刻樂舞圖來看,推想坐、立二部經歷了長期的發展,至唐玄宗時終於定為制度,列明曲目。《兩唐書》、《通典》所列曲目,應是以玄宗定制為樣本,所以其中才有成於玄宗時期的《龍池樂》、《小破陣樂》等曲出現。
立部伎的曲目,史籍所載為以下八曲:
今立部伎有《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光聖樂》,凡八部。(《舊唐書.音樂志二》)
其中第三部《破陣樂》、第八部《大定樂》,都與燕樂大曲《破陣樂》相關。由史籍所載,第三部《破陣樂》和燕樂大曲的《破陣樂》一脈相承,依舊是百二十人披甲執戟的排場。我們無從得知此曲在完整的立部伎演出中如何呈現,但在天寶年間(742-755)卻有相關而有趣的演出記載:
◎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丸劍角抵,戲馬鬥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鄭處誨《明皇雜錄》,《唐代叢書》初集)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樂,若讌設酺會,即御勤政樓。……太常大鼓,藻繪如錦,樂工齊擊,聲震城闕。太常卿引雅樂,每色數十人,自南魚貫而進,列於樓下。鼓笛雞婁,充庭考擊。太常樂立部伎、坐部伎依點鼓舞,間以胡夷之伎。……又令宮女數百人自帷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雖太常積習,皆不如其妙也。(《舊唐書.音樂志一》)
◎後賜宴設酺,亦會勤政樓,……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宮人數百衣錦繡衣,出帷中,擊雷鼓,奏《小破陣樂》,歲以為常。(《新唐書.禮樂志十二》卷二十二)
以上三條資料,所記述的應是同一個場合,就是玄宗在勤政樓「賜宴設酺」的場景,在這場君民同歡的戶外表演裡,有坐立部伎、胡夷之伎,以及舞馬等表演,已是聲色動人,熱鬧無比,但最後還安排了壓軸節目,身穿錦繡的宮女數百,自帷幕裡突然現身,擊大鼓,奏《破陣》、《太平》、《上元》等曲。由曲目來看,都是立部伎的樂曲,也是太常寺樂工本色當行的曲目,但即使是太常寺老樂工都甘拜下風,自歎不如,可見這些宮女水準之高[20]。此一表演省略了「披甲執戟」、「往來擊刺」的舞蹈,將歌舞樂合一令人眼花撩亂的表演還原為單純的音樂。我們不知道這是否是玄宗的親自安排,然而以酷好音樂的皇帝而言,無疑此種表演方式才能打破燕樂演出時繁複儀制的拘束,也才更能展現樂曲的藝術性。
另外一曲《大定樂》也值得深究;《大定樂》為高宗時創作的樂舞,此曲確乎為《破陣樂》的變體。《舊唐書.音樂志二》曰:「《大定樂》,出自《破陣樂》。」此曲的創作時間,史籍有如下記載:
帝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高宗時代曾屢次征代高麗[21],對高麗的戰事時斷時續,幾乎不曾停止,但如果以高宗在東都洛陽來推判,則有可能是顯慶五年(660)、龍朔元年(661)之間,
據《新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五年十二月,高宗前往東都洛陽,命蘇定方等人伐高麗,次年龍朔元年四月正式進軍[22]。《大定樂》的創製有可能在此時。《資治通鑑》曰:
(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上與群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通鑑》卷二○○〈唐紀十六〉,頁6323)
確定這是龍朔元年(661)的作品;猶如《破陣樂》為太宗彪炳戰功的象徵,《大定樂》則為高宗勛業的表述,此曲的創作理念、樂舞設計均與《破陣樂》有密切關係,並流露了高宗子繼父業的強列企圖與矛盾心情,這點下文仍有討論。
3.坐部伎《破陣樂》
坐部伎曲目有六:
坐部伎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新唐書.禮樂志十二》
這六部曲之中,也有兩首《破陣樂》,其一是《讌樂》中的《破陣樂》,上文已經論述,但《舊唐書.音樂志》特別提及「此(《讌樂》)樂惟《景雲舞》僅存,餘並亡。」似乎在坐、立部制度成熟的唐玄宗時期,《讌樂》中的《破陣樂》已經不存。其二是第六部《小破陣樂》,顧名思義,此曲正是燕樂大曲《破陣樂》的「變體」:
《破陣樂》[23],玄宗所造也。生於立部伎《破陣樂》。舞四人,金甲冑。
這首《小破陣樂》為玄宗所作,根據的是立部伎的《破陣樂》,追本溯源,其本尊始祖還是唐太宗時的燕樂大曲《破陣樂》。立部伎的《破陣樂》演出時一百二十名舞者「甲以銀飾之」(《舊唐書.音樂志》),《小破陣樂》則四名舞者以「金甲冑」而舞,可見規模縮小,但形象更為精緻。《小破陣樂》的創作時間並無可考,但可能在玄宗即位之初,《新唐書.禮樂志》載:
是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24](《新唐書.禮樂志十二》)
由「其後,河西節度使……」云云,可知至少在開元年間(713-741)《小破陣樂》已經製成,因為楊敬述獻《霓裳》的時間正是開元中[25]。由「是時,……,帝又……」這種上下文的連屬看來,似乎《小破陣樂》、《文成曲》的製作,在《夜半樂》、《還京樂》之後不久。這四首樂曲以更迭輪奏的形式演出,其組合別具深義。玄宗由潞州別駕任上罷官還京,「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26],誅韋后,鏟除韋、武兩家勢力,奉其父李旦為帝,李唐皇權由此勃興,因而民間有《夜半樂》、《還京樂》,表達對少年李三郎的崇拜,此種情形一如最早的《秦王破陣樂》的創作背景。四曲聯奏,《夜半樂》、《還京樂》代表了萬民擁戴之誠,《小破陣樂》歌頌殲滅元兇巨憝之功,《文成曲》則稱美文治。四曲恰恰表彰了玄宗少年誅除韋武,安定唐室的功業。
4.雜曲中的《破陣樂》
崔令欽撰寫《教坊記》,著錄盛唐玄宗時教坊所用曲目,共計大曲46首,小曲278首,其中也有兩首《破陣樂》的「變體」,一是第17首《破陣樂》,另一是第245首《破陣子》,這兩首樂曲必然出自《破陣樂》,但與上述各曲關聯如何,已經無從考查,僅能附列於此。不過可以注意的是,《教坊記》裡的《破陣樂》並不在大曲之中,當然這不代表太宗的燕樂大曲《破陣樂》已經不傳,但至少說明了盛唐教坊並不表演那首「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的燕樂大曲。至於《破陣子》,即是後來李煜所倚詞調「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更是小曲的形式,是由歌兒舞女啟朱脣,發皓齒,拍按香檀,在酒筵歌席之間演唱,與原來《破陣樂》必有極大差異。這兩曲已經脫離了原來燕樂的儀式性,成為純粹的音樂賞美、怡情悅耳之用,遺憾的是,它的音樂實況均已無法探究了。
(三)《破陣樂》的雅樂化
雅樂與燕樂有何不同?一言以蔽之,雅樂是祭祀用樂,用於祭祀天地山川人鬼,「音樂充當著天人溝通的媒介,主要的功能是悅神娛鬼,而不是取悅活人。」[27]而燕樂則用於朝廷饗宴之中,雖然也不乏繁複的儀節,但主要目的在於上下同歡,娛賓遣興。《周禮》〈春官.大宗伯〉論大宗伯所掌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吉禮事邦國之人鬼神祇……,以嘉禮親萬民。」正可以用來對照說明雅樂、燕樂的分別。
何以斷言《破陣樂》為雅樂?因為它曾用於郊廟祭祀之中。這一段雅樂化的歷程始於唐高宗李治在位的時期。麟德2年(665),《破陣樂》被「提昇」為雅樂,成為郊廟用樂:
麟德二年十月,制曰:「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韜而未伸。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被甲執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並於縣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別設。(《舊唐書.音樂志一》)
音樂的功能,是為了「紀功旌德」,因此「先朝之樂」必須特加表彰,為了推崇太宗功業,高宗下令於麟德2年(665)下詔,文舞改用《慶善樂》,以紀念太宗降誕之地,武舞改用《破陣樂》[28],以歌頌太宗百戰開基。進入雅樂的《破陣樂》,規模更加堂皇,舞者依舊「披甲執戟」,並增加了樂隊「簫、笛、歌、鼓」等編制,而最大的特色,是與宮懸合奏,合鐘磬而歌舞,點明了《破陣樂》此時的雅樂身分。
然而,《破陣樂》進入雅樂,在實際施用上頗有窒礙,自高宗麟德2年(665)至儀鳳2年(677),整整12年間,所謂《破陣樂》用為雅樂,不過是官樣文章,陽奉陰違,終於引起太常少卿韋萬石的批評[29],儀鳳2年十一月六日,韋萬石奏曰:
奉麟德二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器服等。自奉敕以來,為《慶善樂》不可降神,《神功破陣樂》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猶依舊,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者。(《舊唐書.音樂志一》)
原來自高宗下詔以來,《慶善樂》與《破陣樂》始終未曾真正進入雅樂之中,有司不過更改了樂舞的服飾,至於樂舞的本身,「迄今不改」,這種名實不符,顛倒錯亂的情形必須有所處置,於是高宗再次下詔:
舊文舞、武舞既不可廢,并器服總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作。(《舊唐書.音樂志一》)
《上元舞》是高宗所製樂舞[30],此曲在著成之初,就同時用於雅樂和燕樂之中,所以立部伎有之,「祠享」亦有之。上元3年(676)[31],高宗下詔,減少《上元舞》用於雅樂的機會,僅限於祭祀「圓丘、方澤、太廟」而已[32]。在此,針對韋萬石提出來的問題,皇帝解決的方法如下:一、《慶善》、《破陣》不再用為文舞、武舞,恢復使用原來的《治康》、《凱安》,包括原來有司更改服飾器用以魚目混珠的作法也一律取消,恢復原貌。二、凡是使用《上元舞》的祭祀,也同時加入《慶善》、《破陣》二舞,所指應是祭祀「圓丘、方澤、太廟」的場合。三、在《慶善》、《破陣》、《上元》三舞演出之時,為與雅樂有所區隔,因此舞者的表演場域是宮懸之外[33]。
此一安排,在唐代音樂史上有其重要的意義,亦即確立了所謂「三大舞」的概念。史籍有如下記載:
唐之自製樂凡三: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七德》即是《破陣樂》、《九功》即是《慶善樂》。事實上,唐代自製樂舞當然不止於這三首,如前文所述《大定樂》、《讌樂》、《小破陣樂》,以及坐立部伎中各個曲目,也都是唐人自製,特別標舉「三大舞」,說明此三曲在唐代宮廷音樂裡的重要性,並且形成特殊的表演慣例,成為唐代代表性的樂舞,這是高宗試圖將《破陣樂》雅樂化而獲致的意外成果。
(四)《破陣樂》的法曲化
何以斷言《破陣樂》為法曲?有如下三條證據:
◎太常梨園別教院,教法曲樂章等:《王昭君樂》一章、《思歸樂》一章、《傾盃樂》一章、《破陳樂》一章、《聖明樂》一章、《五更轉樂》一章、《玉樹後庭花樂》一章、《泛龍舟樂》一章、《萬歲長生樂》一章、《飲酒樂》一章、《鬥百草樂》一章、《雲韶樂》一章。十二章。(《唐會要》卷三十三〈諸樂〉)
◎按法曲起於唐,謂之法部,其曲之妙者有《破陣樂》、《一戎大定樂》、《長生樂》、《赤白桃李花》。……(《樂府詩集》卷九十六〈法曲〉序)
◎漢祖過沛亦有歌,《秦王破陣》非無作。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元稹《新樂府.法曲》,《全唐詩》卷四一九,頁4617)
根據以上三條,應能肯定法曲中確有《破陣樂》一曲,此曲必然是李三郎的手筆,但如何製成?來源如何?均無從考查,丘瓊蓀先生認為法曲《破陣樂》可能來自於張文收《讌樂》[34],但未獲實證。因為法曲是唐代音樂中藝術性極高的一個樂種,我們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此一法曲《破陣樂》應有相當的音樂之美,其餘則僅能闕疑。
(五)餘波
經歷安史之亂一番天崩地坼的變動,盛唐以後,《破陣樂》仍然不絕如縷,間有記載,德宗貞元14年(798),有「初奏《破陣樂》」的紀錄[35],應是盛唐喪亂之後,試圖恢復國威的一種嘗試。此後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時機下偶有演出,如憲宗元和年間,白居易曾在觀覽之後為詩識之,即是《新樂府》中的〈七德舞〉[36]。敬宗時,曾有妓女石火胡其人,將《破陣樂》作為雜技表演的背景音樂,踏著《破陣樂》的節奏,「俯仰來去,越節如飛」[37]。懿宗時,藩鎮也曾紛紛舞《破陣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