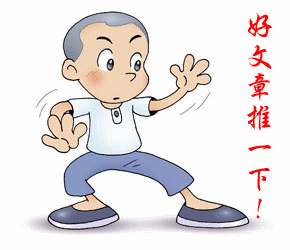方綺 「阿媽走了。」深夜裡,阿爸來電,聲音哽咽。
連夜搭車南下,車窗外一片漆黑,黑暗中,那張布滿風霜、歷經滄桑的面龐竟清晰浮現在我眼前,直到眼角滲出淚水,才逐漸模糊…。
出生在六○年代的台灣偏遠鄉村,病苦必定與貧窮緊緊纏結在一起,像一張蜘蛛網,盤據住一個家庭,從這個角落擴延到那個角落。身染癆病的阿爸鎮日躺在陰暗的小屋,不時傳來陣陣劇咳聲。受不了貧、病拖累的阿母,終於狠心丟下病弱老小,遠離家門。一家的重擔,全落在瘦小的阿媽肩上。每天,天色微暈,阿媽就推著一輛破舊的嬰兒車出門,巡街掃巷撿拾一些可以賣錢的破銅爛鐵。
這是我的童年記憶,記憶中蘊藏著童年時期對貧窮的自卑與憎惡。
從小,我就覺得自己不如人。一個不能賺錢的阿爸,一個撿拾破爛賴以持家的阿媽,這樣的家庭組合讓我感到卑微,我總覺得在別人面前拾不起頭來。
國中時代,是我自尊心作祟最強烈的時期。我幾乎成了自閉症,從不與同學往來,怕同學了解我的狀況、知道我的家人,尤其是阿媽,她的謀生方式簡直令我羞恥。
平日,最怕與撿破爛的阿媽在街頭巷尾不期而遇,那蓬鬆的亂髮、滿臉的塵垢,乍看之下像是瘋婦一般。有一次,我與阿媽在街口偶遇,她親切的召喚,引起路人對我行注目禮。
當下,我覺得難堪極了,紅熱的臉,像被一塊燒紅的鐵烙印上,灼痛不堪。從此,老遠見到阿媽的身影,我便閃到另一條巷道,深怕面對阿媽熱絡的眼神,大庭廣眾之下,阿媽的臉,成了我的夢魘,彷彿是惡魔的猙獰面貌,令我厭惡、害怕。
有一次,老師要到家裡做家庭訪問,我心中緊張極了,怕長期以來建構的帷幕一下子被揭露了。當天,我在約好老師來的時間,刻意支開阿媽。偏偏,就在老師訪談結束準備離去之際,阿媽突然推著嬰兒車出現在門口,車上一大堆廢紙、鐵罐。
「妳是?…喔!老師喔!阮是伊阿媽啦,進來厝內坐啦!」阿媽熱情地招呼老師,一旁的同學卻露出訝異的表情:「原來她就是妳的阿媽呀!」彷彿沈積已久的謎底,終於答案揭曉。那眼神,是驚訝、是嘲弄、是…頓時,我覺得受到極大的羞辱和傷害。
送走老師後,我衝進小院,將阿媽的嬰兒車翻倒在地,憤怒地將滾落地面的鐵罐踢得鏗鏘價響,瘋狂咆哮著:「為什妳是撿破爛的?為什麼妳要這個時候回來?為什麼妳要讓在同學面前丟臉?…」
當下,阿媽愣住了,眼睛眨了眨,隨即蹲下身去撿拾散落一地的廢紙、瓶罐。
阿媽的淚,一滴一滴落在塵土上,不發一言。
國中畢業後,我離家住校,靠著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大學學業。那段日子我親身體會到經濟窘迫時的難耐,終於理解阿媽對金錢的迫切與拾荒的無奈心情。
大學畢業,有了穩定的工作,經濟獲得改善,我總是將大部分的薪水寄回家,希望阿媽不必再為生活奔波。不止一次勸阿媽不要再去撿破爛,阿媽卻說:「有什麼不好?當作是運動,老人仔需要活動筋體,才不會生病。」
起初,我實在不能理解阿媽的固執。直到有一次,我與阿媽上街,阿媽看見一個鋁罐,本能地彎下腰去,卻被我用力拉住。我看到阿媽的眼神從原先乍喜的光彩轉為暗淡。我終於明白一件事:「撿拾」已成為阿媽生活的一種慣性,即使經濟無虞,在她的深層意識中也潛藏著一份莫名的執著,是一種苦樂交雜的情懷。理解了阿媽的心境,我不再堅持要求阿媽改變什麼。
去年,我帶著男友回南部老家,在車站巧遇阿媽。
「阿媽!」我高聲喊她,阿媽回首,滄桑的臉龐露出欣喜。她佝僂的身子依附著那輛嬰兒車,兩者之間,彷彿是難以分割宿命。
當她看見我身旁的男友時,笑容突然僵住了,神色緊張,結結巴巴地說:「阮…阮不是伊媽啦!」
望著阿媽慌張的神情,我的眼眶立刻充盈著淚水。童年的記憶像一把利刃,同時戳向阿媽和我的心房。我上前摟住她的肩,親熱地對她說:「妳不是我阿媽,是誰的阿媽?」阿媽看著我,又看了男友一眼,她笑了,笑中閃爍著淚光。
夕陽餘暈映照著阿媽銀灰的亂髮和布滿皺紋的臉,黑黝的臉龐映出油亮的光彩。阿媽笑別了嘴,露出沒有門牙的牙齦,那燦爛的笑容真美,恰如絢麗的晚霞。
那是一張動人的臉;一張堅持、固執,不向環境低頭認輸的臉;一張刻劃著艱辛歲月,卻無怨無悔的臉。
南無阿彌陀佛,願對大家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