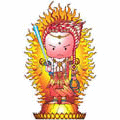蕭平實說:佛性須以眼見為憑,……見性應以肉眼親見佛性為憑,……「佛性非天眼所能見」除系依佛語外,亦依實際證量而言。我會中同修亦有得天眼者,受菩薩戒後隨余修學六月,終未能見佛性,復回神道教中。若不學大涅槃經,而雲天眼能見佛性者,無有是處。 答: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知,有些人可能連一些基本的佛法名相都未能搞明白,在這種前提下還要沐猴而冠、好為人師,處處以佛教權威解釋者的面孔自居,就實在是有些不倫不類、勉為其難了。 一般而論,肉眼有兩種解釋:一是指凡夫的眼根,二是謂「五眼六通」中「五眼」之一的肉眼。《金剛經》中曾提到過所謂的五眼,其中就包括了肉眼與天眼。《現觀莊嚴論》第一品中就有涉及「五眼六通」的內容(很明顯,蕭先生是把五眼與六通的功德混為一談了。);第二品教言品中則專門從因、作用範圍、類別等幾方面解釋五眼。此論以教量抉擇道:資糧道之菩薩開始具有肉眼,資糧道以上之菩薩相續中都具足。而別的一些論典中則具體闡釋道:肉眼是在加行道時通過供燈、修等持而獲得的,依靠肉眼可以現見一百由旬到三千大千世界整個世間內的方方面面。 儘管在敘述上略有差別,但一般而言,佛教經論基本上公認:天眼的功德遠遠超越肉眼。一些論典中認為修禪定等六度才是具足天眼之因,憑天眼可以照見十方所有眾生前生後世、投生受生的具體情況。依道地而論,加行道以上的人相續中方才具足天眼之功德,此功德通過修持有漏善法而獲得。 若按照以上標準來衡量,則蕭先生會下一具足天眼者卻無法眼見佛性,唯有具足肉眼者方能眼見佛性,則天眼、肉眼之順序豈非要前後顛倒?一般而論,得天眼者若具足肉眼,(按次第遞進之規律,這是必然的。)則他必能見佛性;若不具足,則他是否如《楞嚴經》中阿那律所言:「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 如果蕭先生所謂的「肉眼」非是「五眼」中的肉眼,那麼我們就只能把此處的肉眼理解成是普通凡夫的眼根了。若真是這樣的話,那他論點中的漏洞就更大。儘管他本人在《護法集》中曾引用過《大般涅槃經》中的幾句話(見一百七十一頁),但不知他看過沒看過,或者說理解不理解此經卷八中的這一句話:「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雖然經中亦有迦葉菩薩問佛:「佛性微細難知,雲何肉眼而能見?」佛對此回答道:「聲聞緣覺信順如是大涅槃經,自知己身有如來性,亦復如是。」但此處重點宣說的根本就不是以肉眼見不見佛性的問題,而是通過「信順」佛語從而堅信自身有如來藏的問題。 此經文明示:眾生皆具佛性,然佛性細微難察,凡夫位不見,有學道時以誠信而可了達其總相。十地菩薩亦只是片面了知,唯佛陀才能以具備如所有智、盡所有智之佛眼洞見佛性。倘若依此而認為肉眼可看見佛性,則此實為錯謬之談,因經中明確告訴我們:聲聞緣覺依此經而起勝解,並信受自身具有佛性之說。否則的話,應將經文改成「自見己身有如來性」了。 再者學過因明、唯識、俱捨的人都知道,肉眼所見之對境為色塵,而佛性乃無為法,絕對不可能被色法涵蓋。假若佛性真的可以依肉眼見之,那麼請問它的長短、大小、形狀、顏色又如何? 憨山老人在《<金剛經>決疑》中也曾提到過五眼的問題,他對此的解釋是:「空生疑佛具五眼,將謂有法可見,有世界眾生有情。世尊告以所具五眼非眼也,但約見眾生心為眼爾。」藕益大師在《<金剛經>破空論》中亦云:「夫五眼者,能照之知見也。」從中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裡所說的「眼」哪裡是指肉眼!這五眼均為眾生本具之功德,通過信解佛經、努力修持、戒定慧次第升進,一定可以將之顯發出來。若把經中所言的眼見佛性理解成肉眼見佛性,只能說持此說者混淆了五眼與六通、肉眼與五眼及「心眼」、照與見之間的界限、關聯。《涅槃經》中對此說得非常明瞭:「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瞭;佛眼見故,而得了了。」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不論是肉眼、天眼還是慧眼,都無法「眼」見佛性,只有佛眼才能將之了了分明地一覽無餘。 為了掩蓋自己論點中的致命缺陷,蕭先生又在別處提出所謂的「綜合肉眼說」。即他認為眼見佛性之眼除了包含眼根外,尚綜合了從心到如來藏一系列器官、心意識乃至佛性等或精神或物質或超離言說的種種實體與非實體之活動、功能。這種論調依然掩蓋不了其本質上的錯誤,一個非常淺顯的反駁理由是:在「綜合肉眼見佛性」說中,肉眼發揮不發揮根本作用?如果發揮根本作用,則我們已在上文破斥過此種觀點;如果肉眼不發揮決定性作用,那麼僅以肉眼結合如來藏為例,如此說成立,則有如來藏自己見自己之過。如來藏在什麼樣的對境下可以見到如來藏?肉眼見不到佛性,佛性自身也無法見到佛性,以此理推之,人人手中都沒有一分錢,這樣的人即就是湊足一千個,依然湊不出一分錢。「綜合見性說」的漏洞也就在這裡。 另一方面,根據《俱捨論》的觀點,眼識的產生需要具備三點條件:外境、眼根以及作意。剎那間具足這三點,隨後眼識便告產生。如果如來藏要見如來藏的話,那麼它又是如何作意的?最後再強調一點以正視聽:按照因明的觀點,五根識皆為現量親見、親聞、親觸等,若肉眼能見,當為現量了了而見。但佛陀在經典中早已說得清清楚楚,十地菩薩都不可能現量了了親見佛性。既如此,凡夫雲何得以憑肉眼就親見佛性? 既無教證,也無理證,看來我們又得問一句老話了:這到底是在闡發經義,還是在大肆宣揚自己的分別念?
蕭平實說:有謂《大智度論》所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為中道。」,乃是說緣起性空,謂緣起性空即是中道。然而此種解釋乃依二乘法而解釋龍樹菩薩之中道,實非中道,何以故?以緣起性空所顯一切理,皆依有為法之現象界而言;現象界之一切有為法悉皆不離緣起性空,是則一切皆屬無常,終歸於空無;此則無性,不名空性,名為無常性;既性無常,不名中道,此非大乘《大般若經》、《大般涅槃經》、《楞伽經》、《楞嚴經》、《圓覺經》、《維摩詰經》、《法華經》所說之中道也。 答:蕭平實先生認為緣起性空非為大乘中道、人們錯解了《大智度論》以及龍樹菩薩之密意,對此可破斥如下: 般若經典、《大智度論》所闡釋的皆為大乘緣起性空之成佛之道,非為成就聲緣羅漢之二乘法。般若經中一再強調:從色乃至一切智智,萬法皆無實有性,都為本體不恆存的自性空,萬法之自性當下即是空性。對此,《大智度論》引用佛語已將這一觀點表達得異常清楚:「舍利弗,色、色相空,受、想、行、識、識相空;檀波羅蜜、檀波羅蜜相空,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如是。內空、內空相空,乃至無法有法空、無法有法空相空。四念處、四念處相空,乃至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相空。如法性、實際不可思議性,不可思議性相空。三昧門、三昧門相空,陀羅尼門、陀羅尼門相空。一切智、一切智相空,道種智、道種智相空,一切種智、一切種智相空。」《中論》中同樣直接指出一切法本來為空的道理:「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回諍論》中亦云:「我無承認故,我即為無過。」這些經論統統都在表明:不僅有為法是空性,即就是無為法,包括如來藏、佛之功德、涅槃等,其本體依然為空,但在顯現上則恆常具有、無欺存在。 不過蕭先生卻似乎不這樣認為,在其所著的《狂密與真密》一書中,先生即如是論述道:「當知一切有情所知之心及覺知性,皆不能外於名色而獨存;能外於名色及一切法而獨自存在之心,唯有第八識如來藏(此識於凡夫及解脫道之有學位中名為阿賴耶識,無學位中改名為第九識異熟識,佛地改名為第十識無垢識,亦名真如。未至佛地之前一切位中總名如來藏)可以離於一切法而單獨存在,其餘一切識皆不能外於諸法而單獨存在。」且不說在這幾句話及先生的所有著作中一犯再犯的將如來藏不加任何區分地等同於阿賴耶識這類錯誤,單就其認定如來藏或阿賴耶識可離於一切法而單獨存在這一觀點即可看出:蕭先生顯然堅定地認為如來藏或阿賴耶是實有的,因只有實有法才談得上不觀待一切因緣。如果我們沒有歪曲平實先生原意的話,則以下結論的推出當屬必然之結果:這種將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當成不依賴於任何外在之法的實有存在,與外道所謂的常有不變的「神我」實無絲毫本質差別!儘管先生拼盡全力、毫不「嘴」軟地痛斥別宗,特別是密宗的某些宗派為常見外道,奈何自己的觀點卻真正與常見外道不謀而合,這多多少少會讓人產生一種看某些人自扇其臉的感覺。執著了如來藏或阿賴耶的實有,然後再來大談中道,這無論如何都有點自相矛盾的味道。因所謂中道必須破除一切邊執,牢牢執著如來藏的實有之人,又怎可能了知諸佛菩薩宣講中道的密意?雖說在《邪見與佛法》中,先生曾懇請諸方大德「莫因愚之舉陳『如來藏實有』,便責愚為『執著如來藏』,愚意乃在辨正此第八識實有,教化佛門中之斷滅論者回心,純為佛教正法著眼,無著可言。」但我們還是要責其執著如來藏,因只要承認法界中有不空的成實法,對此法的執著便決定無法消除。既如此,中道又從何談起?只有破除了一切法的實有,包括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的本體實有,中道才有可能現前——如果說中道有密意的話,恐怕這才是它本具的密意。若非如是,則以上經論應在破除了一切法的成實性之後,再來安立阿賴耶識、如來藏的成實性,如此方才符合他本人對龍樹菩薩密意的「挖掘」——「龍樹此偈乃闡釋大乘般若空性,非謂五陰及諸現象界之空相;乃謂如來藏之中道空,非謂二乘法中緣起緣滅之空相。真實中道觀者真如佛性也,……以此智慧而斷遍計執性。於一切緣起緣滅之依他起性中,證得如來藏之非有非無中道空性——圓成實性;方符龍樹此偈本旨、真實證驗中觀,不墮二乘無常法中,……」不過,不論是般若經還是龍樹論,在破析了萬法實有、建立了真實中道之後,都沒有再提出過存在一個不空的阿賴耶識或如來藏的觀點。順帶說一句,看來先生始終不解佛陀於第三轉法輪期間所安立的如來藏之「有」,與第二轉法輪期間所破除的萬法之「有」到底有何區別,一如先生籠統地將如來藏與阿賴耶識劃上等號一樣。 另外,若按照蕭先生的論斷來分析,則斷除了遍計執即為非有,而留下緣起緣滅的依他起則謂非無,如此即成為四邊戲論中的第四邊「非有非無雙俱邊」。這樣一來,不僅這兩邊戲論未被斷除,而且依此理推之,有邊、無邊的執著也未被放下,這就直接與《中論》中的論述「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相違背,這又如何能被稱之為中道? 下面再從蕭先生的諸多文章中摘取一例,以令大眾更進一步理解先生眼中的中道或曰空究竟是何景觀。 先生曾把如來的解脫空理解成如「人去樓空的村莊、枯竭的河川、瓶中無水,並非沒有了村莊河川瓶子,由於其中已經虛無了,所以說是空。」依憑《楞伽經》的論證,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所謂的「解脫空」與說經堂裡沒有人、馬上沒有牛一樣,都是最低劣的一種空。此經中云:「大慧,譬如鹿子母捨,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捨捨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余處無象馬,是名一切法自相,是名彼彼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當遠離。」既然此經中已經明白揭示了空的真實含義,如果再按照蕭先生的論述看待佛陀的解脫,則有無上正等正覺之佛陀所證悟的竟然是最低劣的空這種過失!可能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法界當中依然存有不滅的山川河流與瓶子吧。 如來根據不同眾生的根基而分別闡揚了八萬四千法門,其三轉法輪的究竟密意依然是針對所化眾生的不同根性而相應施與了義或不了義之教授。只有在理解了這個大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既不割裂三轉法輪的整體性,又能清楚了知究竟說法與不究竟說法之間的區別,從而力斷籠統含混、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錯雜混亂等過失。我們必須瞭解,第二轉與第三轉法輪既本體相通,同時又反體有別,只有這樣才能把如來藏與空性完美地統一起來,否則都不可能達於中道。 個別人總是要把緣起性空當成空無之斷滅來理解,但這兩者之間實有天大的差別。空無之斷滅是謂先有後無;而緣起之萬法其本性就是空性,正因為空所以才可依各種因緣而得以顯現。認為緣起緣滅是無常性、非中道的觀點是否是真正的斷滅見,智者當以經教自己衡量,因緣起緣滅闡發的恰恰就是遠離有無執著的中道觀。解釋般若經典及龍樹之論的意旨,如果只憑借凡夫的分別念,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師心自用、難以契入佛經堂奧。對於無師自通之人的那些未經過印證的種種說法,我們只可以一家之言、一得之見待之,真要奉之為聖旨,那就只能說明自己眼界太狹窄了。
蕭平實說:密法是將印度教的教法及印度教性力派邪說與「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混合起來的一個宗教。 答:密法是純正清淨的佛法,絕非附佛外道。談到密法的來源,大量的經教都指出:一部分密法內容是釋迦牟尼佛住世時親口宣說,比如於印度南方哲蚌米積大塔處宣說《文殊真實名經》、《時輪金剛續》等,又在烏仗那國宣說《密集金剛》等續部經典;還有一些則是釋尊以不同身相、不同方式在不同剎土為不同的所化眾生分別敷演的。這些在別的剎土被佛陀宣講過的密宗妙法,其後又通過種種方式輾轉流傳至人間。其中關於五持明於佛涅槃若干年後從某位菩薩那裡接受普賢如來於法界所傳密法的內容,以及佛陀在某些經典中授記蓮花生大師將於未來出世廣弘密法的具體經過、細節,還有多種密法傳承次第的分別介紹,我們會在下文或者別的一些專著中行文描述,這裡就不再展開論述了。 將密法定義為是一種印度教、性力派邪說再加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混合而成的大雜燴,這種說法的得出想必是對密宗知之甚少的結果。這也情有可原,因藏文《大藏經》中多達二十餘函的密續只有少數被翻譯成漢文,而系統、全面、客觀、正確介紹密宗的論典與著作也少見問世。因此對一個或許多不懂藏文的人來說,缺乏對藏傳佛教的瞭解也並不為過。但無知不應該成為值得炫耀的資本,如果把因無知而得來的偏見再當作真理到處宣揚,這種做法就有些令人生厭了。 僅僅只是聽說了一些雙運、護摩、降服等對普通人來說似乎略顯陌生的名詞,從而就把密宗與在其論典中也出現過這些名相的印度教劃上等號,這種論調恐怕有失偏頗。非常明顯的一個例證是,佛陀在三轉法輪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宣說小乘及大乘顯宗的時候,都曾用過一些外道同樣也在使用的名詞術語,諸如五蘊、八識、人天善果等,如此說來,是否顯宗也應從此被更名為附印度教或婆羅門教之外道了呢?賦予共同名詞以嶄新含義,這本來就是佛法有容乃大的表現之一,也是佛法超越一切外道及世間思想之所在,豈能以名詞相同就認定其背後的指導思想也相同。再比如六度中的佈施度、持戒度、安忍度等說法,很多外道及世俗倫理、道德體系中也有關於此方面的內容,但每一個正信佛教徒都不會因此就把佛教曲為比附於任何外道,佛教在六度思想背後的顯空雙運的究竟底蘊,你在所有的非佛教之宗教中都了無覓處。 而且從歷史來看,佛法傳入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期間也出現了不少依附佛教的外道與邪教,它們不僅抄襲了不少佛教名詞,還偽造了一些經典,甚至搬出佛教中的很多佛菩薩為自己裝點門面。不過這些真正的附佛外道的最終結局卻大致相同:雖然可以欺騙得了一時,終究還是要被人們看破其廬山真面。這也給了我們一點啟示,如果密法真是借用佛法名相的一種外道宗派的話,為何獨它能綿延千餘年而至今仍長盛不衰?難道密法的欺騙性就那麼大,以致能始終混在佛教隊伍中不被人們踢除出界? 客觀說來,從密法誕生直到現在,歷朝歷代都不乏對它橫加指責之人。這些人既包括了教內人士,也涵蓋了世間智者。但不論他們是從佛理出發,還是從世間哲學、倫理或科學的角度展開對密法的圍剿,迄今為止,尚未有一人能提出駁倒密法存在理由以及其作為佛法正統分支的根據。也許幾千年中都未曾誕生過像蕭平實先生這般聰明絕頂的人物,其一人之力足以抵得上無數前驅者的智慧與努力。不過這無論如何都令人難以置信,因我們實在看不出此人卓絕的智慧到底體現在哪裡。 他自己認為密宗儘管引用了佛法名相的理論,但與佛法絕對不是一回事。在《甘露法雨》中他如是評論道:「這種引用佛法名相的理論,和佛教中所說的正遍知覺,完全不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人還是懂得引用者與被引用者並不能同日而語。不過他的標準卻是兩重性的:只要密法中出現與外道相同的一些詞句,那麼不管密宗在本質上如何與它們不同,蕭先生也必須把密法與外道等同起來;除此之外,他對借鑒、引用與被借鑒、被引用以及共用之間的關係還是涇渭分明的。這種極具兩面性的判定指南只能讓我們感到,某些人心中的偏見已徹底扭曲了他自己的認識公平度。 現代人如若想走進密法並進而評論密法,唯一的方式只能是充分地瞭解、研究、修習密宗,其依據應該是浩如煙海的經續及祖師大德的論著;其皈依處應該是具相上師;其可靠的途徑則是聞思修,捨此別無他途。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既不要盲從對密法一無所知且滿懷不知從何處來的憤恨者的話語,也不能依據沒有傳承、通過抄襲、拼湊而成的文字,當然也不應把所謂的考證、純學術化的宗教學研究以及心理分析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 有一點很是讓人費解,即蕭先生一方面大力痛斥密法,一方面又通過神通借助禪定及睡夢得知,自己過去世曾當過密宗覺囊派的修行人,甚至是教主。這樣矛盾的說法的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是在誇耀自己的神通,還是誇耀密宗的覺囊派?或者在他眼中,覺囊派根本就不屬於密法,與另外幾大密宗派別實有天壤之別?如果這後一種說法能成立的話,這倒是一千古奇談,因不論是覺囊派本身還是密宗的其他所有教派,無不公認覺囊派是純正的密法,而且是極具藏地本土特色的密法流派。難道作為覺囊派曾經的一派之主,蕭先生現在在禪定中或夢境裡竟沒看出來這一點? 有一點常識我想我們都應該知道,即密宗有著非常嚴格的傳承系統。藏密五大教派的祖師均源於印度,如寧瑪巴的蓮花生大師、噶舉派的帝洛巴尊者、薩迦派的布瓦巴尊者、覺囊派的月護、噶當派的阿底峽尊者,這些人全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們創立的宗派也都不是空穴來風,只要查閱各派的祖師傳承年表、歷代祖師傳記即可一目瞭然。不過在《宗通與說通》中,蕭先生卻千古獨步般地論說道:「至於覺囊巴,並非密宗初始即有之教派,法道亦異紅白黃花四大派。」在這裡,他生硬地將覺囊從藏傳佛教的整體系統中割裂開來,實則沒有任何教證理證的根據。 眾所周知,不動金剛(彌覺多吉)於十一世紀中葉創立了他空見,其後經法自在、虛空光等傳至土傑尊珠,他於拉孜縣東北建立起覺摩囊寺,簡稱覺囊,從此該派即以寺名。在傳至堆波瓦·喜饒堅贊後,此派遂大興於世。其有羅追貝、喬列南傑、薩桑瑪底班欽等著名弟子,後兩人曾為宗喀巴大師之上師。公元十六世紀,此派大喇嘛由轉世相延續,其中定為袞噶卓喬轉世的多羅那他名聲最著,使該派一度中興。 既然蕭先生說過:「雖然我今生沒有學密,但過去世我也在密宗覺囊派待過一兩百年,也曾是一派之主。」那麼對這些關於自宗的歷史就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我想你這個一派之主的禪定功夫再怎麼不行、睡得再怎麼沉沉不醒,對這一點歷史事實大約還是應能回憶起來的:即覺囊派主要是從印度的無著菩薩、旃陀羅閣彌等聖者那裡汲取了其顯宗部分的立論之基——中觀他空見;又於《時輪金剛續》中擷取了自身的密法精華。而《時輪金剛續》以及無著菩薩等聖者,皆被密宗所有宗派共同承認且一致作為自己的實修之有機組成部分及理論導師,因此把覺囊派與別的四大教派截然分開顯然不合理。而且最關鍵的問題是,《時輪金剛續》分明是釋尊親口宣說,如果蕭先生還認為自己當過覺囊派法王的話,那他就必須承認所有密法教派的合理性!否則自己豈不成為了一個外道之王?還有什麼理由在這裡以佛法的捍衛者自居? 但蕭先生卻在《邪見與佛法》中如是說道:「密教第四種誤會:時輪金剛的無上密續。這就是時輪金剛最後階段的父續與母續——喜金剛……這都是屬於男女兩性的雙身合修法,是移植自印度教裡的密法,是密宗金剛上師與異性弟子間永遠的秘密。」將自宗的根本續貶低為與世間凡夫之男歡女愛同屬一個檔次的法王,翻遍密宗歷史也查無此人!可能是在蕭先生擔任覺囊法王期間,才開始大規模地引進印度教的性力派邪說吧。在這裡我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任何人在任何有關覺囊派的歷史著作中都找不到否定自宗密法修煉之基的法王存在。這麼說來,人們不得不產生一個疑惑——到底是蕭平實先生在篡改覺囊派歷史,還是他本人的禪定功夫出了偏差?抑或他自己根本就不懂什麼才是真正的時輪金剛修法?古人有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許先生自己浸淫在性力派的學說中太過沉迷,以致不辨東西、難以自拔,故最後便把自己對男女性愛的狂想硬塞進與以凡夫貪心為基礎的世間情愛毫無關聯的密宗之中? 而且《狂密與真密》中還如是說道:「近年因閱讀《土觀宗派源流》一書之後,於定中及夢中漸漸引出往世在覺囊派中二世任法王……」擔任了兩世的法王,那串習應該相當深厚了,何以如今不僅不幫助我們這些普通的密宗行者弘揚密法,反而更要對密法斬盡殺絕?這種巨大的反差不能不讓人懷疑你說的是大妄語。 如果真在這件事情上打了妄語,則《賢愚經·長者無耳目舌品》中的一段公案當足資言妄語者借鑒。那個名為檀若世質的平事,因未秉公執法、在一件需他作證的事情上沒能說實話,結果竟轉生成一個生下來即沒有眼、耳、嘴、舌及手腳、一片混沌只有男根的人。這還只是不說實話的果報,若進而顛倒黑白、謗法謗僧,其罪報恐怕就非常人所可想像了。況且先生自己也曾說過:「果報真是厲害;……若沒有證據,絕對不敢再輕易評論任何善知識。」既如此明理,那就請先拿出《時輪金剛》非佛所說、覺囊派法王從未修過此種大法、覺囊派非屬密宗體系等相關論點的證據,然後再給眾人講解自己的夢境吧。 翻開覺囊的歷史一查,則所有覺囊法王都是與時輪金剛有甚深因緣的大成就者。不過不知蕭先生知不知,雙運修法就是釋尊在《時輪金剛》中重點宣講的。你如果學過密法、懂得藏語的話,一定能了知此點。而你不僅否定了所有密法,更對密法中的雙運修法大加鞭撻,以為其是淫蕩的代名詞。既如此,我們就有些不明白了,覺囊派沒有一個法王不修《時輪金剛》而成就,而它的內容已如上說,但你又最痛恨雙運修法,那你成的到底是哪一位覺囊法王?你當法王時修的都是哪些獨特大法?請再顯神通,為我們道上姓名來,好讓我們對照著覺囊的歷史一一查看一下。好在覺囊的歷史並不是很長,如果你報上姓名,核對一下大概花不了多長時間。 大部分覺囊派的寺廟在十七世紀中葉時就已基本上歸屬於格魯巴了,以至於現在的康區一帶極少有其所屬寺廟存世。眼見這種景觀,難道你作為一派之主竟無動於衷?不久前,受人恭敬的覺囊一代法主雲丹桑布不幸圓寂,不知蕭平實先生有沒有動過再掌覺囊大印、重振覺囊雄風的念頭?有時在腦海中情不自禁地就會浮現出這樣的一幅畫面:蕭先生頭戴時輪金剛佛冠、高坐他空見寶座上、手裡還拿著被他自己譏諷為是性力派法器的金剛橛及鈴杵,正在給眾人宣說非密宗之自創宗派教義。這該是多麼值得被寫進世界佛教史上的一頁畫卷!如果蕭先生真有這樣的雄心壯志,那我將側耳聆聽為你舉行新法王坐床大典的消息。 我們今天所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成為歷史,而歷史只有留待後人去評說。但別因此就為所欲為,因為不管後人如何評說,無欺之因果才是最嚴厲也是最終的審判官。而因果自負,所以務必多加慎重!
蕭平實說:佛性須以眼見為憑,……見性應以肉眼親見佛性為憑,……「佛性非天眼所能見」除系依佛語外,亦依實際證量而言。我會中同修亦有得天眼者,受菩薩戒後隨余修學六月,終未能見佛性,復回神道教中。若不學大涅槃經,而雲天眼能見佛性者,無有是處。 答: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知,有些人可能連一些基本的佛法名相都未能搞明白,在這種前提下還要沐猴而冠、好為人師,處處以佛教權威解釋者的面孔自居,就實在是有些不倫不類、勉為其難了。 一般而論,肉眼有兩種解釋:一是指凡夫的眼根,二是謂「五眼六通」中「五眼」之一的肉眼。《金剛經》中曾提到過所謂的五眼,其中就包括了肉眼與天眼。《現觀莊嚴論》第一品中就有涉及「五眼六通」的內容(很明顯,蕭先生是把五眼與六通的功德混為一談了。);第二品教言品中則專門從因、作用範圍、類別等幾方面解釋五眼。此論以教量抉擇道:資糧道之菩薩開始具有肉眼,資糧道以上之菩薩相續中都具足。而別的一些論典中則具體闡釋道:肉眼是在加行道時通過供燈、修等持而獲得的,依靠肉眼可以現見一百由旬到三千大千世界整個世間內的方方面面。 儘管在敘述上略有差別,但一般而言,佛教經論基本上公認:天眼的功德遠遠超越肉眼。一些論典中認為修禪定等六度才是具足天眼之因,憑天眼可以照見十方所有眾生前生後世、投生受生的具體情況。依道地而論,加行道以上的人相續中方才具足天眼之功德,此功德通過修持有漏善法而獲得。 若按照以上標準來衡量,則蕭先生會下一具足天眼者卻無法眼見佛性,唯有具足肉眼者方能眼見佛性,則天眼、肉眼之順序豈非要前後顛倒?一般而論,得天眼者若具足肉眼,(按次第遞進之規律,這是必然的。)則他必能見佛性;若不具足,則他是否如《楞嚴經》中阿那律所言:「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 如果蕭先生所謂的「肉眼」非是「五眼」中的肉眼,那麼我們就只能把此處的肉眼理解成是普通凡夫的眼根了。若真是這樣的話,那他論點中的漏洞就更大。儘管他本人在《護法集》中曾引用過《大般涅槃經》中的幾句話(見一百七十一頁),但不知他看過沒看過,或者說理解不理解此經卷八中的這一句話:「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雖然經中亦有迦葉菩薩問佛:「佛性微細難知,雲何肉眼而能見?」佛對此回答道:「聲聞緣覺信順如是大涅槃經,自知己身有如來性,亦復如是。」但此處重點宣說的根本就不是以肉眼見不見佛性的問題,而是通過「信順」佛語從而堅信自身有如來藏的問題。 此經文明示:眾生皆具佛性,然佛性細微難察,凡夫位不見,有學道時以誠信而可了達其總相。十地菩薩亦只是片面了知,唯佛陀才能以具備如所有智、盡所有智之佛眼洞見佛性。倘若依此而認為肉眼可看見佛性,則此實為錯謬之談,因經中明確告訴我們:聲聞緣覺依此經而起勝解,並信受自身具有佛性之說。否則的話,應將經文改成「自見己身有如來性」了。 再者學過因明、唯識、俱捨的人都知道,肉眼所見之對境為色塵,而佛性乃無為法,絕對不可能被色法涵蓋。假若佛性真的可以依肉眼見之,那麼請問它的長短、大小、形狀、顏色又如何? 憨山老人在《<金剛經>決疑》中也曾提到過五眼的問題,他對此的解釋是:「空生疑佛具五眼,將謂有法可見,有世界眾生有情。世尊告以所具五眼非眼也,但約見眾生心為眼爾。」藕益大師在《<金剛經>破空論》中亦云:「夫五眼者,能照之知見也。」從中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裡所說的「眼」哪裡是指肉眼!這五眼均為眾生本具之功德,通過信解佛經、努力修持、戒定慧次第升進,一定可以將之顯發出來。若把經中所言的眼見佛性理解成肉眼見佛性,只能說持此說者混淆了五眼與六通、肉眼與五眼及「心眼」、照與見之間的界限、關聯。《涅槃經》中對此說得非常明瞭:「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瞭;佛眼見故,而得了了。」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不論是肉眼、天眼還是慧眼,都無法「眼」見佛性,只有佛眼才能將之了了分明地一覽無餘。 為了掩蓋自己論點中的致命缺陷,蕭先生又在別處提出所謂的「綜合肉眼說」。即他認為眼見佛性之眼除了包含眼根外,尚綜合了從心到如來藏一系列器官、心意識乃至佛性等或精神或物質或超離言說的種種實體與非實體之活動、功能。這種論調依然掩蓋不了其本質上的錯誤,一個非常淺顯的反駁理由是:在「綜合肉眼見佛性」說中,肉眼發揮不發揮根本作用?如果發揮根本作用,則我們已在上文破斥過此種觀點;如果肉眼不發揮決定性作用,那麼僅以肉眼結合如來藏為例,如此說成立,則有如來藏自己見自己之過。如來藏在什麼樣的對境下可以見到如來藏?肉眼見不到佛性,佛性自身也無法見到佛性,以此理推之,人人手中都沒有一分錢,這樣的人即就是湊足一千個,依然湊不出一分錢。「綜合見性說」的漏洞也就在這裡。 另一方面,根據《俱捨論》的觀點,眼識的產生需要具備三點條件:外境、眼根以及作意。剎那間具足這三點,隨後眼識便告產生。如果如來藏要見如來藏的話,那麼它又是如何作意的?最後再強調一點以正視聽:按照因明的觀點,五根識皆為現量親見、親聞、親觸等,若肉眼能見,當為現量了了而見。但佛陀在經典中早已說得清清楚楚,十地菩薩都不可能現量了了親見佛性。既如此,凡夫雲何得以憑肉眼就親見佛性? 既無教證,也無理證,看來我們又得問一句老話了:這到底是在闡發經義,還是在大肆宣揚自己的分別念?
蕭平實說:有謂《大智度論》所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為中道。」,乃是說緣起性空,謂緣起性空即是中道。然而此種解釋乃依二乘法而解釋龍樹菩薩之中道,實非中道,何以故?以緣起性空所顯一切理,皆依有為法之現象界而言;現象界之一切有為法悉皆不離緣起性空,是則一切皆屬無常,終歸於空無;此則無性,不名空性,名為無常性;既性無常,不名中道,此非大乘《大般若經》、《大般涅槃經》、《楞伽經》、《楞嚴經》、《圓覺經》、《維摩詰經》、《法華經》所說之中道也。 答:蕭平實先生認為緣起性空非為大乘中道、人們錯解了《大智度論》以及龍樹菩薩之密意,對此可破斥如下: 般若經典、《大智度論》所闡釋的皆為大乘緣起性空之成佛之道,非為成就聲緣羅漢之二乘法。般若經中一再強調:從色乃至一切智智,萬法皆無實有性,都為本體不恆存的自性空,萬法之自性當下即是空性。對此,《大智度論》引用佛語已將這一觀點表達得異常清楚:「舍利弗,色、色相空,受、想、行、識、識相空;檀波羅蜜、檀波羅蜜相空,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如是。內空、內空相空,乃至無法有法空、無法有法空相空。四念處、四念處相空,乃至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相空。如法性、實際不可思議性,不可思議性相空。三昧門、三昧門相空,陀羅尼門、陀羅尼門相空。一切智、一切智相空,道種智、道種智相空,一切種智、一切種智相空。」《中論》中同樣直接指出一切法本來為空的道理:「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回諍論》中亦云:「我無承認故,我即為無過。」這些經論統統都在表明:不僅有為法是空性,即就是無為法,包括如來藏、佛之功德、涅槃等,其本體依然為空,但在顯現上則恆常具有、無欺存在。 不過蕭先生卻似乎不這樣認為,在其所著的《狂密與真密》一書中,先生即如是論述道:「當知一切有情所知之心及覺知性,皆不能外於名色而獨存;能外於名色及一切法而獨自存在之心,唯有第八識如來藏(此識於凡夫及解脫道之有學位中名為阿賴耶識,無學位中改名為第九識異熟識,佛地改名為第十識無垢識,亦名真如。未至佛地之前一切位中總名如來藏)可以離於一切法而單獨存在,其餘一切識皆不能外於諸法而單獨存在。」且不說在這幾句話及先生的所有著作中一犯再犯的將如來藏不加任何區分地等同於阿賴耶識這類錯誤,單就其認定如來藏或阿賴耶識可離於一切法而單獨存在這一觀點即可看出:蕭先生顯然堅定地認為如來藏或阿賴耶是實有的,因只有實有法才談得上不觀待一切因緣。如果我們沒有歪曲平實先生原意的話,則以下結論的推出當屬必然之結果:這種將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當成不依賴於任何外在之法的實有存在,與外道所謂的常有不變的「神我」實無絲毫本質差別!儘管先生拼盡全力、毫不「嘴」軟地痛斥別宗,特別是密宗的某些宗派為常見外道,奈何自己的觀點卻真正與常見外道不謀而合,這多多少少會讓人產生一種看某些人自扇其臉的感覺。執著了如來藏或阿賴耶的實有,然後再來大談中道,這無論如何都有點自相矛盾的味道。因所謂中道必須破除一切邊執,牢牢執著如來藏的實有之人,又怎可能了知諸佛菩薩宣講中道的密意?雖說在《邪見與佛法》中,先生曾懇請諸方大德「莫因愚之舉陳『如來藏實有』,便責愚為『執著如來藏』,愚意乃在辨正此第八識實有,教化佛門中之斷滅論者回心,純為佛教正法著眼,無著可言。」但我們還是要責其執著如來藏,因只要承認法界中有不空的成實法,對此法的執著便決定無法消除。既如此,中道又從何談起?只有破除了一切法的實有,包括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的本體實有,中道才有可能現前——如果說中道有密意的話,恐怕這才是它本具的密意。若非如是,則以上經論應在破除了一切法的成實性之後,再來安立阿賴耶識、如來藏的成實性,如此方才符合他本人對龍樹菩薩密意的「挖掘」——「龍樹此偈乃闡釋大乘般若空性,非謂五陰及諸現象界之空相;乃謂如來藏之中道空,非謂二乘法中緣起緣滅之空相。真實中道觀者真如佛性也,……以此智慧而斷遍計執性。於一切緣起緣滅之依他起性中,證得如來藏之非有非無中道空性——圓成實性;方符龍樹此偈本旨、真實證驗中觀,不墮二乘無常法中,……」不過,不論是般若經還是龍樹論,在破析了萬法實有、建立了真實中道之後,都沒有再提出過存在一個不空的阿賴耶識或如來藏的觀點。順帶說一句,看來先生始終不解佛陀於第三轉法輪期間所安立的如來藏之「有」,與第二轉法輪期間所破除的萬法之「有」到底有何區別,一如先生籠統地將如來藏與阿賴耶識劃上等號一樣。 另外,若按照蕭先生的論斷來分析,則斷除了遍計執即為非有,而留下緣起緣滅的依他起則謂非無,如此即成為四邊戲論中的第四邊「非有非無雙俱邊」。這樣一來,不僅這兩邊戲論未被斷除,而且依此理推之,有邊、無邊的執著也未被放下,這就直接與《中論》中的論述「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相違背,這又如何能被稱之為中道? 下面再從蕭先生的諸多文章中摘取一例,以令大眾更進一步理解先生眼中的中道或曰空究竟是何景觀。 先生曾把如來的解脫空理解成如「人去樓空的村莊、枯竭的河川、瓶中無水,並非沒有了村莊河川瓶子,由於其中已經虛無了,所以說是空。」依憑《楞伽經》的論證,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所謂的「解脫空」與說經堂裡沒有人、馬上沒有牛一樣,都是最低劣的一種空。此經中云:「大慧,譬如鹿子母捨,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捨捨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余處無象馬,是名一切法自相,是名彼彼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當遠離。」既然此經中已經明白揭示了空的真實含義,如果再按照蕭先生的論述看待佛陀的解脫,則有無上正等正覺之佛陀所證悟的竟然是最低劣的空這種過失!可能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法界當中依然存有不滅的山川河流與瓶子吧。 如來根據不同眾生的根基而分別闡揚了八萬四千法門,其三轉法輪的究竟密意依然是針對所化眾生的不同根性而相應施與了義或不了義之教授。只有在理解了這個大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既不割裂三轉法輪的整體性,又能清楚了知究竟說法與不究竟說法之間的區別,從而力斷籠統含混、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錯雜混亂等過失。我們必須瞭解,第二轉與第三轉法輪既本體相通,同時又反體有別,只有這樣才能把如來藏與空性完美地統一起來,否則都不可能達於中道。 個別人總是要把緣起性空當成空無之斷滅來理解,但這兩者之間實有天大的差別。空無之斷滅是謂先有後無;而緣起之萬法其本性就是空性,正因為空所以才可依各種因緣而得以顯現。認為緣起緣滅是無常性、非中道的觀點是否是真正的斷滅見,智者當以經教自己衡量,因緣起緣滅闡發的恰恰就是遠離有無執著的中道觀。解釋般若經典及龍樹之論的意旨,如果只憑借凡夫的分別念,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師心自用、難以契入佛經堂奧。對於無師自通之人的那些未經過印證的種種說法,我們只可以一家之言、一得之見待之,真要奉之為聖旨,那就只能說明自己眼界太狹窄了。
蕭平實說:密法是將印度教的教法及印度教性力派邪說與「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混合起來的一個宗教。 答:密法是純正清淨的佛法,絕非附佛外道。談到密法的來源,大量的經教都指出:一部分密法內容是釋迦牟尼佛住世時親口宣說,比如於印度南方哲蚌米積大塔處宣說《文殊真實名經》、《時輪金剛續》等,又在烏仗那國宣說《密集金剛》等續部經典;還有一些則是釋尊以不同身相、不同方式在不同剎土為不同的所化眾生分別敷演的。這些在別的剎土被佛陀宣講過的密宗妙法,其後又通過種種方式輾轉流傳至人間。其中關於五持明於佛涅槃若干年後從某位菩薩那裡接受普賢如來於法界所傳密法的內容,以及佛陀在某些經典中授記蓮花生大師將於未來出世廣弘密法的具體經過、細節,還有多種密法傳承次第的分別介紹,我們會在下文或者別的一些專著中行文描述,這裡就不再展開論述了。 將密法定義為是一種印度教、性力派邪說再加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混合而成的大雜燴,這種說法的得出想必是對密宗知之甚少的結果。這也情有可原,因藏文《大藏經》中多達二十餘函的密續只有少數被翻譯成漢文,而系統、全面、客觀、正確介紹密宗的論典與著作也少見問世。因此對一個或許多不懂藏文的人來說,缺乏對藏傳佛教的瞭解也並不為過。但無知不應該成為值得炫耀的資本,如果把因無知而得來的偏見再當作真理到處宣揚,這種做法就有些令人生厭了。 僅僅只是聽說了一些雙運、護摩、降服等對普通人來說似乎略顯陌生的名詞,從而就把密宗與在其論典中也出現過這些名相的印度教劃上等號,這種論調恐怕有失偏頗。非常明顯的一個例證是,佛陀在三轉法輪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宣說小乘及大乘顯宗的時候,都曾用過一些外道同樣也在使用的名詞術語,諸如五蘊、八識、人天善果等,如此說來,是否顯宗也應從此被更名為附印度教或婆羅門教之外道了呢?賦予共同名詞以嶄新含義,這本來就是佛法有容乃大的表現之一,也是佛法超越一切外道及世間思想之所在,豈能以名詞相同就認定其背後的指導思想也相同。再比如六度中的佈施度、持戒度、安忍度等說法,很多外道及世俗倫理、道德體系中也有關於此方面的內容,但每一個正信佛教徒都不會因此就把佛教曲為比附於任何外道,佛教在六度思想背後的顯空雙運的究竟底蘊,你在所有的非佛教之宗教中都了無覓處。 而且從歷史來看,佛法傳入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期間也出現了不少依附佛教的外道與邪教,它們不僅抄襲了不少佛教名詞,還偽造了一些經典,甚至搬出佛教中的很多佛菩薩為自己裝點門面。不過這些真正的附佛外道的最終結局卻大致相同:雖然可以欺騙得了一時,終究還是要被人們看破其廬山真面。這也給了我們一點啟示,如果密法真是借用佛法名相的一種外道宗派的話,為何獨它能綿延千餘年而至今仍長盛不衰?難道密法的欺騙性就那麼大,以致能始終混在佛教隊伍中不被人們踢除出界? 客觀說來,從密法誕生直到現在,歷朝歷代都不乏對它橫加指責之人。這些人既包括了教內人士,也涵蓋了世間智者。但不論他們是從佛理出發,還是從世間哲學、倫理或科學的角度展開對密法的圍剿,迄今為止,尚未有一人能提出駁倒密法存在理由以及其作為佛法正統分支的根據。也許幾千年中都未曾誕生過像蕭平實先生這般聰明絕頂的人物,其一人之力足以抵得上無數前驅者的智慧與努力。不過這無論如何都令人難以置信,因我們實在看不出此人卓絕的智慧到底體現在哪裡。 他自己認為密宗儘管引用了佛法名相的理論,但與佛法絕對不是一回事。在《甘露法雨》中他如是評論道:「這種引用佛法名相的理論,和佛教中所說的正遍知覺,完全不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人還是懂得引用者與被引用者並不能同日而語。不過他的標準卻是兩重性的:只要密法中出現與外道相同的一些詞句,那麼不管密宗在本質上如何與它們不同,蕭先生也必須把密法與外道等同起來;除此之外,他對借鑒、引用與被借鑒、被引用以及共用之間的關係還是涇渭分明的。這種極具兩面性的判定指南只能讓我們感到,某些人心中的偏見已徹底扭曲了他自己的認識公平度。 現代人如若想走進密法並進而評論密法,唯一的方式只能是充分地瞭解、研究、修習密宗,其依據應該是浩如煙海的經續及祖師大德的論著;其皈依處應該是具相上師;其可靠的途徑則是聞思修,捨此別無他途。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既不要盲從對密法一無所知且滿懷不知從何處來的憤恨者的話語,也不能依據沒有傳承、通過抄襲、拼湊而成的文字,當然也不應把所謂的考證、純學術化的宗教學研究以及心理分析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 有一點很是讓人費解,即蕭先生一方面大力痛斥密法,一方面又通過神通借助禪定及睡夢得知,自己過去世曾當過密宗覺囊派的修行人,甚至是教主。這樣矛盾的說法的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是在誇耀自己的神通,還是誇耀密宗的覺囊派?或者在他眼中,覺囊派根本就不屬於密法,與另外幾大密宗派別實有天壤之別?如果這後一種說法能成立的話,這倒是一千古奇談,因不論是覺囊派本身還是密宗的其他所有教派,無不公認覺囊派是純正的密法,而且是極具藏地本土特色的密法流派。難道作為覺囊派曾經的一派之主,蕭先生現在在禪定中或夢境裡竟沒看出來這一點? 有一點常識我想我們都應該知道,即密宗有著非常嚴格的傳承系統。藏密五大教派的祖師均源於印度,如寧瑪巴的蓮花生大師、噶舉派的帝洛巴尊者、薩迦派的布瓦巴尊者、覺囊派的月護、噶當派的阿底峽尊者,這些人全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們創立的宗派也都不是空穴來風,只要查閱各派的祖師傳承年表、歷代祖師傳記即可一目瞭然。不過在《宗通與說通》中,蕭先生卻千古獨步般地論說道:「至於覺囊巴,並非密宗初始即有之教派,法道亦異紅白黃花四大派。」在這裡,他生硬地將覺囊從藏傳佛教的整體系統中割裂開來,實則沒有任何教證理證的根據。 眾所周知,不動金剛(彌覺多吉)於十一世紀中葉創立了他空見,其後經法自在、虛空光等傳至土傑尊珠,他於拉孜縣東北建立起覺摩囊寺,簡稱覺囊,從此該派即以寺名。在傳至堆波瓦·喜饒堅贊後,此派遂大興於世。其有羅追貝、喬列南傑、薩桑瑪底班欽等著名弟子,後兩人曾為宗喀巴大師之上師。公元十六世紀,此派大喇嘛由轉世相延續,其中定為袞噶卓喬轉世的多羅那他名聲最著,使該派一度中興。 既然蕭先生說過:「雖然我今生沒有學密,但過去世我也在密宗覺囊派待過一兩百年,也曾是一派之主。」那麼對這些關於自宗的歷史就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我想你這個一派之主的禪定功夫再怎麼不行、睡得再怎麼沉沉不醒,對這一點歷史事實大約還是應能回憶起來的:即覺囊派主要是從印度的無著菩薩、旃陀羅閣彌等聖者那裡汲取了其顯宗部分的立論之基——中觀他空見;又於《時輪金剛續》中擷取了自身的密法精華。而《時輪金剛續》以及無著菩薩等聖者,皆被密宗所有宗派共同承認且一致作為自己的實修之有機組成部分及理論導師,因此把覺囊派與別的四大教派截然分開顯然不合理。而且最關鍵的問題是,《時輪金剛續》分明是釋尊親口宣說,如果蕭先生還認為自己當過覺囊派法王的話,那他就必須承認所有密法教派的合理性!否則自己豈不成為了一個外道之王?還有什麼理由在這裡以佛法的捍衛者自居? 但蕭先生卻在《邪見與佛法》中如是說道:「密教第四種誤會:時輪金剛的無上密續。這就是時輪金剛最後階段的父續與母續——喜金剛……這都是屬於男女兩性的雙身合修法,是移植自印度教裡的密法,是密宗金剛上師與異性弟子間永遠的秘密。」將自宗的根本續貶低為與世間凡夫之男歡女愛同屬一個檔次的法王,翻遍密宗歷史也查無此人!可能是在蕭先生擔任覺囊法王期間,才開始大規模地引進印度教的性力派邪說吧。在這裡我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任何人在任何有關覺囊派的歷史著作中都找不到否定自宗密法修煉之基的法王存在。這麼說來,人們不得不產生一個疑惑——到底是蕭平實先生在篡改覺囊派歷史,還是他本人的禪定功夫出了偏差?抑或他自己根本就不懂什麼才是真正的時輪金剛修法?古人有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許先生自己浸淫在性力派的學說中太過沉迷,以致不辨東西、難以自拔,故最後便把自己對男女性愛的狂想硬塞進與以凡夫貪心為基礎的世間情愛毫無關聯的密宗之中? 而且《狂密與真密》中還如是說道:「近年因閱讀《土觀宗派源流》一書之後,於定中及夢中漸漸引出往世在覺囊派中二世任法王……」擔任了兩世的法王,那串習應該相當深厚了,何以如今不僅不幫助我們這些普通的密宗行者弘揚密法,反而更要對密法斬盡殺絕?這種巨大的反差不能不讓人懷疑你說的是大妄語。 如果真在這件事情上打了妄語,則《賢愚經·長者無耳目舌品》中的一段公案當足資言妄語者借鑒。那個名為檀若世質的平事,因未秉公執法、在一件需他作證的事情上沒能說實話,結果竟轉生成一個生下來即沒有眼、耳、嘴、舌及手腳、一片混沌只有男根的人。這還只是不說實話的果報,若進而顛倒黑白、謗法謗僧,其罪報恐怕就非常人所可想像了。況且先生自己也曾說過:「果報真是厲害;……若沒有證據,絕對不敢再輕易評論任何善知識。」既如此明理,那就請先拿出《時輪金剛》非佛所說、覺囊派法王從未修過此種大法、覺囊派非屬密宗體系等相關論點的證據,然後再給眾人講解自己的夢境吧。 翻開覺囊的歷史一查,則所有覺囊法王都是與時輪金剛有甚深因緣的大成就者。不過不知蕭先生知不知,雙運修法就是釋尊在《時輪金剛》中重點宣講的。你如果學過密法、懂得藏語的話,一定能了知此點。而你不僅否定了所有密法,更對密法中的雙運修法大加鞭撻,以為其是淫蕩的代名詞。既如此,我們就有些不明白了,覺囊派沒有一個法王不修《時輪金剛》而成就,而它的內容已如上說,但你又最痛恨雙運修法,那你成的到底是哪一位覺囊法王?你當法王時修的都是哪些獨特大法?請再顯神通,為我們道上姓名來,好讓我們對照著覺囊的歷史一一查看一下。好在覺囊的歷史並不是很長,如果你報上姓名,核對一下大概花不了多長時間。 大部分覺囊派的寺廟在十七世紀中葉時就已基本上歸屬於格魯巴了,以至於現在的康區一帶極少有其所屬寺廟存世。眼見這種景觀,難道你作為一派之主竟無動於衷?不久前,受人恭敬的覺囊一代法主雲丹桑布不幸圓寂,不知蕭平實先生有沒有動過再掌覺囊大印、重振覺囊雄風的念頭?有時在腦海中情不自禁地就會浮現出這樣的一幅畫面:蕭先生頭戴時輪金剛佛冠、高坐他空見寶座上、手裡還拿著被他自己譏諷為是性力派法器的金剛橛及鈴杵,正在給眾人宣說非密宗之自創宗派教義。這該是多麼值得被寫進世界佛教史上的一頁畫卷!如果蕭先生真有這樣的雄心壯志,那我將側耳聆聽為你舉行新法王坐床大典的消息。 我們今天所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成為歷史,而歷史只有留待後人去評說。但別因此就為所欲為,因為不管後人如何評說,無欺之因果才是最嚴厲也是最終的審判官。而因果自負,所以務必多加慎重! 蕭平實說:佛性須以眼見為憑,……見性應以肉眼親見佛性為憑,……「佛性非天眼所能見」除系依佛語外,亦依實際證量而言。我會中同修亦有得天眼者,受菩薩戒後隨余修學六月,終未能見佛性,復回神道教中。若不學大涅槃經,而雲天眼能見佛性者,無有是處。 答: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知,有些人可能連一些基本的佛法名相都未能搞明白,在這種前提下還要沐猴而冠、好為人師,處處以佛教權威解釋者的面孔自居,就實在是有些不倫不類、勉為其難了。 一般而論,肉眼有兩種解釋:一是指凡夫的眼根,二是謂「五眼六通」中「五眼」之一的肉眼。《金剛經》中曾提到過所謂的五眼,其中就包括了肉眼與天眼。《現觀莊嚴論》第一品中就有涉及「五眼六通」的內容(很明顯,蕭先生是把五眼與六通的功德混為一談了。);第二品教言品中則專門從因、作用範圍、類別等幾方面解釋五眼。此論以教量抉擇道:資糧道之菩薩開始具有肉眼,資糧道以上之菩薩相續中都具足。而別的一些論典中則具體闡釋道:肉眼是在加行道時通過供燈、修等持而獲得的,依靠肉眼可以現見一百由旬到三千大千世界整個世間內的方方面面。 儘管在敘述上略有差別,但一般而言,佛教經論基本上公認:天眼的功德遠遠超越肉眼。一些論典中認為修禪定等六度才是具足天眼之因,憑天眼可以照見十方所有眾生前生後世、投生受生的具體情況。依道地而論,加行道以上的人相續中方才具足天眼之功德,此功德通過修持有漏善法而獲得。 若按照以上標準來衡量,則蕭先生會下一具足天眼者卻無法眼見佛性,唯有具足肉眼者方能眼見佛性,則天眼、肉眼之順序豈非要前後顛倒?一般而論,得天眼者若具足肉眼,(按次第遞進之規律,這是必然的。)則他必能見佛性;若不具足,則他是否如《楞嚴經》中阿那律所言:「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 如果蕭先生所謂的「肉眼」非是「五眼」中的肉眼,那麼我們就只能把此處的肉眼理解成是普通凡夫的眼根了。若真是這樣的話,那他論點中的漏洞就更大。儘管他本人在《護法集》中曾引用過《大般涅槃經》中的幾句話(見一百七十一頁),但不知他看過沒看過,或者說理解不理解此經卷八中的這一句話:「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雖然經中亦有迦葉菩薩問佛:「佛性微細難知,雲何肉眼而能見?」佛對此回答道:「聲聞緣覺信順如是大涅槃經,自知己身有如來性,亦復如是。」但此處重點宣說的根本就不是以肉眼見不見佛性的問題,而是通過「信順」佛語從而堅信自身有如來藏的問題。 此經文明示:眾生皆具佛性,然佛性細微難察,凡夫位不見,有學道時以誠信而可了達其總相。十地菩薩亦只是片面了知,唯佛陀才能以具備如所有智、盡所有智之佛眼洞見佛性。倘若依此而認為肉眼可看見佛性,則此實為錯謬之談,因經中明確告訴我們:聲聞緣覺依此經而起勝解,並信受自身具有佛性之說。否則的話,應將經文改成「自見己身有如來性」了。 再者學過因明、唯識、俱捨的人都知道,肉眼所見之對境為色塵,而佛性乃無為法,絕對不可能被色法涵蓋。假若佛性真的可以依肉眼見之,那麼請問它的長短、大小、形狀、顏色又如何? 憨山老人在《<金剛經>決疑》中也曾提到過五眼的問題,他對此的解釋是:「空生疑佛具五眼,將謂有法可見,有世界眾生有情。世尊告以所具五眼非眼也,但約見眾生心為眼爾。」藕益大師在《<金剛經>破空論》中亦云:「夫五眼者,能照之知見也。」從中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裡所說的「眼」哪裡是指肉眼!這五眼均為眾生本具之功德,通過信解佛經、努力修持、戒定慧次第升進,一定可以將之顯發出來。若把經中所言的眼見佛性理解成肉眼見佛性,只能說持此說者混淆了五眼與六通、肉眼與五眼及「心眼」、照與見之間的界限、關聯。《涅槃經》中對此說得非常明瞭:「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瞭;佛眼見故,而得了了。」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不論是肉眼、天眼還是慧眼,都無法「眼」見佛性,只有佛眼才能將之了了分明地一覽無餘。 為了掩蓋自己論點中的致命缺陷,蕭先生又在別處提出所謂的「綜合肉眼說」。即他認為眼見佛性之眼除了包含眼根外,尚綜合了從心到如來藏一系列器官、心意識乃至佛性等或精神或物質或超離言說的種種實體與非實體之活動、功能。這種論調依然掩蓋不了其本質上的錯誤,一個非常淺顯的反駁理由是:在「綜合肉眼見佛性」說中,肉眼發揮不發揮根本作用?如果發揮根本作用,則我們已在上文破斥過此種觀點;如果肉眼不發揮決定性作用,那麼僅以肉眼結合如來藏為例,如此說成立,則有如來藏自己見自己之過。如來藏在什麼樣的對境下可以見到如來藏?肉眼見不到佛性,佛性自身也無法見到佛性,以此理推之,人人手中都沒有一分錢,這樣的人即就是湊足一千個,依然湊不出一分錢。「綜合見性說」的漏洞也就在這裡。 另一方面,根據《俱捨論》的觀點,眼識的產生需要具備三點條件:外境、眼根以及作意。剎那間具足這三點,隨後眼識便告產生。如果如來藏要見如來藏的話,那麼它又是如何作意的?最後再強調一點以正視聽:按照因明的觀點,五根識皆為現量親見、親聞、親觸等,若肉眼能見,當為現量了了而見。但佛陀在經典中早已說得清清楚楚,十地菩薩都不可能現量了了親見佛性。既如此,凡夫雲何得以憑肉眼就親見佛性? 既無教證,也無理證,看來我們又得問一句老話了:這到底是在闡發經義,還是在大肆宣揚自己的分別念?
蕭平實說:有謂《大智度論》所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為中道。」,乃是說緣起性空,謂緣起性空即是中道。然而此種解釋乃依二乘法而解釋龍樹菩薩之中道,實非中道,何以故?以緣起性空所顯一切理,皆依有為法之現象界而言;現象界之一切有為法悉皆不離緣起性空,是則一切皆屬無常,終歸於空無;此則無性,不名空性,名為無常性;既性無常,不名中道,此非大乘《大般若經》、《大般涅槃經》、《楞伽經》、《楞嚴經》、《圓覺經》、《維摩詰經》、《法華經》所說之中道也。 答:蕭平實先生認為緣起性空非為大乘中道、人們錯解了《大智度論》以及龍樹菩薩之密意,對此可破斥如下: 般若經典、《大智度論》所闡釋的皆為大乘緣起性空之成佛之道,非為成就聲緣羅漢之二乘法。般若經中一再強調:從色乃至一切智智,萬法皆無實有性,都為本體不恆存的自性空,萬法之自性當下即是空性。對此,《大智度論》引用佛語已將這一觀點表達得異常清楚:「舍利弗,色、色相空,受、想、行、識、識相空;檀波羅蜜、檀波羅蜜相空,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如是。內空、內空相空,乃至無法有法空、無法有法空相空。四念處、四念處相空,乃至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相空。如法性、實際不可思議性,不可思議性相空。三昧門、三昧門相空,陀羅尼門、陀羅尼門相空。一切智、一切智相空,道種智、道種智相空,一切種智、一切種智相空。」《中論》中同樣直接指出一切法本來為空的道理:「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回諍論》中亦云:「我無承認故,我即為無過。」這些經論統統都在表明:不僅有為法是空性,即就是無為法,包括如來藏、佛之功德、涅槃等,其本體依然為空,但在顯現上則恆常具有、無欺存在。 不過蕭先生卻似乎不這樣認為,在其所著的《狂密與真密》一書中,先生即如是論述道:「當知一切有情所知之心及覺知性,皆不能外於名色而獨存;能外於名色及一切法而獨自存在之心,唯有第八識如來藏(此識於凡夫及解脫道之有學位中名為阿賴耶識,無學位中改名為第九識異熟識,佛地改名為第十識無垢識,亦名真如。未至佛地之前一切位中總名如來藏)可以離於一切法而單獨存在,其餘一切識皆不能外於諸法而單獨存在。」且不說在這幾句話及先生的所有著作中一犯再犯的將如來藏不加任何區分地等同於阿賴耶識這類錯誤,單就其認定如來藏或阿賴耶識可離於一切法而單獨存在這一觀點即可看出:蕭先生顯然堅定地認為如來藏或阿賴耶是實有的,因只有實有法才談得上不觀待一切因緣。如果我們沒有歪曲平實先生原意的話,則以下結論的推出當屬必然之結果:這種將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當成不依賴於任何外在之法的實有存在,與外道所謂的常有不變的「神我」實無絲毫本質差別!儘管先生拼盡全力、毫不「嘴」軟地痛斥別宗,特別是密宗的某些宗派為常見外道,奈何自己的觀點卻真正與常見外道不謀而合,這多多少少會讓人產生一種看某些人自扇其臉的感覺。執著了如來藏或阿賴耶的實有,然後再來大談中道,這無論如何都有點自相矛盾的味道。因所謂中道必須破除一切邊執,牢牢執著如來藏的實有之人,又怎可能了知諸佛菩薩宣講中道的密意?雖說在《邪見與佛法》中,先生曾懇請諸方大德「莫因愚之舉陳『如來藏實有』,便責愚為『執著如來藏』,愚意乃在辨正此第八識實有,教化佛門中之斷滅論者回心,純為佛教正法著眼,無著可言。」但我們還是要責其執著如來藏,因只要承認法界中有不空的成實法,對此法的執著便決定無法消除。既如此,中道又從何談起?只有破除了一切法的實有,包括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的本體實有,中道才有可能現前——如果說中道有密意的話,恐怕這才是它本具的密意。若非如是,則以上經論應在破除了一切法的成實性之後,再來安立阿賴耶識、如來藏的成實性,如此方才符合他本人對龍樹菩薩密意的「挖掘」——「龍樹此偈乃闡釋大乘般若空性,非謂五陰及諸現象界之空相;乃謂如來藏之中道空,非謂二乘法中緣起緣滅之空相。真實中道觀者真如佛性也,……以此智慧而斷遍計執性。於一切緣起緣滅之依他起性中,證得如來藏之非有非無中道空性——圓成實性;方符龍樹此偈本旨、真實證驗中觀,不墮二乘無常法中,……」不過,不論是般若經還是龍樹論,在破析了萬法實有、建立了真實中道之後,都沒有再提出過存在一個不空的阿賴耶識或如來藏的觀點。順帶說一句,看來先生始終不解佛陀於第三轉法輪期間所安立的如來藏之「有」,與第二轉法輪期間所破除的萬法之「有」到底有何區別,一如先生籠統地將如來藏與阿賴耶識劃上等號一樣。 另外,若按照蕭先生的論斷來分析,則斷除了遍計執即為非有,而留下緣起緣滅的依他起則謂非無,如此即成為四邊戲論中的第四邊「非有非無雙俱邊」。這樣一來,不僅這兩邊戲論未被斷除,而且依此理推之,有邊、無邊的執著也未被放下,這就直接與《中論》中的論述「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相違背,這又如何能被稱之為中道? 下面再從蕭先生的諸多文章中摘取一例,以令大眾更進一步理解先生眼中的中道或曰空究竟是何景觀。 先生曾把如來的解脫空理解成如「人去樓空的村莊、枯竭的河川、瓶中無水,並非沒有了村莊河川瓶子,由於其中已經虛無了,所以說是空。」依憑《楞伽經》的論證,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所謂的「解脫空」與說經堂裡沒有人、馬上沒有牛一樣,都是最低劣的一種空。此經中云:「大慧,譬如鹿子母捨,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捨捨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余處無象馬,是名一切法自相,是名彼彼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當遠離。」既然此經中已經明白揭示了空的真實含義,如果再按照蕭先生的論述看待佛陀的解脫,則有無上正等正覺之佛陀所證悟的竟然是最低劣的空這種過失!可能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法界當中依然存有不滅的山川河流與瓶子吧。 如來根據不同眾生的根基而分別闡揚了八萬四千法門,其三轉法輪的究竟密意依然是針對所化眾生的不同根性而相應施與了義或不了義之教授。只有在理解了這個大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既不割裂三轉法輪的整體性,又能清楚了知究竟說法與不究竟說法之間的區別,從而力斷籠統含混、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錯雜混亂等過失。我們必須瞭解,第二轉與第三轉法輪既本體相通,同時又反體有別,只有這樣才能把如來藏與空性完美地統一起來,否則都不可能達於中道。 個別人總是要把緣起性空當成空無之斷滅來理解,但這兩者之間實有天大的差別。空無之斷滅是謂先有後無;而緣起之萬法其本性就是空性,正因為空所以才可依各種因緣而得以顯現。認為緣起緣滅是無常性、非中道的觀點是否是真正的斷滅見,智者當以經教自己衡量,因緣起緣滅闡發的恰恰就是遠離有無執著的中道觀。解釋般若經典及龍樹之論的意旨,如果只憑借凡夫的分別念,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師心自用、難以契入佛經堂奧。對於無師自通之人的那些未經過印證的種種說法,我們只可以一家之言、一得之見待之,真要奉之為聖旨,那就只能說明自己眼界太狹窄了。
蕭平實說:密法是將印度教的教法及印度教性力派邪說與「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混合起來的一個宗教。 答:密法是純正清淨的佛法,絕非附佛外道。談到密法的來源,大量的經教都指出:一部分密法內容是釋迦牟尼佛住世時親口宣說,比如於印度南方哲蚌米積大塔處宣說《文殊真實名經》、《時輪金剛續》等,又在烏仗那國宣說《密集金剛》等續部經典;還有一些則是釋尊以不同身相、不同方式在不同剎土為不同的所化眾生分別敷演的。這些在別的剎土被佛陀宣講過的密宗妙法,其後又通過種種方式輾轉流傳至人間。其中關於五持明於佛涅槃若干年後從某位菩薩那裡接受普賢如來於法界所傳密法的內容,以及佛陀在某些經典中授記蓮花生大師將於未來出世廣弘密法的具體經過、細節,還有多種密法傳承次第的分別介紹,我們會在下文或者別的一些專著中行文描述,這裡就不再展開論述了。 將密法定義為是一種印度教、性力派邪說再加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混合而成的大雜燴,這種說法的得出想必是對密宗知之甚少的結果。這也情有可原,因藏文《大藏經》中多達二十餘函的密續只有少數被翻譯成漢文,而系統、全面、客觀、正確介紹密宗的論典與著作也少見問世。因此對一個或許多不懂藏文的人來說,缺乏對藏傳佛教的瞭解也並不為過。但無知不應該成為值得炫耀的資本,如果把因無知而得來的偏見再當作真理到處宣揚,這種做法就有些令人生厭了。 僅僅只是聽說了一些雙運、護摩、降服等對普通人來說似乎略顯陌生的名詞,從而就把密宗與在其論典中也出現過這些名相的印度教劃上等號,這種論調恐怕有失偏頗。非常明顯的一個例證是,佛陀在三轉法輪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宣說小乘及大乘顯宗的時候,都曾用過一些外道同樣也在使用的名詞術語,諸如五蘊、八識、人天善果等,如此說來,是否顯宗也應從此被更名為附印度教或婆羅門教之外道了呢?賦予共同名詞以嶄新含義,這本來就是佛法有容乃大的表現之一,也是佛法超越一切外道及世間思想之所在,豈能以名詞相同就認定其背後的指導思想也相同。再比如六度中的佈施度、持戒度、安忍度等說法,很多外道及世俗倫理、道德體系中也有關於此方面的內容,但每一個正信佛教徒都不會因此就把佛教曲為比附於任何外道,佛教在六度思想背後的顯空雙運的究竟底蘊,你在所有的非佛教之宗教中都了無覓處。 而且從歷史來看,佛法傳入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期間也出現了不少依附佛教的外道與邪教,它們不僅抄襲了不少佛教名詞,還偽造了一些經典,甚至搬出佛教中的很多佛菩薩為自己裝點門面。不過這些真正的附佛外道的最終結局卻大致相同:雖然可以欺騙得了一時,終究還是要被人們看破其廬山真面。這也給了我們一點啟示,如果密法真是借用佛法名相的一種外道宗派的話,為何獨它能綿延千餘年而至今仍長盛不衰?難道密法的欺騙性就那麼大,以致能始終混在佛教隊伍中不被人們踢除出界? 客觀說來,從密法誕生直到現在,歷朝歷代都不乏對它橫加指責之人。這些人既包括了教內人士,也涵蓋了世間智者。但不論他們是從佛理出發,還是從世間哲學、倫理或科學的角度展開對密法的圍剿,迄今為止,尚未有一人能提出駁倒密法存在理由以及其作為佛法正統分支的根據。也許幾千年中都未曾誕生過像蕭平實先生這般聰明絕頂的人物,其一人之力足以抵得上無數前驅者的智慧與努力。不過這無論如何都令人難以置信,因我們實在看不出此人卓絕的智慧到底體現在哪裡。 他自己認為密宗儘管引用了佛法名相的理論,但與佛法絕對不是一回事。在《甘露法雨》中他如是評論道:「這種引用佛法名相的理論,和佛教中所說的正遍知覺,完全不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人還是懂得引用者與被引用者並不能同日而語。不過他的標準卻是兩重性的:只要密法中出現與外道相同的一些詞句,那麼不管密宗在本質上如何與它們不同,蕭先生也必須把密法與外道等同起來;除此之外,他對借鑒、引用與被借鑒、被引用以及共用之間的關係還是涇渭分明的。這種極具兩面性的判定指南只能讓我們感到,某些人心中的偏見已徹底扭曲了他自己的認識公平度。 現代人如若想走進密法並進而評論密法,唯一的方式只能是充分地瞭解、研究、修習密宗,其依據應該是浩如煙海的經續及祖師大德的論著;其皈依處應該是具相上師;其可靠的途徑則是聞思修,捨此別無他途。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既不要盲從對密法一無所知且滿懷不知從何處來的憤恨者的話語,也不能依據沒有傳承、通過抄襲、拼湊而成的文字,當然也不應把所謂的考證、純學術化的宗教學研究以及心理分析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 有一點很是讓人費解,即蕭先生一方面大力痛斥密法,一方面又通過神通借助禪定及睡夢得知,自己過去世曾當過密宗覺囊派的修行人,甚至是教主。這樣矛盾的說法的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是在誇耀自己的神通,還是誇耀密宗的覺囊派?或者在他眼中,覺囊派根本就不屬於密法,與另外幾大密宗派別實有天壤之別?如果這後一種說法能成立的話,這倒是一千古奇談,因不論是覺囊派本身還是密宗的其他所有教派,無不公認覺囊派是純正的密法,而且是極具藏地本土特色的密法流派。難道作為覺囊派曾經的一派之主,蕭先生現在在禪定中或夢境裡竟沒看出來這一點? 有一點常識我想我們都應該知道,即密宗有著非常嚴格的傳承系統。藏密五大教派的祖師均源於印度,如寧瑪巴的蓮花生大師、噶舉派的帝洛巴尊者、薩迦派的布瓦巴尊者、覺囊派的月護、噶當派的阿底峽尊者,這些人全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們創立的宗派也都不是空穴來風,只要查閱各派的祖師傳承年表、歷代祖師傳記即可一目瞭然。不過在《宗通與說通》中,蕭先生卻千古獨步般地論說道:「至於覺囊巴,並非密宗初始即有之教派,法道亦異紅白黃花四大派。」在這裡,他生硬地將覺囊從藏傳佛教的整體系統中割裂開來,實則沒有任何教證理證的根據。 眾所周知,不動金剛(彌覺多吉)於十一世紀中葉創立了他空見,其後經法自在、虛空光等傳至土傑尊珠,他於拉孜縣東北建立起覺摩囊寺,簡稱覺囊,從此該派即以寺名。在傳至堆波瓦·喜饒堅贊後,此派遂大興於世。其有羅追貝、喬列南傑、薩桑瑪底班欽等著名弟子,後兩人曾為宗喀巴大師之上師。公元十六世紀,此派大喇嘛由轉世相延續,其中定為袞噶卓喬轉世的多羅那他名聲最著,使該派一度中興。 既然蕭先生說過:「雖然我今生沒有學密,但過去世我也在密宗覺囊派待過一兩百年,也曾是一派之主。」那麼對這些關於自宗的歷史就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我想你這個一派之主的禪定功夫再怎麼不行、睡得再怎麼沉沉不醒,對這一點歷史事實大約還是應能回憶起來的:即覺囊派主要是從印度的無著菩薩、旃陀羅閣彌等聖者那裡汲取了其顯宗部分的立論之基——中觀他空見;又於《時輪金剛續》中擷取了自身的密法精華。而《時輪金剛續》以及無著菩薩等聖者,皆被密宗所有宗派共同承認且一致作為自己的實修之有機組成部分及理論導師,因此把覺囊派與別的四大教派截然分開顯然不合理。而且最關鍵的問題是,《時輪金剛續》分明是釋尊親口宣說,如果蕭先生還認為自己當過覺囊派法王的話,那他就必須承認所有密法教派的合理性!否則自己豈不成為了一個外道之王?還有什麼理由在這裡以佛法的捍衛者自居? 但蕭先生卻在《邪見與佛法》中如是說道:「密教第四種誤會:時輪金剛的無上密續。這就是時輪金剛最後階段的父續與母續——喜金剛……這都是屬於男女兩性的雙身合修法,是移植自印度教裡的密法,是密宗金剛上師與異性弟子間永遠的秘密。」將自宗的根本續貶低為與世間凡夫之男歡女愛同屬一個檔次的法王,翻遍密宗歷史也查無此人!可能是在蕭先生擔任覺囊法王期間,才開始大規模地引進印度教的性力派邪說吧。在這裡我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任何人在任何有關覺囊派的歷史著作中都找不到否定自宗密法修煉之基的法王存在。這麼說來,人們不得不產生一個疑惑——到底是蕭平實先生在篡改覺囊派歷史,還是他本人的禪定功夫出了偏差?抑或他自己根本就不懂什麼才是真正的時輪金剛修法?古人有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許先生自己浸淫在性力派的學說中太過沉迷,以致不辨東西、難以自拔,故最後便把自己對男女性愛的狂想硬塞進與以凡夫貪心為基礎的世間情愛毫無關聯的密宗之中? 而且《狂密與真密》中還如是說道:「近年因閱讀《土觀宗派源流》一書之後,於定中及夢中漸漸引出往世在覺囊派中二世任法王……」擔任了兩世的法王,那串習應該相當深厚了,何以如今不僅不幫助我們這些普通的密宗行者弘揚密法,反而更要對密法斬盡殺絕?這種巨大的反差不能不讓人懷疑你說的是大妄語。 如果真在這件事情上打了妄語,則《賢愚經·長者無耳目舌品》中的一段公案當足資言妄語者借鑒。那個名為檀若世質的平事,因未秉公執法、在一件需他作證的事情上沒能說實話,結果竟轉生成一個生下來即沒有眼、耳、嘴、舌及手腳、一片混沌只有男根的人。這還只是不說實話的果報,若進而顛倒黑白、謗法謗僧,其罪報恐怕就非常人所可想像了。況且先生自己也曾說過:「果報真是厲害;……若沒有證據,絕對不敢再輕易評論任何善知識。」既如此明理,那就請先拿出《時輪金剛》非佛所說、覺囊派法王從未修過此種大法、覺囊派非屬密宗體系等相關論點的證據,然後再給眾人講解自己的夢境吧。 翻開覺囊的歷史一查,則所有覺囊法王都是與時輪金剛有甚深因緣的大成就者。不過不知蕭先生知不知,雙運修法就是釋尊在《時輪金剛》中重點宣講的。你如果學過密法、懂得藏語的話,一定能了知此點。而你不僅否定了所有密法,更對密法中的雙運修法大加鞭撻,以為其是淫蕩的代名詞。既如此,我們就有些不明白了,覺囊派沒有一個法王不修《時輪金剛》而成就,而它的內容已如上說,但你又最痛恨雙運修法,那你成的到底是哪一位覺囊法王?你當法王時修的都是哪些獨特大法?請再顯神通,為我們道上姓名來,好讓我們對照著覺囊的歷史一一查看一下。好在覺囊的歷史並不是很長,如果你報上姓名,核對一下大概花不了多長時間。 大部分覺囊派的寺廟在十七世紀中葉時就已基本上歸屬於格魯巴了,以至於現在的康區一帶極少有其所屬寺廟存世。眼見這種景觀,難道你作為一派之主竟無動於衷?不久前,受人恭敬的覺囊一代法主雲丹桑布不幸圓寂,不知蕭平實先生有沒有動過再掌覺囊大印、重振覺囊雄風的念頭?有時在腦海中情不自禁地就會浮現出這樣的一幅畫面:蕭先生頭戴時輪金剛佛冠、高坐他空見寶座上、手裡還拿著被他自己譏諷為是性力派法器的金剛橛及鈴杵,正在給眾人宣說非密宗之自創宗派教義。這該是多麼值得被寫進世界佛教史上的一頁畫卷!如果蕭先生真有這樣的雄心壯志,那我將側耳聆聽為你舉行新法王坐床大典的消息。 我們今天所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成為歷史,而歷史只有留待後人去評說。但別因此就為所欲為,因為不管後人如何評說,無欺之因果才是最嚴厲也是最終的審判官。而因果自負,所以務必多加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