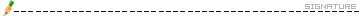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 ||
前晚三名死刑犯槍決後,捐出不少器官與組織,意外的是,仍有一名北部等待換腎的患者獲知,可接受移植的腎臟來自死刑犯,最後決定放棄。 當年殺害白曉燕的陳進興伏法後捐出肺臟,但有病患因不願變得「狼心狗肺」,拒絕陳進興的肺,當時學者洪蘭即表示,台灣民眾太缺乏科學常識。昨天又有人拒絕移植死刑犯的腎臟,洪蘭大嘆,「台灣的科學教育還要加把勁」。 三名生前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的死刑犯,前晚伏法後,火速被送往醫院,醫護人員摘下他們的心、肝、腎、胰臟、眼角膜、血管和骨骼等器官和組織後,再移植到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身上,心急如焚的患者和家屬有如大旱獲甘霖。 不過,卻意外出現一段插曲。移植醫師透露,一名排在移植第一順位的患者,被醫院通知可換腎時,患者卻說:「不要這顆腎了!」原來,患者得知腎臟是來自死刑犯,就決定不要,醫護人員只好在大半夜裡,緊急通知其他醫院,把已處理好,馬上可植入的腎臟,轉給第二順位患者。 根據器捐登錄中心規定,拒絕接受這顆腎臟的患者,須重回等待名單,在沒有其他人等待時間更長時,才有機會再獲贈腎臟。振興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治醫師陽厚生說,腎臟、胰臟衰竭患者敢拒絕,可能因為暫時仍能依賴洗腎等治療,不像心、肺衰竭,等著救命的患者,幾乎是「倒數計時」,無論是何處來的心臟,「最後一根稻草也得抓」。台灣移植醫學會理事長、成大醫學院外科教授李伯璋說,過去的確有不少患者,拒絕死刑犯器官,儘管時間緊急,還是琢磨再三。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當年曾為一位等待肺臟移植的女士,拒絕陳進興捐贈的肺,因為那是「狼心狗肺」,最後因等不到其他人的肺而死掉頗多感觸。 「肺是幫助你呼吸的器官,一個人行為好壞是腦子管,怎麼會是肺呢?」那件事讓洪蘭很震撼,感嘆台灣的科學教育到底教到哪去了,十幾年過去了,昨天洪蘭聽說又有第一順位的等待移植者拒絕死刑犯器官,她不假思索說,若透過血液就會傳染另一個人的個性,那全球每天成千上萬接受別人捐血的病患,豈不都變了另一個人?「為何大家都不怕?」 「接受移植心、肺、腎等器官,其實不會把捐贈者的個性也移植到體內,兩者沒有關係。」洪蘭感嘆,台灣的科學教育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2011/03/06 聯合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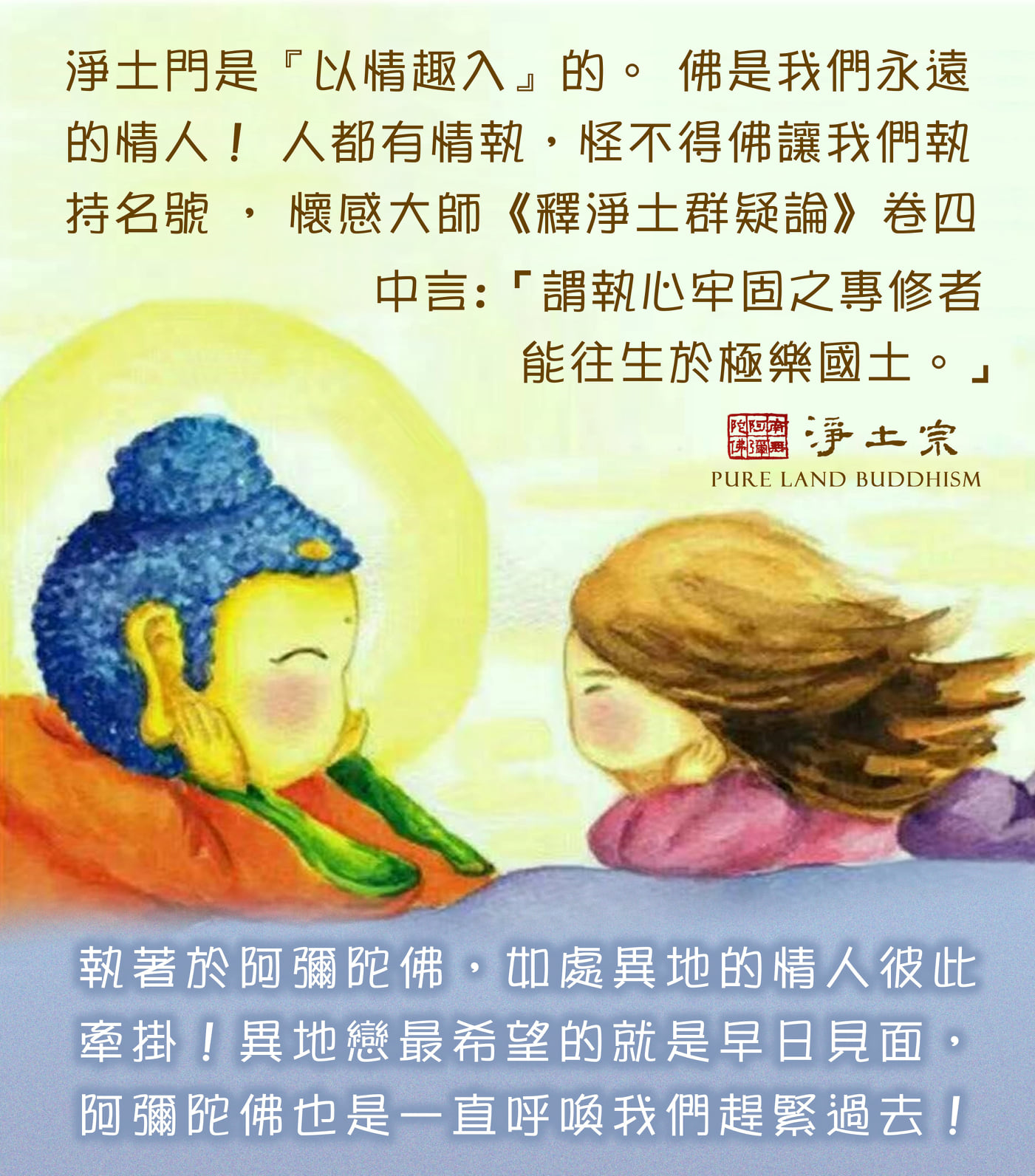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