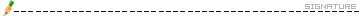在天下觀里,大清朝是“中國”。可在世界觀里,地球是圓的,“中國”在哪里?
《大清一統志》里的“天下”,在世界地圖上,被經緯度瓜分了,“中國”不再居天下中央,而是同世界各國一樣,被限定在經緯度里。在經緯度的世界里,産生了地緣政治,國與國之間的邊界,不是大喝一聲“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就能確定的,要坐下來算。
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何況無算乎!”在天下觀里自慰的清王朝,在世界觀里卻無算。
到了晚清,西洋潮來,清之應對,遠不如明,乾隆帝不如萬曆帝,林則徐不如徐光啓,張之洞“中體西用”,何如徐光啓“中西會通”?
洪鈞在歐洲呆了三年,混得比郭嵩燾好多了。他知道,像郭嵩燾那樣,向西方學習,那是自討苦吃。還在德國時,他就開始研究元史。為此,他還專門請了一位比利時人,幫他翻譯史料。囘國以後,官場應酬之餘,他就著手寫《元史釋文證補》。
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力氣來研究元史呢?這里面有政治。元以異族入主中原,清亦如此,以元史為正統,還是為異端?牽涉到對大清朝怎麽看。
清初經略西北,然其抱負,卻非緣起於漢唐,而是來自元史。因此,朝廷提倡研究元史,大凡有點天下觀抱負的人,都要懂得西北地理。當年,林則徐“睜眼看世界”,在天下觀里看,看不慣。可他在西北找到了感覺,翻譯世界地理,名曰《四洲志》。“四洲”乃佛家語,以此翻譯,又使世界回到天下觀里。“四洲”有如四方,有四方必有中央,以此類推,有“四洲”亦當有“中州”。何謂“中州”?自然以“中國”為“中州”,以“中國”為神州。
他把未竟之稿,托付魏源,而將未竟之業,托付給左宗棠。
他看好湖湘人物,以為將來天下,要湖湘文化擔待。後來,魏源編著《海國圖志》,用天下觀寫世界地理,左宗棠西征,坐實了西北地理。可惜了西征,半路而止,其豐功偉績,還是不如元史。
在新疆伊犁之西,科布爾之南的帕米爾一帶,中俄之疆界,久不分明。洪鈞講西北輿地之學,最弄不明白的便是這里,不能言其究竟。
出使俄國時,有人拿出一張中俄國界圖來,山川道路,條列分明,他喜出望外,以為找到了劃分邊界的證據,當即出重金,買下地圖。請人譯成中文,在德國柏林印書局刻印,報送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也很高興,以為找到了劃分中俄邊界的憑證。誰知俄國人在國界圖上,對帕米爾高原一帶做了手腳,他沒有看出來,因而鑄成大錯。他像蔣幹盜書一樣,偷偷摸摸的行徑,送了他一命。
他回國後,在總理衙門行走,有一天,英國公使來了。氣沖沖問道:何以好端端的,要割地數百里給俄國?
他不知所雲。後經英國公使解釋,才知俄欲以帕米爾南窺印度,與英衝突。英方認為,如帕米爾仍屬中國,形成緩沖,俄就不能南下。
總理衙門奉命,查明了原因,就向俄國公使提出抗議。
不料,俄公使却取出那張洪鈞譯制的“中俄交界圖”,正是在那份地圖上,帕米爾被劃入了俄國疆界。他又氣又惱,羞憤交加,病倒了。
晚清政治,有兩大笑柄,一是張佩綸好談兵,卻聞戰逃命。另一就是這位洪鈞,自詡西北地理,卻找不到“北”在哪里。
可滿朝文武,又有幾人知道帕米爾高原的經緯度?誰知勘定國界,最終要劃分經緯度呢?經緯度上略微偏移,在地面上一劃就是幾百公里。就算洪鈞上了俄國人的當,可朝廷呢?那麽多飽學之士,誰又能發現圖上有錯誤?如果不拿這張國界圖,朝廷還真不知要拿出怎樣的疆輿圖。大家都罵他糊塗,可罵他的人里面,有幾人真的清楚?
明朝人是看世界的,利瑪竇來時,就帶來了世界地圖,還教會了明朝人怎樣劃分經緯度。緯度,中國人早就懂了,而經度,是利瑪竇教的。
誰知,到了清朝,這些都成了亡國的經驗教訓,被統治者忘了。本來大清朝在《大清一統志》里高枕無憂,可沒想到,還是中了夷人的招。
薛福成是明白人。洪鈞從德國回來時,他剛好要去英國,出任駐英國公使。他在稿本上有一段話,說清楚了帕米爾高原上那塊地的經緯度。
他說那塊地,緯度“自赤道北緯三十六度四十五公分起,三十九度四十五分止”;而經度“居京師西四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四十七度零八分止”。在地上勘出來,有縱三百公里,橫四百六十餘公里的面積。
當時,熟知洋務者,除了曾紀澤已死,就是這個能說清帕米爾高原之地經緯度的薛福成。而洪鈞辦外交,不過是以西北地理,來濫竽充數。
《大清一統志》里的“天下”,在世界地圖上,被經緯度瓜分了,“中國”不再居天下中央,而是同世界各國一樣,被限定在經緯度里。在經緯度的世界里,産生了地緣政治,國與國之間的邊界,不是大喝一聲“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就能確定的,要坐下來算。
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何況無算乎!”在天下觀里自慰的清王朝,在世界觀里卻無算。
到了晚清,西洋潮來,清之應對,遠不如明,乾隆帝不如萬曆帝,林則徐不如徐光啓,張之洞“中體西用”,何如徐光啓“中西會通”?
洪鈞在歐洲呆了三年,混得比郭嵩燾好多了。他知道,像郭嵩燾那樣,向西方學習,那是自討苦吃。還在德國時,他就開始研究元史。為此,他還專門請了一位比利時人,幫他翻譯史料。囘國以後,官場應酬之餘,他就著手寫《元史釋文證補》。
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力氣來研究元史呢?這里面有政治。元以異族入主中原,清亦如此,以元史為正統,還是為異端?牽涉到對大清朝怎麽看。
清初經略西北,然其抱負,卻非緣起於漢唐,而是來自元史。因此,朝廷提倡研究元史,大凡有點天下觀抱負的人,都要懂得西北地理。當年,林則徐“睜眼看世界”,在天下觀里看,看不慣。可他在西北找到了感覺,翻譯世界地理,名曰《四洲志》。“四洲”乃佛家語,以此翻譯,又使世界回到天下觀里。“四洲”有如四方,有四方必有中央,以此類推,有“四洲”亦當有“中州”。何謂“中州”?自然以“中國”為“中州”,以“中國”為神州。
他把未竟之稿,托付魏源,而將未竟之業,托付給左宗棠。
他看好湖湘人物,以為將來天下,要湖湘文化擔待。後來,魏源編著《海國圖志》,用天下觀寫世界地理,左宗棠西征,坐實了西北地理。可惜了西征,半路而止,其豐功偉績,還是不如元史。
在新疆伊犁之西,科布爾之南的帕米爾一帶,中俄之疆界,久不分明。洪鈞講西北輿地之學,最弄不明白的便是這里,不能言其究竟。
出使俄國時,有人拿出一張中俄國界圖來,山川道路,條列分明,他喜出望外,以為找到了劃分邊界的證據,當即出重金,買下地圖。請人譯成中文,在德國柏林印書局刻印,報送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也很高興,以為找到了劃分中俄邊界的憑證。誰知俄國人在國界圖上,對帕米爾高原一帶做了手腳,他沒有看出來,因而鑄成大錯。他像蔣幹盜書一樣,偷偷摸摸的行徑,送了他一命。
他回國後,在總理衙門行走,有一天,英國公使來了。氣沖沖問道:何以好端端的,要割地數百里給俄國?
他不知所雲。後經英國公使解釋,才知俄欲以帕米爾南窺印度,與英衝突。英方認為,如帕米爾仍屬中國,形成緩沖,俄就不能南下。
總理衙門奉命,查明了原因,就向俄國公使提出抗議。
不料,俄公使却取出那張洪鈞譯制的“中俄交界圖”,正是在那份地圖上,帕米爾被劃入了俄國疆界。他又氣又惱,羞憤交加,病倒了。
晚清政治,有兩大笑柄,一是張佩綸好談兵,卻聞戰逃命。另一就是這位洪鈞,自詡西北地理,卻找不到“北”在哪里。
可滿朝文武,又有幾人知道帕米爾高原的經緯度?誰知勘定國界,最終要劃分經緯度呢?經緯度上略微偏移,在地面上一劃就是幾百公里。就算洪鈞上了俄國人的當,可朝廷呢?那麽多飽學之士,誰又能發現圖上有錯誤?如果不拿這張國界圖,朝廷還真不知要拿出怎樣的疆輿圖。大家都罵他糊塗,可罵他的人里面,有幾人真的清楚?
明朝人是看世界的,利瑪竇來時,就帶來了世界地圖,還教會了明朝人怎樣劃分經緯度。緯度,中國人早就懂了,而經度,是利瑪竇教的。
誰知,到了清朝,這些都成了亡國的經驗教訓,被統治者忘了。本來大清朝在《大清一統志》里高枕無憂,可沒想到,還是中了夷人的招。
薛福成是明白人。洪鈞從德國回來時,他剛好要去英國,出任駐英國公使。他在稿本上有一段話,說清楚了帕米爾高原上那塊地的經緯度。
他說那塊地,緯度“自赤道北緯三十六度四十五公分起,三十九度四十五分止”;而經度“居京師西四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四十七度零八分止”。在地上勘出來,有縱三百公里,橫四百六十餘公里的面積。
當時,熟知洋務者,除了曾紀澤已死,就是這個能說清帕米爾高原之地經緯度的薛福成。而洪鈞辦外交,不過是以西北地理,來濫竽充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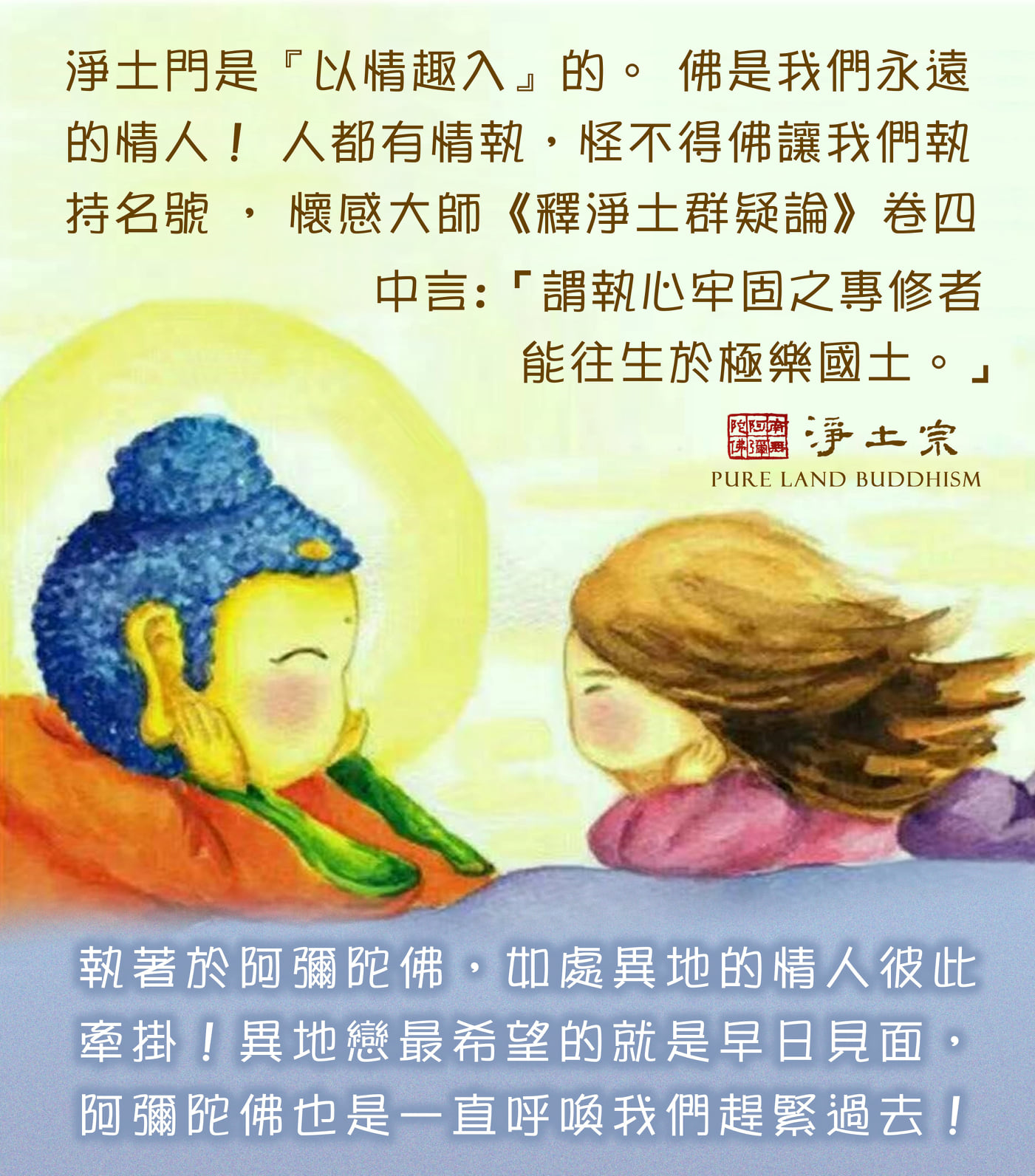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