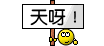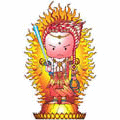當了多年護士,見慣悲歡離合,也漸漸懂得人世的無奈半點不由人,是非成敗誰判定?情真愛怨又由誰說清?
而故事一直在走廊上演,那長廊是適合等待的。
半夜兩個女人,一個閃亮如同美麗的外衣,一個緘默卻蘊含溫柔的慈悲,但都伴隨著他起舞,或者該說是他同時佔領美麗與溫柔,而情人與老婆的角色,是如此鮮明對立又模糊地存在,令人錯愕不已。
她的進來,使人眼亮,臉上始終掛著笑意,很真心、很有信心,教病人覺得安心的那種。
她的男人是急診送來的,聽說是肝癌,事先沒有一點徵兆,不吸菸、不喝酒、不打夜牌、不嚼檳榔的標準先生,說倒就倒了。
她為他換上病房規定的病患衣服,調好點滴,他不斷喊泠,她以身子溫柔地擁住他,笑著告訴他:「一會兒就會好,打完點滴,高燒便會退。」她耐心地哄著小孩般不安的他,直到他似昏似睡的不再有騷動。
我看看腕錶,清晨四點,天已微明,她一夜沒睡,守著點滴,彷彿每落下一滴水,她才有一拍心跳,她的枕畔人已滿頭白髮,她該也有四十好幾了吧!她非常客氣地請我們去換已打完的點滴,許多謝意在臉上,份外讓人不忍。
天亮透的時分,病人的燒終於退了,她為他除去汗濕透的厚被,穿過拿取不易的點滴,換上一套乾淨的病服,抹身擦澡,微笑看著甦醒的他,對他低語,哄他安心,我覺得這肝癌病人的命其實挺好的。有這麼一位老婆,該是前世修來的福吧!
她總是在中午時分回家煮些粥、湯之類的補品,下午兩、三點才再過;而這位病人卻還有個漂亮的情婦,才真叫人又羨又妒。
那位美麗的情人卻精明得在她前腳走後,後腳就跨進來,高跟鞋格格的響徹長廊,打扮入時的套裝,一張仔細化過妝的臉,和一臉的撒嬌,她還要他哄著呢!
我聽到他輕輕對她說:「我一直在等妳來呢!」同房的病人都覺得他實在艷福不淺,賢慧的黃臉婆疼他如小孩,美麗的情人在空檔立刻來陪他,他始終都不寂寞。
他的病似乎沒有送來時那麼危急,手術切除術做的還不錯,他終於可以進食、散步,甚至不久也拔除了點滴管,可以在院外走動走動了,他的老婆日夜不停地照顧他,三餐弄吃的來,削水果、送椰子汁、拿書給他看、讀報給他聽,
她活得很有勁,也把這股勁兒傳輸給他,期待他的病情受控制之後,能提起生命的勁道來和病魔抗衡,好好地活下去。
我是挺佩服他的情婦,因為她可以聰慧的算到每次他老婆走了才會過來,匆匆坐一、兩個小時,又在他老婆回來之前離去,也佩服她永遠把自己收拾的光鮮亮麗,絕不在他面前露出邋遢相,不像他老婆總是踩腳褲、寬襯衫、平底鞋、綁個髮髻在腦後頭。
有時我們也愛八卦一下,怪不得18號病床的病人愛搞外遇,老婆和情婦實在沒得比,老婆每天弄吃弄喝,陪他散步、作運動,半夜還送消夜,算是賢慧了,他還是照樣在外頭有情婦,可見得漂亮得體,永遠是男士們臣服的,賢慧又算什麼呢?
週末下午,情婦又出現了,裁剪合身的粉紅色套裝,同色系髮帶與高跟鞋,令人耳目一新,我們輕輕點頭和她打招呼,卻赫然見到她帶著一個小男孩,十歲左右,長得清秀、調皮、聰明伶俐,他見到18號病床,老遠就撲過去,親親熱熱地喊「爸!」整個人埋在他爹身上又撒嬌,又思念地哭起來,他爸也老淚縱橫,那情景,真是令全病房為之動容。
我們暗地裡笑他是「累」出病來的,享盡齊人之福,在外頭連兒子都偷生了,的確不簡單,中國人的「有後」觀念很重,情婦有本事生個壯丁,人前人後喊爹的,讓他多得意啊!也怪不得兩個女人的待遇差那麼多,一個看起來淡然的像朋友,雖然無話不談卻沒有激情,一個看起來卻像蜂蜜,即使只是蜻蜓點水的來去,卻總令他期待。
孩子跟他爹去院裡玩了,美麗女人無聊地坐在床邊翻這翻那,翻到抽屜裡的一本筆記,她一頁一頁看,美麗的臉卻開始扭曲,她把筆記啪一聲扔進抽屜,幾乎是衝到護士間來,尖叫著詢問:「喂!告訴我,我不在的時候,有誰來看過18病床的病?」
「太多啦!每天都有人來看,鮮花、水果那麼多,您沒瞧見嗎?」
護理長很得體的擋開被質問的小護士,小心地回答她。
「我不是指來探病的,我是指平時的看護,您們是不是提供了特別看護?」
「沒有呀!只是太太、媽媽、姊妹之類的親人而已啊!」
「太太?搞清楚沒有?我才是他太太,您們沒看到他兒子都這麼大了嗎?」
「啊!」護士間的七、八個護士全都嚇住了。
這兩個月來,每個護士都照顧過18號病床,也親見那女人照顧他無微不至,弄屎弄尿、擦身換衣、煮三餐的辛苦。
如果說,眼前這才是真正的太太,那麼!那麼!那個平凡而且邋遢的女人難道才是他的情婦嗎?
這樣出色的男人會找這麼平凡的情婦嗎?
「您們回答我呀!」她的美麗和尖銳的聲音構成極不協調的畫面,我們沒有一個敢說話。
還是護理長最先回過神來、禮貌的告訴她:「18號病床是重病患,您是家屬,當然是知道的,平常醫院的伙食他嚥不下,需要其他家中進補的伙食,所以他母親和姊妹就輪著送來,倒沒別的人,太太,您放心吧!他有病在身,作不了怪啦!小心,生氣多了會有皺紋哦!」
「您們這幾個年輕護士最好少動他的歪腦筋,他是我一個人的,不准妳們挑逗他!」
說完頭也不回的回病床了,長廊響起的高跟鞋聲久久不散。
我們幾個面面相覷,搖頭嘆息,這一大票人竟然在這兩個月內都看走了眼。
原來那個不起眼的才是情婦...
而故事一直在走廊上演,那長廊是適合等待的。
半夜兩個女人,一個閃亮如同美麗的外衣,一個緘默卻蘊含溫柔的慈悲,但都伴隨著他起舞,或者該說是他同時佔領美麗與溫柔,而情人與老婆的角色,是如此鮮明對立又模糊地存在,令人錯愕不已。
她的進來,使人眼亮,臉上始終掛著笑意,很真心、很有信心,教病人覺得安心的那種。
她的男人是急診送來的,聽說是肝癌,事先沒有一點徵兆,不吸菸、不喝酒、不打夜牌、不嚼檳榔的標準先生,說倒就倒了。
她為他換上病房規定的病患衣服,調好點滴,他不斷喊泠,她以身子溫柔地擁住他,笑著告訴他:「一會兒就會好,打完點滴,高燒便會退。」她耐心地哄著小孩般不安的他,直到他似昏似睡的不再有騷動。
我看看腕錶,清晨四點,天已微明,她一夜沒睡,守著點滴,彷彿每落下一滴水,她才有一拍心跳,她的枕畔人已滿頭白髮,她該也有四十好幾了吧!她非常客氣地請我們去換已打完的點滴,許多謝意在臉上,份外讓人不忍。
天亮透的時分,病人的燒終於退了,她為他除去汗濕透的厚被,穿過拿取不易的點滴,換上一套乾淨的病服,抹身擦澡,微笑看著甦醒的他,對他低語,哄他安心,我覺得這肝癌病人的命其實挺好的。有這麼一位老婆,該是前世修來的福吧!
她總是在中午時分回家煮些粥、湯之類的補品,下午兩、三點才再過;而這位病人卻還有個漂亮的情婦,才真叫人又羨又妒。
那位美麗的情人卻精明得在她前腳走後,後腳就跨進來,高跟鞋格格的響徹長廊,打扮入時的套裝,一張仔細化過妝的臉,和一臉的撒嬌,她還要他哄著呢!
我聽到他輕輕對她說:「我一直在等妳來呢!」同房的病人都覺得他實在艷福不淺,賢慧的黃臉婆疼他如小孩,美麗的情人在空檔立刻來陪他,他始終都不寂寞。
他的病似乎沒有送來時那麼危急,手術切除術做的還不錯,他終於可以進食、散步,甚至不久也拔除了點滴管,可以在院外走動走動了,他的老婆日夜不停地照顧他,三餐弄吃的來,削水果、送椰子汁、拿書給他看、讀報給他聽,
她活得很有勁,也把這股勁兒傳輸給他,期待他的病情受控制之後,能提起生命的勁道來和病魔抗衡,好好地活下去。
我是挺佩服他的情婦,因為她可以聰慧的算到每次他老婆走了才會過來,匆匆坐一、兩個小時,又在他老婆回來之前離去,也佩服她永遠把自己收拾的光鮮亮麗,絕不在他面前露出邋遢相,不像他老婆總是踩腳褲、寬襯衫、平底鞋、綁個髮髻在腦後頭。
有時我們也愛八卦一下,怪不得18號病床的病人愛搞外遇,老婆和情婦實在沒得比,老婆每天弄吃弄喝,陪他散步、作運動,半夜還送消夜,算是賢慧了,他還是照樣在外頭有情婦,可見得漂亮得體,永遠是男士們臣服的,賢慧又算什麼呢?
週末下午,情婦又出現了,裁剪合身的粉紅色套裝,同色系髮帶與高跟鞋,令人耳目一新,我們輕輕點頭和她打招呼,卻赫然見到她帶著一個小男孩,十歲左右,長得清秀、調皮、聰明伶俐,他見到18號病床,老遠就撲過去,親親熱熱地喊「爸!」整個人埋在他爹身上又撒嬌,又思念地哭起來,他爸也老淚縱橫,那情景,真是令全病房為之動容。
我們暗地裡笑他是「累」出病來的,享盡齊人之福,在外頭連兒子都偷生了,的確不簡單,中國人的「有後」觀念很重,情婦有本事生個壯丁,人前人後喊爹的,讓他多得意啊!也怪不得兩個女人的待遇差那麼多,一個看起來淡然的像朋友,雖然無話不談卻沒有激情,一個看起來卻像蜂蜜,即使只是蜻蜓點水的來去,卻總令他期待。
孩子跟他爹去院裡玩了,美麗女人無聊地坐在床邊翻這翻那,翻到抽屜裡的一本筆記,她一頁一頁看,美麗的臉卻開始扭曲,她把筆記啪一聲扔進抽屜,幾乎是衝到護士間來,尖叫著詢問:「喂!告訴我,我不在的時候,有誰來看過18病床的病?」
「太多啦!每天都有人來看,鮮花、水果那麼多,您沒瞧見嗎?」
護理長很得體的擋開被質問的小護士,小心地回答她。
「我不是指來探病的,我是指平時的看護,您們是不是提供了特別看護?」
「沒有呀!只是太太、媽媽、姊妹之類的親人而已啊!」
「太太?搞清楚沒有?我才是他太太,您們沒看到他兒子都這麼大了嗎?」
「啊!」護士間的七、八個護士全都嚇住了。
這兩個月來,每個護士都照顧過18號病床,也親見那女人照顧他無微不至,弄屎弄尿、擦身換衣、煮三餐的辛苦。
如果說,眼前這才是真正的太太,那麼!那麼!那個平凡而且邋遢的女人難道才是他的情婦嗎?
這樣出色的男人會找這麼平凡的情婦嗎?
「您們回答我呀!」她的美麗和尖銳的聲音構成極不協調的畫面,我們沒有一個敢說話。
還是護理長最先回過神來、禮貌的告訴她:「18號病床是重病患,您是家屬,當然是知道的,平常醫院的伙食他嚥不下,需要其他家中進補的伙食,所以他母親和姊妹就輪著送來,倒沒別的人,太太,您放心吧!他有病在身,作不了怪啦!小心,生氣多了會有皺紋哦!」
「您們這幾個年輕護士最好少動他的歪腦筋,他是我一個人的,不准妳們挑逗他!」
說完頭也不回的回病床了,長廊響起的高跟鞋聲久久不散。
我們幾個面面相覷,搖頭嘆息,這一大票人竟然在這兩個月內都看走了眼。
原來那個不起眼的才是情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