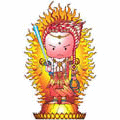第十四章 上師的圓寂
在最後的那些時光中,我有個隱約的焦慮感,那就是我跟桑天•嘉措相處的日子來日無多了。所以,每當機會來臨時,我都不放過,趕緊向他請益以澄清許多疑點。
在這段期間,我也變得大膽到敢問他人生最深處的目標。這是他所說的話:“年少時,除了待在山上一個又一個洞穴之外,我什麼都不渴求,我從不希冀崇高喇嘛的頭銜與地位。實際上,我想要過著隱姓埋名的的生活,而且盡最大努力這樣去做。”
他補充告訴我另一個目標:“我打從心底渴望搜集完整一套秋吉•林巴的伏藏法。”(1)他成功地達成了這個願望,不只收集了典籍,還連同圖像、壇城,以及其他每件必要的配備,而且每樣東西的品質都無可挑剔。
雖然做得極為成功,而且非常知名,但桑天•嘉措總是將身為其他人的金剛上師或根本上師視為一種個人障礙。因為,事實上他的主要目標一直都是終生獨自待在岩穴裡修持,所以,他哀歎地對我說:“我感覺自己整個人生已經走錯方向了,因為我受到障礙的左右。”
往昔的傳統是,一個人必須服從上師的指示,上師會說:“去某某地方,高舉了悟的勝利旗幟。當你獲致了成就,就可以真正利益眾生了。”
弟子會到那個地點專心一致地修持,直至達到了悟為止。在那之後,他或她會走出來冒險犯難,進入紅塵利益眾生。那是理所當然的過程。沒有接獲上師的允許或指示,一個人是不會以金剛上師的身份為他人福祉而打拼。然而,接獲指示或允許之後,一個人就必定要擔負起任務。
當桑天•嘉措年紀漸長後,他心裡時常想著:“我本該要待在洞穴裡的,但相反地,我卻陷於障難的威勢之下。”
功成名就是修道的障礙
這不是嘴巴說說而已,他確實那麼認為;他並沒有企圖要成為一位金剛上師,或高坐於任何其他人之上。他有一次說明道:“功成名就事實上是令人愉快的障礙。相對於任何令人不愉快的障礙能夠輕易地被認出,成功卻鮮少被認為是修道上的一種障礙。令人不愉快的障礙,舉例來說,包括了遭人誹謗、涉入醜聞、身陷病苦,不然就是遭致失敗或不幸。有能力的行者可以處理這些問題,他們認出這些情況是障礙,並運用它們作為修道的一部分。”
“然而對於令人愉快的障礙,例如變得知名、身邊有弟子聚集、致力於他人福祉,一個人心裡就會開始想著:‘喲,這下好了!我真的變得與眾不同了。我利益許多人,事事順心!我是如此的成功!’卻沒有認出,對成功的迷戀是進步的主要障難。”
當這樣的情況發生時,桑天•嘉措警示道,人們心裡只會想:“我利益他人的能力正在擴展!”這是他們跟自己說的話,卻始終沒有發現自己已成為障礙的俘虜。
桑天•嘉措有一次以他慣常輕描淡寫的口氣提到,他期待他的家族能為《新伏藏》的延續至少貢獻一點心力。我表弟堪楚是噶美堪布的轉世,他的心智極為敏銳,也精通佛教典籍。我認為他理所當然會是主要傳承的持有人。
然而,那卻不在桑天•嘉措的規劃裡。堪楚跟我時常住在同一座寺院裡,不過我卻跟桑天•比較親近。我時常納悶為何我們上師從未將堪楚視為傳承持有人。“假若不是他的話,那麼誰有可能會護持傳承呢?為何桑天•嘉措不給他更多特殊待遇呢?”
這個年輕人除了非常有膽識外,也相當博學多聞,展現出威嚴的儀態。然而,有一次他到中藏領受更多教法與灌頂時,我們卻接到了他在那裡過世的消息。
當堪楚過世時,我們全都悲傷欲絕,而那發生在他能夠傳續傳承之前。要不是因為這樣的話,我毫不懷疑他將會是個稱職的上師。然而回顧過往,我想桑天•嘉措極可能早已經瞭解堪楚的生命力不會持久,將會英年早逝。
堪楚過世後,桑天•嘉措說道:“你是我寄望延續傳承的第二人選。”他以這種態度說話是極不尋常的;他絕不會奉承討好任何人,更別說是他自己的家人了,他甚至不會當著噶瑪巴的面來誇讚他。
另一方面,他也從未批評過任何人。倘若任何人有過錯的話,他也只會視而不見,不發一語。我只聽過他讚揚欽哲、康楚、秋林,再也沒有其他人了;他莊重、寡言,是不會做出無意義言行的那種人。除非你對他知之甚詳,否則你絕對無從得知他真正的看法。
然而,當我誠實地面對自己時,我心想:“我毫無特殊之處,我教養不佳。我唯一的優點是跟桑天•嘉措住在一起。”當時,我只想待在他身邊,除此之外並無特別的企圖心。
他告訴我好幾次:“《新伏藏》的傳承是否有一天會中斷,就掌握在你的手中。因此我希望自己對你的稍微嚴格,能夠有所代價。”
當阿杜仁波切幾年前從囊謙來的時候,他說在家鄉那裡,他們都視我為《新伏藏》的主要持有人。這並非因為我一直特別勤奮,完全是由於桑天•嘉措的緣故。
因為我們共同肩負同一座寺院的責任,而且我一直都跟桑天•嘉措待在一起,因此當他給予灌頂時,根本不可能找到理由不參加。
“我盼望以後你會護持這個傳承。”他會這麼說。因此,我領受了他所給予的每個灌頂與教法。這並非每次都出於我自己的選擇,我只是不敢缺席罷了,因為他可是個令人非常畏懼的人。
委交《新伏藏》護法
生命將盡之際,桑天•嘉措給了我一次特殊的託付儀式,將我委託給《新伏藏》的護法(2),這是他從未授予任何的人的一種傳承。秋吉•林巴也只將這個特定的修持傳給偉大的康楚而已,而康楚又只傳給了噶美堪布,桑天•嘉措就是從他那兒領受到的。桑天•嘉措現在是唯一知道細節並定期在壘峰修持的人。它特殊的功能之一,就是保護穀物免於霜凍之害。
然而不幸地,缺乏毅力似乎是我的人格特質之一。倘若某個傳承必須每日保持任何方式的嚴格專注,那就違反了我的本性,這是我為何沒有進一步將那項修持,運用在相關特殊場合的理由所在(3)。所以,現今我擁有口傳與灌頂可以將它傳承下去,不過卻沒有實際運用時所必要的專門知識,顯然其他人也沒有。
在甘托克的時候,宗薩•欽哲問我是否有帶來由該項修持加持而做出的物品,於是我將我所有的相關東西都給了他。現在我沒有任何東西留下來,所以儘管宗薩•欽哲證實它具有極大效用,但也沒有人能將它做出來了。
我的父親與伯叔們相繼過世前,他們的臉龐似乎有了驚人的改變,他們仿佛變年輕了。他們灰白的頭髮並未轉成黑色,但他們的肌膚確實變得更年輕、更有光澤。有些人說這種青春的肌膚狀況與光澤是一種了悟的徵兆。事實上,密續典籍談及達到某種程度的經驗與了悟後,肌膚會變得柔軟而有彈性。
我首先注意到桑天•嘉措有了轉變。他離開身軀的那一年,肌膚顯而易見變得充滿了生氣;臉部的五官似乎就像位年輕男子一樣,因此你完全忘一記他其實已經相當年老了;他的肌膚轉為淺淡、柔亮的顏色,宛如內在正發生著某些不尋常的變化。
在那之前,他看起來衰老而疲倦,然而倏忽間他呈現出青春的相貌。人們會問道:“您到底幾歲了,桑天•嘉措?您看起來如此年輕!怎麼一回事?他們給您吃神奇的東西,還是您正在修特別的法?”
這種相貌上的轉變,大約在他圓寂前一年開始。不過老實說,如果你仔細思量一下,那其實並非是個好兆頭——在內心深處的某個角落,你感覺到那是不可能持久的。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我父親身上;他的肌膚散發出古銅色調的亮光,你可以將它稱為“莊嚴光彩”,仿佛肌膚裡面有著燃燒未盡的餘火般,面容也呈現出很有朝氣的青春樣貌。他在三個月後過世了。
當桑拿叔叔過世時,我在楚布寺,不過我聽說他也發生了相同的情形。所有當地人都注意到他的皺紋消失不見了,也好奇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當地流傳著:“桑拿仁波切發生了什麼事,一讓他看起來如此年輕?我們都看不到他的皺紋了。我們曾經在他兩位兄長身上見到這種情形,這有可能是他也許將於今年圓寂的徵兆嗎?”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稍後他在那年去世了。
德喜叔叔有一次對我說道:“當親近的家人像我兄長那樣,看起來比他們實際年齡朝氣蓬勃、容光煥發時,一般人應該會感到開心才對。然而我卻沒有。我覺得那是個惡兆,表示死期將至。”至於德喜叔叔自己,他過世前不久,同樣的儘管是滿頭灰發,臉龐卻像個年輕男子一樣。
那就是一個人如何預先知道這幾位兄弟即將不久人世。我並未捏造這些事情,而這也不僅止於一、兩個人的印象而已,每個見到他們的人都這麼說。
生命將盡的閉關
生命將盡之際,桑天•嘉措進行閉關,且打算餘生都待在那裡。但是,他並未直接宣佈這件事,只是跟大家說,他要留在距拉恰寺一天行程的壘峰,進行為期兩星期的鬆散閉關,而在那段期間,他會為國家的人民修保護儀式。之後,當他一安頓好就傳送資訊說,這是他進行長期嚴格閉關的時機。
然而只過了一小段時間,囊謙王子就病倒了,兩位重要大臣被派來召喚桑天•嘉措。
“我們王子病況嚴重,也許不久就會過世了。”他們宣稱:“您必須跟我們一同回到皇宮。陛下已經指示我們,沒有您同行就不要回去了,所以我們不會走!”
由於這兩位高官在客房裡等待,我們這些跟桑天•嘉措親近的人爭辯著該如何處理。除了他妹妹,也就是擔任寺院與閉關中心管家的紮西•吉美之外,桑拿叔叔當時也在附近。
當時我雖然只是個年輕人,卻不畏懼皇室家族。我力爭說:不管任何人請求,也無論他們是多麼重要的人物,桑天•嘉措都不該離開閉關處。
另一個人提出相反論調:“早年,上師待在皇宮三年期間,時常主持法會幫助國王。到目前為止,每件事都吉祥如意。國王捐贈了一大片包含許多肥沃田地的土地給寺院,他一直是個慷慨大方的功德主,所以實在沒有選擇餘地——桑天•嘉措必須中斷閉關到皇宮去。”
“我們上師應該不會理會這項資訊,會拒絕跟他們走。”我由衷地堅持,儘管或許有點兒天真。
又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國王已經下達命令了,臣民不是通常都要服從君命嗎?”
“即使這樣的命令難以回絕,”我繼續說道:“如果你這次同意了,你將永遠都必須順從。因為我們上師受到如此崇高的珍視,我憂心每個人都有可能會要求他做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請求將沒完沒了!”
一股強烈的不祥預感沉重地壓在我心頭。我有一個比較不受讚賞的特質,那就是無法將這種感覺放在心裡。因此,我一心一意試圖勸阻房間裡的每個人。
討論過程中,有一度大家其實決議不要去。我們告知了兩位正在等候的大臣這個決定。
然而,他們其中一人回復道:“如果結論是這樣的話,我們不會返回皇宮,未來的日子我們都會待在這裡!我將睡在桑天•嘉措的門前!”
他以冷靜頑強的典型康巴人強硬態度這麼說完。又補充說道:“即使我必須在壘峰等桑天•嘉措九年,我也不會在沒有他同行之下回去!”
這時,另一位舉足輕重的喇嘛:“倘若桑天•嘉措拒絕,而年輕王子過世了,會發生什麼事呢?說真的,除了去之外,他沒有選擇的餘地。”
到最後,大家的共識是桑天•嘉措必須要去。我做了最後一次的努力,提高聲量說道:“假使他現在中斷閉關到皇宮去,將會沒完沒了,他將永遠無法再回去閉關了。倘若你這次順從了國王的心願,你未來就無法違抗,將永遠都必須照著辦。因此,還是請求免除任務,保持堅定的態度。”
然而,似乎我是團體中唯一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且因為我仍被視為是年輕人,能有多少權力說服任何人呢?其他人有最後的決定權,因此到後來,桑天•嘉措還是決定去了。我被要求跟著一塊兒去,但我拒絕:“我絕對不會去,尤其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去。說實在話,事情這樣轉變讓我深感不快。請見諒,我要回拉恰寺。”
就在臨行前,桑天•嘉措的小刀怎麼都找不到。他從來不曾跟這把刀子分開過;刀鞘還在,但刀子不見了,他必須在沒有這把刀子的情況下離開。
一抵達皇宮後,桑天•嘉措就開始修持一場精細複雜,為期九天的長壽法會(4)。當法會結束時,年輕的阿千王子就已經病癒了,絲毫不見疾病,也不見任何邪惡力的蹤影。那場儀式的威力是如此強大。
接著,就是我所擔憂的,又有了另一項請求。由於囊謙皇后來自于德格的皇室家族,桑天•嘉措也受邀到德格的宮廷主持法會。那裡有盛大的遊行隊伍列隊歡迎他,他們以皇室王宮招待人的深切敬意來接待他。幾個星期之後,他終於完成了他的任務並啟程返家。
一切事情似乎都進行得很順利,直到他抵達壘峰腳下,他從馬背上摔下來,腿受了傷。他的侍者幫忙將他扶上馬,騎了最後一段路往上到隱修處。我不確定是出了什麼差錯,不過在那之後,他就無法走路了。
不吉的夢兆
桑天•嘉措抵達後的那天早上,他派人到拉恰寺找我過去。信使花了一整天時間才抵達寺院,當那位僧侶走進來時,已經接近黃昏了,“桑嘉仁波切(Samgya Rinpoche)已經病倒了。”他指的人就是我上師,“病情顯得相當嚴重,他在找你。”
一聽到這件事,我內心充塞著排山倒海的哀傷;桑天•嘉措即將離我們而去的直覺緊緊抓住了我,讓我難以自抑。他在閉關中途離開,絕對是不吉祥的;而遺失刀子,也絕不會是個好兆頭。自從他離開以後,我沒有片刻感到歡欣。事實上,就在那天早上,我做了一個極為不吉利的夢,夢見桑天•嘉措就要離開壘峰了。我在那裡當他的侍者,抬頭望向西邊的山麓,我看見太陽低垂在天邊。
“嘿,仁波切!”我敦促道:“現在別走!太陽快要下山了!別在黑暗中遠行,拜託您回頭,回到屋裡來。”
我伸出手要引領他回到屋裡,他卻回答說:“不行,不行!我的時間已經到了,我沒有選擇餘地,必須離開。”在夢中我哀求道:“請不要那麼說!”
他卻答道:“業的力量是無法阻擋的,不是嗎?”他從我的手掌滑開,騎馬離開了。片刻之後,太陽下山,而他也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
下一刻我醒了過來,心裡想道:“真是糟糕透了的夢!”那天早上,我告訴我的廚師:“我做了一個跟桑天•嘉措有關,卻令人不安的夢。那個夢讓我想到他已經回到了壘峰。”“不要說那樣的事!”老廚師抗議道。
所以,當那天稍後信使抵達,召喚我回壘峰時,我並不意外,我心裡唯一的想法是,我們上師即將不久于人世,一種讓我心如刀割般的痛苦想法。那夜我輾轉難眠,離破曉還很久時,我就已經起床,為當天騎馬回壘峰做準備。
在山徑上賓士超過十二個小時之後,還沒喘過氣來,我就直接走進桑天•嘉措的房間,探問他的身體情況。顯而易見,他病懨懨地,承受著持續不斷的強烈疼痛。他只能說幾句話而已。
兩位醫師被請來做診治,不過坦白說,他們完全不管用。其中一名醫師將這個可怕病情診斷為“三十重黑暗”,也發現桑天•嘉措的腸子有破裂的跡象。
“他需要施以火療法。”另一個醫生說:“不過那老早以前就該做了。現在已經太晚了,我沒有把握我能辦得到。”醫生提到的是一種傳統的醫療方式“昧雜”(metsa),只用在嚴重的病症上(5)。我準備了火療法的用具,接著用熱得發紅的鐵輕輕碰觸了他的皮膚。這麼做稍微減輕了他的疼痛,讓他能說幾句話。然而,當疾病正在吞噬他的腸道時,暫時減輕痛苦又有什麼用呢?
“仁波切,看起來並未好轉!”我說道:“將會發生什麼事呢?”
“誰曉得呢?”他回答:“秋吉•林巴與他大部分的後代子孫都不長壽;他的兒子旺秋•多傑英年早逝,他的女兒,也就是我們珍貴的母親比較好,活到七十好幾。他另一個兒子哲旺•諾布,六十多歲時過世。我們另一邊家族,倉薩傳承似乎也都不長命。幾乎這個傳承的每個人,包括我自己的父親,都在五十多歲時就往生。而我現在已經六十五歲了。”
他繼續說道:“從另一方面來說,我現在死了也沒關係,實在沒什麼差別。如果我能活得久一點當然很好,不過如果我死了也沒什麼關係,我已經活得夠久了。”
“仁波切,”我接著問道:“我能做什麼幫助您康復嗎?”“別再談這件事了。”他答道。
這讓我哀傷欲絕。那天稍晚的時候,我對他康復所抱的希望已化為泡影。他明顯地就快要離開他的身驅了。
輪回與涅槃皆由心所現
我上師曾一度說道:“心的幻現是言語無法企及的,嘗試將它們表達出來並沒有意義,因為描述將無止無盡。我現在明瞭了,沒有東西是沒見過的,沒有東西是沒有聽過的;輪回與涅槃(nirvana)的所有現象都由此心所幻現,你不同意嗎?”
“我同意,仁波切。”我答道。
這個情況似乎需要我隨順他,雖然這麼深奧的知見肯定不是我當前經驗的一部分。我從來不曾對桑天•嘉措極高層次的證量與神通起過任何疑惑,然而當他到達此生終點的時候,這些甚至變得更為顯而易見。他說的話似乎出自一種無所障礙的心的狀態。
沉默一段時間之後,他又繼續說道:“啊!蔣揚•欽哲•旺波來了!現在偉大的伏藏師秋吉•林巴到了!還有蔣貢•康楚也來了!”
所有大師中,他對康楚懷有最強大的信心,有一種不可思議的信念;他對康楚的著作大為讚歎,時常以這些措辭描述道:“譯師毗盧遮那的轉世、大日如來佛的人身化現,以熠熠生輝的海螺殼——釋迦牟尼佛簡潔明確而無所畏懼的聲音,以無限智慧(Infinite Wisdom)的名義展現出來。”(6)這裡指的是佛陀曾經預言過的康楚。
這時候,桑天•嘉措說他也抵達了。聽到這樣的話讓我內心更加悲傷,因為我覺得已經沒有剩下多少時間了。他的侍者杜竹和我那晚都沒有睡覺,熬夜照顧他。我們試圖要給他一些東西吃,然而他只能喝一點水,而且虛弱到無法說出一、兩個字。杜竹喜歡睡覺,不久我就發現剩下我一人獨自陪伴我臥病的上師。整個夜晚,桑天•嘉措唯一吐出的話語就是要求喝杯水。
我們都開始覺得生命的終點接近了,我問他,但他既不證實也不否認即將離去,他只是說:“我說不準,我們就靜觀其變,明天早上將會分曉。不管哪一種情況,都不需要擔憂。”
第二天早上,他開始發燒得更厲害了。
大約就在這時候,我哥哥遍吉捲入了一場土地紛爭。我哥哥具有一種果決的自信,甚至可以說是挑釁的性格。後來我們發現就在那一天——第四個月的第十九天——一群敵手逮住了他。就在那一刻,桑天•嘉措從病床上驚叫道:“噢,天哪!”
“怎麼了,仁波切。”我問道。
他又再次說了:“噢,天啊!”並補上一句:“遍吉遇到大麻煩了!”
“他發生了什麼事,仁波切?”我問道。
桑天•嘉措回答道:“噢,天啊!現在遍吉大難臨頭了!他快要被人刺殺了!”
偶爾,我們地區的康巴人會有幫派打鬥的事件發生,有時候也會有一兩個人被殺死而進入中陰狀態,而事實上,幾個月前,遍吉的侍者就不幸在打鬥中喪命。
桑天•嘉措這時候提到了他,繼續說道:“遍吉已故的侍者告訴我,他有一匹馬;他死了之後,私人財物以他的名義分送出去,以增進他的功德,然而他家人不知何故忘記將那匹馬也算進去。現在他請求我告訴他家人,賣掉那匹馬,所得的錢做供養。他人在中陰,需要幫助。”
過一會兒之後,桑天•嘉措又接著說:“喲,喲!一個人能說的話是說不完的,所以叨叨絮絮講個不停有什麼用。”然後,他揚起了微笑,看著我輕聲笑了起來。
遙呼上師,祈請鑒知
那整個晚上我都待在他房裡。一大清一早的時候,我探問他感覺如何。他非但沒有直接回答我,還親昵地跟我說話,問道:“噶嘎(Kargah),已經破曉了嗎?”(7)
“是的,就要破曉了。”
“那好,請納迪喇嘛(Ngakdi Lama)進來。”桑天•嘉措低聲說道,叫的是桑拿叔叔的小名。我告訴杜竹把桑拿叔叔請過來。
桑拿叔叔到了,並頂禮了三次。
桑天•嘉措請他坐在一個小法座上,接著說道:“喲,喲!既然喇嘛在這兒,我們何不一起念誦蔣貢•康楚的《遙呼上師祈請文》(calling the Guru from Afar)呢?”
這是一部極為知名的經文,目的是為了打開一個人的虔誠心,能讓我們的心與上師的心更易融合在一起。我們開始一起唱誦,桑拿叔叔帶頭唱起詩文:
“上師,鑒知我。
仁慈之根本上師,鑒知我。
三世一切佛之髓,
教證諸聖法之源,
聖眾總集僧之首,
根本上師,鑒知我。”
當我們唱誦時,桑天•嘉措以令人吃驚的強勁聲音跟著我們一起唱誦。這時候,他把身體坐起來,兩腿散盤,以稱為“安住於心性”的禪修姿勢將手掌心放在膝蓋上;他披著一塊布,從頭蓋住雙耳,以保護他的頭部不受寒氣侵襲,而他的肌膚散發出引人注目的光彩。
我們並沒有將那首祈請文唱完,因為在某個時候,桑天•嘉措打斷了我們,重複唱著經文中的這一句:
“護佑加持我真正地覺知死亡。”
我們全部人都停止念誦,幾經片刻之後,他又唱了這句詩文一次:
“護佑加持我真正地覺知死亡。”
當太陽開始升起時,他又唱了第三次,接著他的身體稍微往下彎一點。你能見到死亡那一刻身軀所發生的鬆馳。當我看著我上師時,我相信他已經圓寂了,儘管當時他的臉龐還掛著美好的微笑,眼睛仍然清澈並睜得大大的,看起來非常像活著的樣子;他的肌膚散發著亮光,幾乎是閃閃發光。他仍舊以知名的龍欽巴大師畫像中可見的同樣禪修姿勢坐著,看起來十分有信心且平靜,然而卻沒有脈搏或呼吸跡象。
根據大圓滿傳統,在死亡過程的特定時刻,在行者耳邊重複念誦廿一次“啊”種子字,可以提醒行者持續修持心的究竟本性。我這時候靠近上師跪了下來,開始重複念誦“啊,啊,啊,啊,啊… … ”
不過,我沒氣了,因此覺得必須從頭再來一次。當我正要吸第二口氣的時候,他相當明顯地點了點頭,仿佛表示說他已經得到要領了。
我仍然念誦第二次一串的“啊”,而他再次點頭了,不過只有輕微地點一下。
因為我不肯定這樣子念夠不夠,所以我又繼續重複第三遍。當我念完時,他的身體甚至挺得更加筆直了;他坐在那裡,眼睛明亮有神、睜得偌大,臉上掛著清楚的笑容。看起來確實宛如根本未曾死去。(8)
只有杜竹、桑拿叔叔,還有我在場而已。如果德喜叔叔也在場的話,毫無疑問地,他會魯莽地要求知道關於桑天•嘉措的轉世可能會在何處被找到的精確消息,他有辦法詢問這麼高度私人的問題,我卻沒有膽量問,因為我還記得桑天•嘉措早先曾經跟噶瑪巴說過,關於他不想過世之後有祖古被找到的事。然而不管怎麼說,我哀傷得難以自抑。
我們上師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而我們對此卻完全束手無策。
進入法界
過了一會兒之後,我們將他的遺體裹在錦緞裡。那天下午稍後,他的遺體被抬下來,放置在大佛堂的一個法座上。偉大上師的遺體通常會被放入一隻巨大的銅盤裡,以防止體液滲出,並覆上一袋袋的鹽來吸收水氣,接著再用袍子將這些全都包裹起來。
在上師前方的桌上,我們放置了他的金剛杵和金剛鈴,再加上其他法器。當人們見到他的面容時,完全無法相信他已經圓寂了;他看起來仍像活著的樣子,臉上帶著平靜祥和的笑容、眼睛明亮清澄,而且就這樣維持了三天。後來,遺體開始有點捲曲了,所以我們就蓋住了他的臉。
有一位信使前去通知住在類烏齊寺的德喜叔叔,另一位則去我父親那兒。我父親在第三天抵達,而類烏齊寺則因為無論從哪條路徑過來,都需要五天路程,所以德喜叔叔一直到次周才抵達。等大家都到齊後,我們開始在法體,即其神聖的遺體前修竹千法會。
當時有一位從拉恰寺過來的喇嘛情緒激動地說:“像桑天•嘉措那樣的人怎麼能死呢?我無法相信,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我從來沒想過他會死。如果這件事是真的,那麼這世界上肯定沒有東西是可靠的了。”
我問他:“你為什麼那麼想?”
“因為他在各方面都非常可靠。”他答道:“因為他的堅定不移與精確感,以及他不變的誠實正直,絲毫沒有欺瞞。像那樣的人怎麼會死呢?”
荼毗大典後,我們在骨灰中發現了令人驚異的東西:顱骨仍維持完好無損(9)。而儘管其他衣物全部都燒得精光了,其中一件卻未燒毀,且不知為何,這件衣服上有著彩虹的五種顏色;骨灰裡則出現包含了東(dung)與舍利等無數聖骸。
茶毗大典中,每個在場的人都目睹了天空中出現令人難以置信的彩虹圖案。真的不可思議!因為深藍的天空清朗到完全不見一絲雲蹤。也許你知道,這被視為是最棒的徵兆。
這些就是伴隨我的上師圓寂進入法界未顯空的徵兆,這些也是以我的凡夫肉眼所能見證的。除此之外,對於他一般的生平故事,我能說的就沒多少了。
桑天•嘉措的三位弟弟齊聚參加了他的荼毗大典。在康區的習俗裡,人往生後會修兩個法事:一是“施身法”,另一則是“杜爾”(dur);“杜爾”和相應於每個人肉身存在的某些靈體有關,在法事的主要部分中,主法上師會讓九種毀滅性靈體脫離往生者的生命能量。我們的瞭解是,人死亡時,除非能與這九種靈體分開,否則就會減緩,甚至障礙到中陰時的解脫。
我父親理所當然地主修施身法。雖然迷信觀念認為“杜爾”不應該由兒子、父親或其他親近男性親戚主修,但我仍自願修此儀式,而且不曾發生任何不幸的事。
我常聽說尼泊爾家庭抱怨他們往生親人的鬼魂返回家中,還陰魂不散地待在房子裡,有時候甚至聽說丈夫往生、火化之後,還試圖回到床上跟妻子在一起;妻子並未見到任何東西,不過卻有可能聽到了他說話的聲音或打鼾的聲音。然而在康區,我從未聽說發生過這種事,或許因為有人往生後,我們總是馬上藉由施身法與“杜爾”來撫慰這九種靈體。
“杜爾”儀式有“平息”與“降伏”兩部分,有時候還包括超度儀式;這是一種召喚亡者意識,淨化它,並將它送到佛國的安撫性活動。“降伏”的部分是要驅除已控制亡者的邪惡力,這些吞食性的靈體是魔鬼,也是眾生的一種。當儀式進行到將九種靈體從各個躲藏的角落驅逐出去時,你會聽到許多次“吽”與“帕”的咒音。
這種法會甚至對桑天•嘉措這樣偉大的上師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樣一位上師的恢弘氣度會吸引許多的世間靈體。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大多數偉大的金剛持有者身上,因為這九種靈體與正在化入無相境界,即所有一切俱生之本空的大師具有某種關連。
因為吉美•多傑是一位具有如此威力的大師,也是一位老練的施身法行者,他或許成功地讓這九種靈體“脫離”了。
當所有法事都圓滿之後,我到中藏旅行了一趟,依慣例為桑天•嘉措的往生作供養。在拉薩時,我碰巧遇見了一位來自德格的桑天•嘉措弟子,是位非常虔誠又固執的喇嘛。儘管這位喇嘛已聽說桑天•嘉措明確表示不要請示噶瑪巴找出轉世祖古的心願,但他無論如何還是跟著我們寺院的總管,一起出發前往中藏請示噶瑪巴。
我們彼此交談了幾句話:“難道你上師沒有告訴你,不要去找尋他的轉世祖古嗎?”我問他:“然而你卻違背了他的意願,一路遠行去拜見噶瑪巴。”
不過,那樣說也沒什麼用,因為康巴人相當頑固,就如俗諺所說:“康巴人就跟犛牛一樣固執——不管是盜匪,還是大禪修者都一樣。”
儘管我一再反對,這名弟子還是逕行前往請示噶瑪巴,那就是為何今日有人被稱為“桑天•嘉措的祖古”的原因。
1、在這段期間之前,秋吉•林巴取出的伏藏法並沒有一套完整的集要。偉大伏藏師在諸多場合中立即將包含雕像、聖物,或來自天界空行母解碼的文字等寶藏,交給一位預言中的領受者,這人就成了那部特定伏藏法的主要傳承持有人。桑天•嘉措年少的時期,囊謙既沒有交通運輸,也沒有現代化通訊工具,但桑天•嘉措開始著手“搜尋伏藏寶”——就以“尋寶”(treasure hunt)最有意義的方面來說。如今集要包含了超過四十部巨作。
2、託付給伏藏教法護法的儀式,包含了確立上師做為“壇城之主”的地位,而後特定護法將隨時供他差遣。這些教法的護法接著應當執行上師神聖的願望與佛行事業。
3、儀軌修持到特定數量或持咒到特定次數之後,行者可以運用在某些特定用途上,例如準備聖物來從事各種不同的佛行事業以保護或服務生者與亡者。
4、以偉大上師欽哲的心意伏藏《長壽佛母牆達利》(Chandali,the Mother of Longevity)為根基。(祖古•烏金仁波切說明)
5、這種以醫療用鐵或黃金尖端快速碰觸身體感染部位的治療方式,比針灸還要激烈得多,有時候馬上就形成了水泡。
6、“熠熠生輝的海螺殼”指的是如釋迦牟尼佛般至高無上化身的喉輪。這種語的力量來自無量無邊的功德,勝過其他卅二相、八十隨行好的總集,而且據說會發出讓人們能以自己語言理解的聲音。
7、拿一個人名字開頭的第一個音節,後面再加上“嘎”,表示“親愛的”意思,這是康巴人通常用來簡稱名字的方式。祖古•烏金仁波切的名字是噶瑪•烏金(Karma Urgyen)。
8、當偉大修行人往生的時候,能完全掌控自己心靈的狀態;他們絕對不像普通人那樣有任何焦慮,因為對他們而言,轉換身體就跟換衣服一樣。有些行者甚至能決定以什麼方式、在何種情況下往生。桑天•嘉措選在與最後那些深刻強烈的詩句相應時往生。在呼出了他的最後一口氣之後,安住於三摩地當中;這是一處非凡的禪定狀態,也是一種常見於高僧與高明佛教行者的現象。這種狀態稱為圖當(tukdam),特徵是心臟周圍仍有些微溫,而肌膚並未失去光澤或褪色,身體也沒有轉為僵硬,仍維持著挺直的坐姿。這種狀態可以持續幾個小時到一星期或更長時間。
9、在祖古•烏金仁波切的荼毗大典後,打開火葬舍利塔時,也發現他的顱骨全然完好如初。顱骨目前被保存在確吉•尼瑪仁波切於尼泊爾的卡甯謝珠林寺(Ka-Nying Shedrudb Ling monastery)私人佛堂裡;其表面可以見到一個自然浮現的“阿”種子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