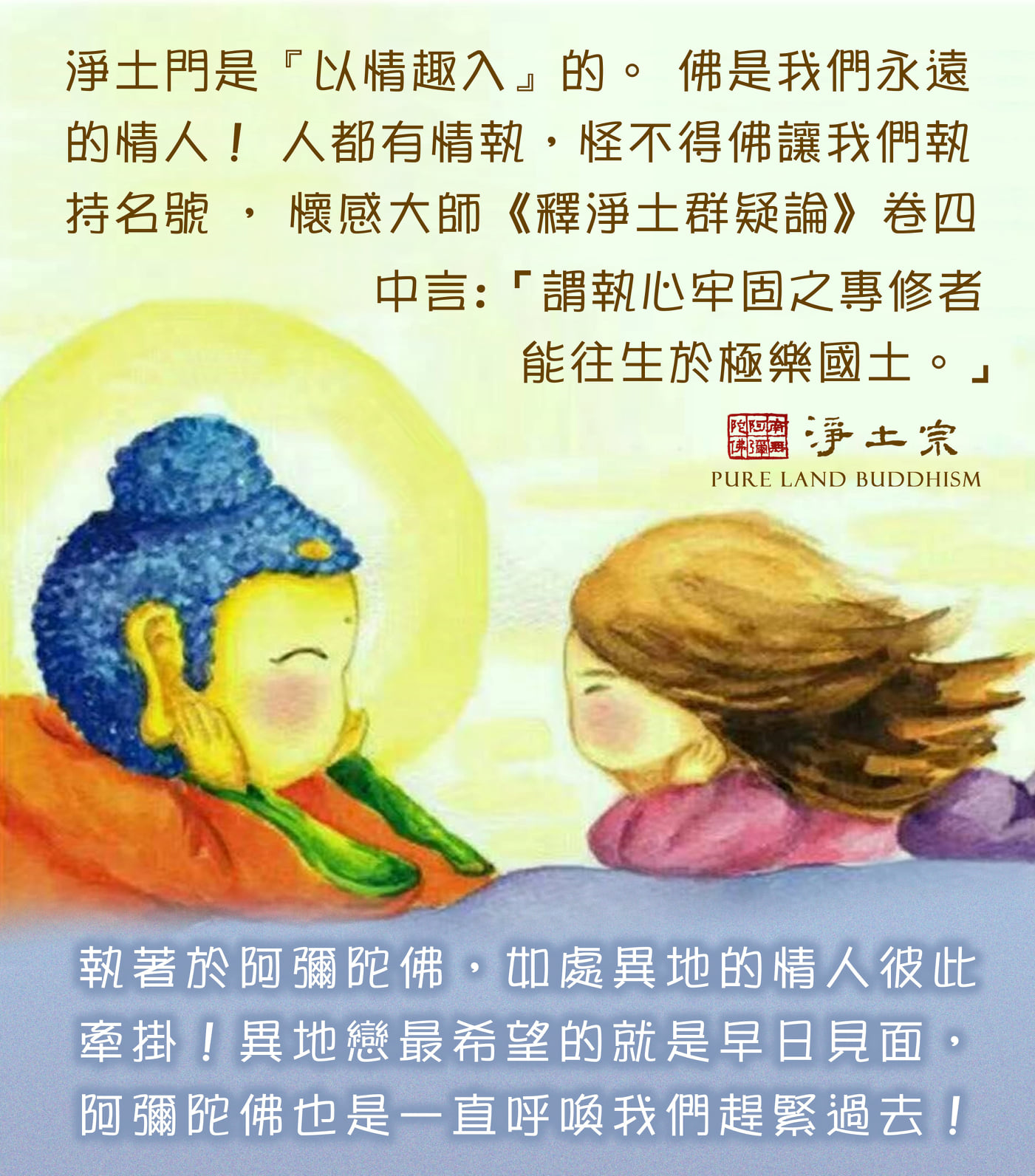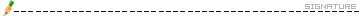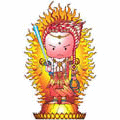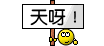2012.09.09 04:36 am |
年輕的母親隨一群眷屬,輾轉流徙,先到台灣,半年後才遇見被共軍俘擄、憑一紙路條中途逃亡海南島、渡過海峽歸來的父親。命運曲折,生死折磨,會使一個人的心房像蜂巢層岩,一格一格儲存的不是蜜,是苦楚的沉積物……
 |
圖/達姆 |
在燈下,我翻閱《滇西抗日血戰紀實》,想起抗戰後期,父親在五十四軍強渡怒江、仰攻高黎貢山的經歷,清楚地又在各段硝煙文字看到他當連長的身影。
蘆溝橋事變,父親被拉夫而出川。在上海的交通壕溝裡,他搬枕木、抬鐵條,赤足棉花田被長鐵釘貫穿過腳板。守衛南翔橋一役,以汽油、稻草設防,火焰沖天中憑一挺輕機槍擊退一排敵兵,當上中士班長。
在這之前,他是效法桃園三結義仁字旗下的「袍哥」;是陳家山一家木廠、一大片梯田的三少爺;是長江上游忠州水岸販售川芎、蟲草、貝母的商旅。民國初年的四川,軍閥交爭地盤,土匪收糧收餉,父親白天上私塾,夜晚逃土匪。及長,進過「邊防一路軍事學校」受訓,也參加過四川軍。原有機會保送中央軍校,卻隨一陝西人學鑄幣,荒遊各地。等積攢了錢想回家,不料夜半發生如〈石壕吏〉「有吏夜捉人」的情景,領了一套粗布軍服、一個新編的隊號,直拉到上海,從二兵幹起。
我在燈下想著父親辭世前幾年,由於握筆的手顫抖,不再寫字、寫信;長日坐在背窗的一張躺椅,一搖一晃地假寐。屋子沒開燈,有些暗,他的臉背光,更顯模糊,總要靠近才知道他是睜著眼或閉著。額頭滿載歲月的疲憊,薄唇緊抿而微凹,渾不覺客廳人聲的喧譁。假日,我想帶他外出走走,多半時候他回答:「帶你媽媽出去散散心吧。我留著看家!」「隨他!──」母親往往賭氣道:「一輩子就只喜歡和外人在一起。」外人,指的是父親的舊日同袍。
我知道,母親並不了解父親。一個生於四川,一個長於山東,因戰爭逃難而結婚,婚後不數日,軍人父親即開拔上火線,年輕的母親隨一群眷屬,輾轉流徙,先到台灣,半年後才遇見被共軍俘擄、憑一紙路條中途逃亡海南島、渡過海峽歸來的父親。命運曲折,生死折磨,會使一個人的心房像蜂巢層岩,一格一格儲存的不是蜜,是苦楚的沉積物。問題是誰能脫開現實的綑束,帶老去的他回到青年人生還沒有碎裂、憾恨還來得及收拾的時代。
1987年,政府宣布開放探親,我計畫陪父親回四川。有一天,他在同樣未開燈而昏暗的屋裡,講了一段一輩子令他愴痛的恨別。
「1938年,最艱苦的作戰期,日軍攻下九江、馬當,國軍在江西與湖北交界築防禦工事,日軍隨即又從武漢背後來襲。你祖母病危,家中連催九封信。我全未收到,隻字不悉,直到戰事告一段落,無意中聽一文書提及……」
父親用四川話,講武漢失守之際鄂北那場戰役。國軍在武漢整訓,他代理排長由徐家棚東行,渡江,防守田家鎮,隸屬五十四軍八十三團第三營第九連。「在敵機艦艇轟擊及毒氣危害下,苦戰兼旬,傷亡極大。9月底,九連奉命掩護五十四軍全軍撤退,在江邊的山頭布下三個排陣地,各領一挺機關槍……」
我訝異已隔了半個世紀的事,他仍分明記得,如鄉音,如不斷溫習的鬱結。
「天麻漬漬亮時,哨兵傳報,江上有一群鴨子。」父親用望遠鏡凝望,發現日軍水陸兩用裝甲車上百輛浮在微明的江面,很快就會靠岸。但國軍在江邊挖有三公尺寬的暗壕溝,裝甲車上岸將陷住,暫時可以擋一陣。他重新查看自己這一排構築的工事:機槍在石崖底下,洞口有一大叢黃金柴掩蔽,射擊及裝彈匣的人都可躲在壕洞裡。陣地前另有一條河,聽到河裡的涉渡聲音,即「叭、叭、叭」三發點放。由於黃金柴擋煙,敵人不易發現機槍位置。
雨越下越大,天雖放亮卻仍陰晦,隱約看見遠方山丘有日軍出沒。突見二崗哨踩水往回跑,緊急報告:敵人已連夜包圍此山,排哨已被俘,他二人因外出小解而得以突圍。
「不久,日機臨空,機關槍、六○礮一起開打,陣地幾乎被打翻過來。從拂曉再入夜,連長負重傷垂危,另兩挺機槍沒了聲息。」父親說:「後來只剩我這一挺機槍還維持點放,一整天有槍響,敵人的部隊不敢貿然撲前。」山野無絲毫蟲鳴聲,只有人的哀號、呻吟斷續起落。他想起漸漸沉寂的另兩個排陣地,前一夜還傳出蒼涼的三弦。衣褲被雨浸透,一陣陣寒意令全身更加痠痛。
夜更深時,有同袍偽裝喊話:「陳連長!把你的機槍連拉到河邊防守。」目的是假造出一個營的聲勢。其實父親的排陣地只剩一槍、二人。「叭、叭、叭」他以三發子彈點放作答。不久,後山團防部派的中尉副官尋聲而至,手持黑巾遮蒙的五節電筒,問:「還有多少人?」說是奉團長令來查看。「還有兩人。」父親說。
「團長命撤守,但必須找齊三挺機槍帶回。」
他們憑記憶的方位,摸黑尋找,由父親帶頭,與副官及彈藥兵,推開阻路的屍體。其中一具機槍管還是燙的,上頭血黏黏地俯伏一個殉職的弟兄。好不容易把機槍找齊,一人扛上一挺。原本通過山腰竹林即可達後防,此刻日軍不斷以燃燒彈轟擊,火光通明截斷了他們的去向,只得繞道,將三十分鐘的路程延長成三個鐘頭。途經一座小廟,體力實在支撐不住了,有人提議休息。結果一坐下,三個人全睡著了。
講述至此,父親起身開燈,上廁所。我記得他曾透露,少時遇一麻衣相士,注視他良久,說兩眼間凹下,乃山根薄弱之相,沒有憑依。又說,活不過三十一歲,正應了1938這一年父親的虛歲。
「朦朧中聽到大隊人馬走過的聲音,軍靴喀哩喀啦地踩在碎石路面。是日軍……」父親形容,那聲音直接踩在鼓起的耳膜、跳動的眼皮和腦神經上,三人不約而同地坐起。中尉副官禁不住牙齒打顫,彈藥兵抓起槍想往外衝。父親伸手制止,等敵兵最後一小隊通過,三挺機槍往地上一架,密集捲起一排弧形火煙。敵人沿右邊大路竄逃,他們則乘隙扛槍從左側乾河溝退走,直奔團駐地張家口。天亮以前槍聲不斷,野地不時爆燃開照明彈。從河床翻上另一條小路,他們鑽進了另一片樹叢。
「身上的衣服被荊棘、利石刺得稀爛,血跡、灰土和汗水混黏在一塊兒。人人臉色灰敗,我嘴巴乾嗆嗆,長滿了火疱,擠不出一點口水來。歸隊時,發覺全連只剩下七個伙夫、五個傳令,連同前線回來的我和彈藥兵,計十四員。上級從別連調撥來二員,計十六員新編成一排。全軍再度退往蘄春、黃岡時,已是10月初旬。團長再度下令新編的我這一排留守,阻截日軍!」
父親說,拿下棋打比,這一排就是一顆犧牲子。結果這回敵人沒從正面攻打,繞過了隘口,直接幹上主力部隊。雖然這一年子彈曾劃破父親後頸,命還是僥倖地保存了下來。難過的是,在老家想兒子哭瞎眼的母親卻先走了!
「家裡寄的九封信,您都沒收到?」我問父親:「還記得信的內容嗎?」
「軍中怕影響士氣,全扣了。信是你姑媽寫的。第一信說:媽媽病重,請趕緊回來服侍湯藥……。第二信說:媽媽成天念你之名,茶不思飯不想,喃喃道:『家亨,喔,家亨回來了!』有時精神錯亂,四壁亂摸,放聲大哭。第三信說:媽媽走了,喪事由前媽生的大哥、二哥變賣家產安葬……。第四信說,你的孩子死了,你的妻子譚氏改嫁,你在國而忘家亡家……」淚水在父親眼眶打轉,他的聲音開始嘶啞。出川前父親原已結婚,育有一女。不過年餘,女兒竟然餓死,妻子被逼改嫁,古往今來亂世人的遭遇何嘗有異。
往後幾封信,姊姊氣急地質問他:怎忍心不回信?為何不回信?且追問部隊,這人是否已陣亡?果然已死,死在何處?當部隊轉進湖南常德時,又有一信,欲前來接陳家亨的靈回鄉。這時父親才看到信,他寫報告給團長說,戰事已告一段落,必先齊家才能報國,要求請假回鄉祭母。
團長說:「戰事半個段落都沒有!任何人都不能請假。即使讓你請假,你回得了四川嗎?到處都在徵兵、募兵……」「的確!」父親說:「不被國軍抓走,也會被紅軍擄去。當時紅軍的宣傳是,即使不戰死,也會凍死、餓死、曬死、徒步死,九死一生的路只有到延安。」
父親的部隊從湖南搭貨車兩日夜到廣東;從廣東徒步一月餘至廣西;再從廣西徒步四十天到雲南。其間補給不足,水土不服,兵士精疲力竭,拉痢又患夜盲,散失近半。而抗戰八年的時間也才過一半,距反攻騰衝、血戰滇西還待三年。
今夜我在燈前記下這一鱗半爪,想到父親晚年的無語,很像杜甫〈垂老別〉「棄絕蓬室居,塌然傷肺肝」描寫的心理:人生離合,哪管你老年還是壯年,從此與家庭決絕,肝肺為之痛苦得崩裂!
1988年5月,終於我陪父親回到他闊別五十餘年的家鄉,人事全非,親長無一存者。又過十四年,他卸下身心重擔,埋骨於台灣北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