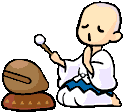我的頭一下子漲大了。
我和丈夫都是O型,女兒卻是AB型。
如果不是檢驗出現什麼問題。
那就意味著女兒的血管裡流的不是他父親的血。
我領著女兒接連去了兩家大醫院。
現實證明了那個不可更改的結論。
我接連失眠,我努力在記憶中搜索,可以坦白的講,我在婚前處過兩個男朋友,都發生過性關係,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個男朋友,如果沒有意外的話,那麼女兒應該是他的骨肉。
十幾年前的往事依昔還在。
雨中夾雜著微小的冰雹,是深夜的冷雨。他打來電話,他在電話中說他病了,問我能不能去看看他。我那時已經結婚半年了,我猶豫了一會兒,還是想去看他,內心儘管挺喜歡他,儘管我們已經有了肌膚之親,但最終我還是離開他,眼淚和疼痛已經成為過去。
他病了。
他在病中想到了我。
我怎麼能讓他一個人去忍受疾病折磨的同時,再去承受其它的痛苦。
我告訴丈夫我有點事,我可能要晚回來。
我來到他面前。
屋內很冷,那是一間租來的簡陋房子,他緊閉雙眼,周身在微微地發抖。
我坐在他的眼前,我把手貼在他額頭,他熱度很高,我帶來了藥,又帶了瓶礦泉水。他服過藥有些喘,我把櫃子裡的所有被子褥子都蓋在他的身上。
我對他說,沒事,出透汗就好了。
他微微點頭,我說我給你做點飯。他說不用,那一雙滾燙的大手突然抓緊了我的手。
他說他想念我。
尤其在病中。
我的眼睛有些發濕,我不知該說什麼。
他慢慢平靜下來,藥物起作用了,他好像睡著了,燈光下,他的臉很憔悴。
我慢慢地抽回手,我給他熬了一些粥,又出去買回些雞蛋,給他做了煎蛋,便叫醒了他。
燒退了,他大概也餓了,他吃得大汗淋淋。
已經很晚了,我回家去了。
他說你過來,我走過去,他慢慢地把我抱在懷裡,那麼緊地。我的嘴被他的嘴親吻,他嘴裡喘著粗氣說,我想你,你不要走。
我們曾經擁有,如今已不再屬於他,但我已在他的懷中,溫熱的胸膛無法抵禦,我已經離開了他,他至今沒有女朋友,他需要。
但我應該有原則。
我建立了家庭就要忠誠。
但我掙脫不了,我在掙脫中心漸漸軟下來,一個病中的男人他在思念我。
他說,別離開我。
我答應著。
窗外風很大,彷彿這個世界只有我和他。我說答應我,就這一次好嗎?
我還有家。
我在黎明時離開了他的家。
過了不久,我就懷孕了。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巧合,大概這是一個逃不脫的命數。
我想隱埋下去,我還想要這個家。
但最終還是被丈夫知道了,他是個老實人,老實的有點窩囊,他心地好,但我一直認為他缺少男人的血性。
他開始用一雙眼睛沉重的瞅著我,沒有責怪,沒有憤怒,只是默默喝著酒,酒後的眼睛帶著血絲,讓人恐懼。
終於有一天,我再忍受不了那雙恐懼的眼睛了。
我說,你為什麼總是用眼睛瞅著我,有話你就說。
他不再瞅我,大口大口地喝酒。
我上前拿下酒瓶說,你不要再喝了好不好。
他憤怒地瞅著我。
把酒給我。
不能再喝了。
把酒給我。
不給。
他上前給了我一記耳光。
把酒給我。
我哭了。
把酒瓶摔在地上。
他從門後拿起一個棒子。
迎頭向我打來。
棒子落在我的頭上。我倒在床上,床頭櫃上有一把水果刀,我抓起來,對他吼,你敢再打我。
他的棒子又落下來,嘴裡罵到,你是個婊子,你是個婊子……
他已經不是過去的他了,積怒已變做瘋狂。
不要打了,你可以不要我,你可以離婚。
我打死你,我不離婚。
棒子一下一下砸下來,我知道他已經失去了理智,我掙紮著,手中的刀紮在他的胳膊上,他看見了血,就來搶我的刀,他一隻手搶著刀,一隻手卡住我的脖子。
他的眼睛充滿了兇殘。
我在將要窒息時用盡全力將刀刺進他的胸膛。
我沒有想到會刺中他的心臟,我只想制止他對我的傷害。
他倒下了,我看著他身體一陣劇烈的抽搐後,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氣,很累的樣子,就嚥氣了。我像傻子一樣坐在他的身邊,我知道他很痛苦,因為他娶了個不貞的妻子,又有了一個不是流著他血液的女兒,他深懷憤怒,他喝酒發洩我能夠理解,但我確實沒想殺他……
我就這樣守著丈夫的屍體坐著,天漸漸變暗了,我沒有害伯,只有絕望,我不知道該怎辦,那天是星期天,女兒去了姥姥家,我想等女兒回來,把這一切告訴她。
大約7時,女兒回來了,她一進屋就驚呆了。女兒大聲哭著說,媽媽,這是怎麼回事啊!爸爸怎麼死了……
我看著女兒的眼睛,我第一次發現女兒的眼睛很像我的那個男朋友,只是我從來沒有往那去想,我抱住女兒,我說媽媽把一切都告訴你。
我對女兒是坦誠的,我把一切都告訴了她,包括我婚前和兩個男朋友的戀愛過程,包括發生的性關係,我告訴她誰是她的生身父親,我告訴她因為有了那個深秋的夜晚才有了她。
女兒睜大了眼睛聽著,她最後說了一句,媽媽我能理解,但是爸爸儘管他不是我的親爸爸,但我很愛他。
我說,女兒,媽媽這一生就快結束了,我希望***,死了就什麼都結束了,如果不死,我會永遠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
那是一種殘酷。
女兒說,媽媽你該怎麼辦呢?
我說媽媽明天去自首,今天我要去看看你姥姥、姥爺,以後我怕就見不著他們了。
女兒跟著我去了姥姥家。
路變得遙遠。
——媽媽,我以後怎麼辦哪。
——去姥姥家吧。
——那姥姥沒有了呢?
——姥姥沒有了,你也長大了。
我拉著女兒的手,攥得很緊。
我和女兒在媽媽家住了一宿,到第二天早晨,我又回到了家。
我把丈夫身上的血痕擦乾淨,給他裡外換上了新衣服,
讓他幹乾淨淨地躺在床上。
然後我去派出所投了案。
我沒有被判處死刑。
但我的心已經死了……
摘自:職工快報:《調查女子性過錯》系列報導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