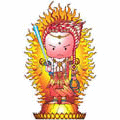一位高官,欲當局長。有三位競爭者。這位官員姓鄧,其他三位是趙、陳、梁。鄧來問我:「可任局長否?」我答:「可。」
經過了約半年之久,局長任命下來,不是姓鄧的,而是姓陳的,姓鄧的大怒,來質問我,當初神算說可任局長,何以今日卻不准了,這還算什麼算?什麼神算第一?根本不靈不應?豈不是騙人嗎?鄧問:「如何說,你怎麼說?」我答不出來。面紅耳赤。鄧再問:「你不是說可嗎?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啞口無言,我只得回答:「其實我是不知道的,我只是聽司祿神說的,祂怎麼說,我怎麼答。」「司祿神?司祿神在那裡?」「司祿神是無形的。」「真是廢話。」鄧極度的不滿。當我神算不準的時候,當人們質問我的時候,可以想見的,我的處境非常的尷尬,神情自然很頹喪,真的只有無語對蒼天了,我這時候,也只能呼叫蒼天。
正當此時──我的眼前一亮,司祿神出現了,這神吏手書一「淫」字,給我看得一清二楚,「淫」字底下是某月某日。
我告訴鄧:「你犯淫戒!」鄧答:「沒有。」「某月某日。」鄧仍然答:「沒有。」我傻了,明明司祿神手書「淫」,又有某月某日,指示非常清晰,怎會可能沒有,我不相信。我說:「請清楚想一想。」鄧想了想,又仔細的算了算日子,仍然答:「沒有。」
這時司祿神又指示我,鄧是偷窺鄰女洗澡,我聽了司祿神講偷窺洗澡,心中就想笑,但不敢笑出來。我對鄧說:「不是私通,而是偷窺鄰女洗澡。」鄧一聽,換他傻住了,他不再說話,低著頭走了。
據我所知,鄧的情況是這樣子的,鄧原本是局長的格,約幾個月前,鄰居搬來一位單身女郎,模樣俏麗,人也落落大方,鄧對她多注意了幾眼。鄧有一窗,巧對鄰居浴室。某月某日,鄰居女郎沐浴,忘了關窗簾,鄧剛好看見,於是鄧取來望遠鏡,從頭看到尾,從頭看到腳,口中嘖嘖稱讚不已,而內心也極度興奮。口中言:「能與此女一度春風,也不枉虛度此生!」眼看心想。心癢難抑也。
司祿神說:「雖然鄧與鄰女事情雖然未成,但鄧窺見鄰女沐浴,應該即時迴避,非但未迴避,竟然從頭偷窺到尾,不但眼動,其實心也動。淫慾之心一發動,雖非有淫事,也已犯了淫戒也,因此削去祿位,須六年後才當局長。」
●
又有一回,一位呂固中將到我處。呂固說:「XX,聽說你神算第一,所以今天我來請問你。記得早年,家父母請來一位鐵板神算的葉師父,替我占算,說我十八歲就拿到全國大學聯招的狀元。後來入軍事研究所,二十七歲取得博士學位。三年赴美,又取得另一博士學位。五十三歲時,將官達上將。」
呂固接著說:「這位鐵板神算的葉師父,是非同等閒的師父,要請他批命,一定要重金,他批命也要看人,小命運的他不算,同時要排期預約,並非隨到隨算。葉師父給我批的,非常的准,我真的十八歲時,全國大學聯招得第一名。然而二十七歲取得博士學位,卻差了一些,我二十九歲才拿到博士學位。三年赴美,取得另一博士學位是真的。五十三歲官達上將,這就差了,如今我五十六歲,仍然是中將,始終和上將擦身而過。現在我要問盧師父,請你算算我一生的命運,又何時會當上將。」
我用我神算的方法,替呂固算了算。我手掐「祿」字手訣。再按時辰手訣。最後用「召請」手訣。我念:「咒起翻雲擾海,指向法界虛空,動處如鑰開鎖,靜處如日破洪,照見陰陽交感,現出司祿仙翁。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這咒念三遍。司祿神如一點星光,漸漸變大,出現了。
我問呂固一生命運。司祿神的回答與葉師父所算無差。我又問:「何以得博士,卻遲了兩年?」司祿神答:「原本他可以如期拿到博士學位,然而他卻和一些年輕學子,在一次酒後,去了娼家,同學鼓舞他,他為了表示有膽,和一位青樓妓女奸宿一宵。因此,遲了兩年。」我問:「娼妓一宿,便差兩年?」司祿神答:「莫看青樓妓女,倚門百媚夭斜,須知君子惜身家,護玉一般深怕。彼自落花有瑕,我終白璧染污,破財傷身誤生涯,染毒罹痾禍大。」司祿神再說:「遲了兩年,只是小罰,染了毒就死了,博士成了博土,又成了博死。」我捲舌無語。
我又問司祿神:「呂固應該在五十三歲升至上將,又何以今年五十六歲,才是中將,而且未擔任重要職務,何以故?」司祿神寫了二字給我,此二字是:「莫書。」「莫書是什麼意思?」我好奇。司祿神答:「人名。」「此人和呂固有關?」「自然。」司祿神說:「呂固算是世間才士,文武皆備,少壯犯一娼妓,已遲兩年,只是小罰。中年之後,卻不知改過,竟然喜男色,莫書者,弱冠才華,丰姿韶秀之下屬者也,呂固與莫書共聚八年。呂固官至中將已是僥倖,何可有上將重職之想,他只求自己祿位,竟不知已惹下孽障。」
「呂固將來如何?」我問。「報在其子。」「其子如何?」「絕嗣夭亡。」司祿神說。我聽了大駭。
我對呂固先談差遲二年拿到博士學位的事。呂固回答:「是有的。年輕時,大夥一起去,大家好玩,想不到就這麼樣,真的遲了兩年。」
再提到何不能當上將?我寫了「莫書」二字遞了給他看,他看了「莫書」兩字,低頭不語。「可有這等事?」我問。「有。」呂固點頭。
呂固站起來,對我說:「XX,你果然神算第一。然而,我終於也明白了,人的命運,雖有天定,但,事實上也一樣會改變,變來變去,唯在自心。」
「說得好,希望你自心體會,免得遭報!」呂固走時,我給他一張紙條警語:「男女居室正理,豈容顛倒陰陽,污他清白暗羞愴,自己聲名先喪,浪費錢財無算,戕生更自堪傷,請君回首看兒郎,果報昭昭不爽。」
過後不久。呂固果然獨子發生車禍身亡,真的絕嗣!司祿神厲害。
●
再有一件有關「司祿神」的事──有袁茂者,是工廠老闆,業五金。早年來問事。司祿神答:「十五年後,大富商。」
結果是,約十多年後,袁茂經營的工廠倒閉,袁茂因借貸太多,負債纍纍,逃到國外,從此流亡海外,無法回到自己的國家。袁茂在海外很辛苦,他在跳蚤市場擺地攤,收入非常微薄,他也當建築工人,原本是工廠老闆,如今卻在屋頂上爬來爬去,結果建築不是內行,被辭退。袁茂在一家餐廳打工,勉強餬口。
後來,袁茂在海外,查訪到我住的地方,坐了灰狗巴士,趕來找我。他在灰狗巴士上,共搖晃了三天兩夜。我清晨看見他,嚇了一跳,昔日的袁茂,西裝筆挺,油亮的頭髮,出門有黑色大轎車,有司機及秘書。今天的袁茂,一頭灰白髮,不修邊幅,一件破夾克,皺紋爬滿臉,風塵僕僕,一幅潦倒的模樣,狀至可憐。我請他進屋內,倒了一杯熱牛乳給他,又請他吃了麵包,他連早餐都未吃。
袁茂問:「司祿神說十五年後,我會成大富商,如今?」「現在幾年了?」我反問他。袁茂用指頭算了算:「剛好十五年,司祿神不准了,你神算不靈了!」「我。……」我回答不出來。袁茂一臉的委屈及無奈,問:「怎會不准不靈呢?」「這。……」
袁茂說:「當年,我的工廠做的最輝煌的時候,也曾請你到工廠來看風水地理,依照你的意思,改正了缺點的地方。也曾請你神算,你說十五年後,一定大發,十五年後是人生的最高峰。如今,正好十五年後,我潦倒如此,你怎麼說?」「我,我也不知道。……」我汗涔涔下。
袁茂說:「現在,我走投無路,你說我怎辦?」「我再幫你算算如何?」「算?怎麼算?」他似乎有點火大。
我閉上眼。竟然看見司祿神,左右手各牽了一個小孩。「誰的小孩?」我問。司祿神答:「袁茂的水子靈。」呵!我知道了,袁茂在這十多年中,殺了生,拿小孩子,所以有兩個水子靈。我說:「袁茂,你殺了生,你的女人墮胎拿了兩個小孩。」袁茂答:「墮胎的多的是,罪有那麼重嗎?」司祿神再現,搖頭示我,用手指向虛空,虛空中現出一座尼姑奄,一位嬌美年輕的比丘尼走了出來,左右手各牽剛剛的那兩名小孩。
這下我駭然,當下明白。我說:「袁茂你夭壽,你污辱比丘尼!那兩名水子靈,是比丘尼生的,是嗎?」這回換袁茂額頭有汗水。「這…這…,這比丘尼也喜歡我啊!」「唉!」我歎氣:「佛寺中有佛有菩薩,有金剛有護法,比丘比丘尼是清淨的修行人,如果去引誘之,這是罪加一等的。你行為不檢,淫比丘尼,連生二子,又墮胎,這是何等重大的罪業,今之潦倒,其來有自。」「是這樣嗎?」「當然是。」我答。
「我以後怎辦?」「發誓持戒,我認為你必須寫疏文,列出你的姓名八字。簽上你的名,對天地立下誓言,焚文書,告於天地,從今懺悔前過,以後舉止動念,務必戰戰兢兢,完全不涉及邪淫,永斷孽根,重新走回正路。不只是如此,以後心存善念,時時以口或傳單,勸人勿邪淫,經雲,戒邪淫,得五增福,也可避三塗惡道之淪也。力圖自振。」袁茂聽了,唯唯稱是。
有一首修行犯淫的詩詞:「彼即修行出世,豈容覓趣調情,敗他戒行壞他名,不顧佛家清淨。神目赫然如電,男女借隙相乘,官刑冥罰禍非輕,真是墮身陷阱。」
我送走袁茂。給他兩千元美金,期望他永遠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