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思想漫談(一.) | |
作者: bv4pr (BBCAL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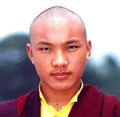


緣起思想漫談(一.) | |
作者: bv4pr (BBCALL) |







至於這個問題也值得思考:
意識的定義又是如何?西洋哲學家笛卡爾,認為,靈魂(意識)是精神實體的屬性,
知覺、思維、意志、願望等是意識的形式,是精神實體的表現形式。笛卡爾的說法
正是反應了一般人的看法......
請問印度對於"意識"的定義,與佛陀對於"意識"的定義,和迪卡爾對於"意識"定義是否相同?
這問題就和這個情況一樣,法華經初品裡面把佛陀的名號說成:如來,應供,正遍知,許多提到佛世尊的時候,這三個號同時出現。其中,應供就是對照梵文,就是阿羅漢。那南傳佛教的信眾就會告訴你:佛陀,就是阿羅漢,連法華經都這麼說了。請問他說的是對嗎?
這名詞是小問題,事實上蘊藏的是大問題。南傳佛教的儀軌裡面開頭就是唸誦:
難無 達色 巴格瓦督,阿剌哈督,三藐三佛陀舍。
這就是南無 世尊,阿羅漢,正等正覺。
南傳佛教所皈依的是和大乘佛教說的是一樣的,請問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
其實法華經對佛的稱號,和南傳佛教拜的佛稱號在文字上是完全相同,可是內涵是不太一樣的。佛陀,為什麼有十個稱號?
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這十個稱號,是當時印度各宗教對於佛陀的敬稱。好像阿羅漢,耆那教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羅漢。各種眾生認為佛陀是他們眼光裡面成就最高的,所以事實上佛陀的稱號應該不只十種。甚至於,假如佛陀出世於以色列,也許他就會被尊稱為彌賽亞。佛陀如果出生在中國,也許就被尊稱為"釋迦子",甚且名列三清之上的一清都有可能。
那梵志是什麼?梵志,根據梵文與巴利文的名稱,知道是與婆羅門行者有關。梵行呢?其實也是婆羅門教的名詞。涅槃呢?涅槃是婆羅門教的理想,佛陀呢?佛陀也是在梵書裡面曾經提到過的理想。是因為有"佛陀"這個名詞,我們才知道釋迦牟尼佛被尊稱為"佛陀"。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請問"見性成佛"與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修成正果的"佛果"是否相同?答案是很大的不同。"見性成佛",是"見性"成為"覺者",是看見了成佛的路的修道者,但是離開釋迦牟尼佛的成就還差得很遠。因此,名詞的定義很重要。名詞就代表了背後所聯結的文化。換言之,實在看來,這些名詞的出現,就是告訴我們,佛教與印度傳統文化是緊密相連的。
我們長期以來已經把佛教當作是中國的宗教了。用中文的眼光去思考佛教的一切,常常讓我們用這部經的名詞去想另外一部經的名詞,串來串去,不知道有時候漢譯有特殊考量,或是法師在譯經的時候已經賦予了特殊的意義,這意義是中國文化裡過去所沒有的。所以佛教的"經學"必須重新再建立。經學要重新建立,就必須從訓詁再開始!
佛教有沒有自己創立的名詞呢?似乎也是有,"菩薩"這個名詞似乎只有佛教強調。但是中國佛教是把所有的佛經裡面名詞一概視為佛教的。事實上,佛教裡面有很多名詞不是佛教創立的,但卻是佛教把它們賦予了更高層的意涵。但是這對中國而言,卻是新鮮的。
要了解佛法,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 那就是回歸到印度人的眼光來看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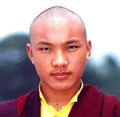





要解決佛法的問題,必須從最根本的名詞定義上來看。
近日參加一場研究生論文的發表,雖然都是用英文進行答辯,但是明顯得看出一個趨勢,那就是佛法的問題必須回歸到原始語言的研討上。
同時近日與仁波切研討漢藏佛法比較問題,我們也不約而同察覺到,古代遺留下來的佛法,造成我們無法深入經藏的問題,必然是經典語文詮釋問題。我曾經比對法華經序品,在一個段落裏頭,竺法護說有十六位弟子,鳩摩羅什卻說有八百位弟子,還好今天流行的是鳩摩羅什的版本,假如有擁護竺法護的版本,那兩邊可有一場論戰。問題很簡單,只要你有梵文原本能讀,就解決了。答案是八百位,因為梵文與藏文都同時記錄是八百位。那你看,漢譯的名詞問題是否需要我們更加留心呢?
還有一個例子,這個沒有人講,大家也不會知道。金剛經,有一首很有名的偈頌: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鳩摩羅什是這樣翻譯的,可是呢,問題就出在於,他沒有把下面另外的四句偈再翻譯出來,下面的四句偈是講法身的問題,說明如來的境界就連第十地菩薩也不能了解。多出來的這四句偈,梵本有,藏文本也有。這是仁波切翻譯藏文金剛經的時候告訴我,我才回頭來去找梵本才知道的。
我前面有講這個問題:見性成佛的"佛",是指釋迦牟尼佛的境界嗎?顯然不是的。法華經上面稱許許多如來名號,在序品裡面稱許日月燈明如來,是如來,應供,正遍知,這是鳩摩羅什的翻譯,翻開梵本,卻是如來阿羅漢,正等正覺。那為什麼要把阿羅漢與如來放在一起呢?我也把這個問題向仁波切請教,才明白,這個阿羅漢與阿含經講的阿羅漢,是有很大的不同。大乘經典這裡的阿羅漢,是以印度文化為背景的阿羅漢來說的。
問題在哪裡?在這裡:中國人是用中國文化的眼光來接受佛法。而不是用佛法,特別是印度的佛法來看佛法。
中國文化的好處在於,中國人可以閱讀千年以前的典籍,傳統典籍在中國來說是沒有時間限制的。但這一套維繫了中國文化的典律,重點在於每個時代都有人再做時代性的解釋,也就是訓詁學為基底的經學,因此中國人可以理解千年以前春秋戰國典籍而不會產生矛盾。但佛典卻是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這從大正藏裡面看到相同的經典可以翻譯多次的情形可以看出。事實上,假如有原本,多種譯本的保存是沒有必要的,頂多保存了重要的流通本就好了。佛法來到中國,充分做了中國的在地化工作。但是在地化,也必須要保存充分的理解基礎,也就是相關的知識背景必須充分而全盤性的保留。就這點而言,西藏無疑地是超越了漢傳佛教的。
我舉個禪法的例子,為什麼禪宗那麼神祕?其實禪宗並不神秘。神秘的是我們對於"禪"一無所知。事實上,禪並不是佛教的專利。禪是印度文化。早於禪宗以前,印度的宗教,大家都在修禪法。瑜珈就是這樣的東西。如果讓我當禪法的老師,我會希望先教瑜珈術。要了解瑜珈,得先了解亞利安人的想法。
亞利安人相信自己的祖先原來是從"天界"下降的,是會飛行的,而且是全身發光的那種"天人",所以他們看不起地球上其他的人種。他們認為他們是來地球做客人,這和客家人的想法很像,客家人祖先認為自己來南方是作客的,總有一天他要回到中原,他的家鄉去。所以他們想盡辦法都在保存文化,宗族的意識很高。我講這樣是沒有貶的心意,只是說明這是一種意識。亞利安人就是有這樣的意識,認為他們是天人的後代,只是當初祖先來到地球,吃了地球上的穀物,慢慢地執著於地球的一切,身體越來越重,飛也飛不了,到最後只能住在地球上。但他們始終對於家鄉有一種很強的眷念,他們想要回家。那要怎麼樣能夠回家呢?答案就是要用天界的思想與生活方式來過生活。那就是瑜珈,和"達摩",也就是所謂的"法"。
信奉婆羅門教的印度人始終相信,他們必須過著與"天人"相應的生活,這樣才能讓他們"解脫"於地球的生命。這就是為什麼印度人始終都很堅持宗教生活的理由,那麼強調戒行的原因。因為他們就是要ET Go Home。他認為自己不是地球人,是來地球當"客人"。
在婆羅門的信仰裡面,成為一位解脫的聖者,是充滿著智慧的光明,所以認為光明很重要,智慧等於光明,光明也等同於智慧。所以婆羅門就拜火,向火神Agni敬拜,婆羅門教很多儀式都和火有關,而且這和波斯的"拜火教"也是同宗的(其實古代亞利安人是從烏拉山區東西兩個方向移動,往東移到印度,往西移到波斯,就是現在的伊朗)。亞利安人就在這個強烈的意識下,發展了自己的"宗教文化",也就是吠陀為主的文化,堅持"去地球化"的生活,建構他們的人生觀。
我們在佛經裡面常常看見淨行,梵行這類的名詞,其實這就是和婆羅門教傳統有密切的關係。不論是淨行,或是梵行,都是從這個"Brahman"單字翻譯過來的。它就是被翻譯成"婆羅門"的那個單字。這也就是佛陀在阿含經裡面不斷在強調的那個淨行的主題。Brahman為何被翻譯成"淨"?那個根本的思想,就是婆羅門要回到天界的"相應"之行。"去地球化"是主要的思想內涵。婆羅門始終堅持他們是要回家,不是要來地球移民的。所以印度教的"梵我合一"是甚麼意思,簡單講,就是要回家,回到梵天的那個家。
所以佛經裡面,尤其是大乘佛教,不是常有大梵天王蒞臨佛講經的會場嗎?這是甚麼意思呢?因為就連婆羅門的家鄉的主宰者,梵天的王都來拜在佛陀的座下學佛,這說明佛法確實是宇宙間最尊貴的,也最能降伏婆羅門來學習佛法。但是這段經文因為漢人沒有印度文化的知識,恐怕是很難理解這層意義。
圍繞在吠陀文化裏面,瑜珈是一個重要的支派。瑜珈就是婆羅門要"回家"的手段。瑜珈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解脫,所謂的"解脫",其實就是恢復到婆羅門祖先的那個身分,成為"大梵天人"。
所以印度教努力強調的修行,其實就要回家的作為。
但是佛陀告訴我們,他的法,不是要回家。事實上是要從六道裡面去解脫的。可是佛陀用的名詞,都是與印度婆羅門教及相關宗教有關的名詞。那你要是不懂這些名詞原來的涵意,你可能真的會發生誤會,或者摸不著邊際。




所以阿含經的原典很清楚,婆羅門就是婆羅門,世尊,就是博伽梵這個單字,如來,也是古代印度宗教就有的理念,很多東西並不是佛陀發明的詞彙。可是佛陀最厲害的是善用印度文化來解說自己的義法。
阿含經理面,常常我們可以看見佛陀都在和印度宗教作對話。假如你不把握這一點,阿含經你會看不懂。佛陀用的是印度宗教的名詞,再做更深一層的剖析。我們都知道佛陀降伏了很多的六師外道與婆羅門教,但是這六師外道與婆羅門教的徒眾是怎麼看佛陀的,這個漢譯本無法告訴我。因為這需要熟悉六師外道與婆羅門教信徒的語言,你才能夠清楚。原來佛陀原先是讓六師外道與婆羅門教徒看做是"自己人"。六師外道以為佛陀是反婆羅門教的同志,婆羅門教徒以為佛陀是教典裡面傳說中的聖者。不然佛陀早讓印度宗教信徒當作是大外道,而驅趕出印度了。你想今天在台灣有人說我就是佛陀,這不正讓大家拿著掃把去趕他出國嗎?
佛教裡面很多東西原來就是印度各宗教本有的。這點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到佛教消失在印度次大陸以後,印度教仍將佛陀放置在極高的位置情形,印度教並不排斥佛陀,歷史上印度也只有這麼一尊佛陀。印度教認為佛陀也是開示一條解脫的道路,讓他們可以回家,只是佛陀並不是最高的,就對了。
佛陀常常是用印度當時的宗教名詞與印度當時宗教的理想,因此我認為佛陀是對印度文化做的一種回應。但,這可能和佛陀的本懷,比較有距離。阿含經裡面你常常看到,佛陀在對婆羅門開示,特別對他們講了很多的"梵行",你是否會以為婆羅門教徒不懂"梵行",需要佛陀這樣教導他們?事實上,佛陀在成佛以前,他也是婆羅門教徒,這一點我們不要忘記了。佛陀在成佛以前,也是精通瑜珈的瑜珈修士,當時印度的瑜珈修士能做到的,佛陀都做到了,所以佛陀能夠獲得印度宗教普遍的認同,他才有辦法可以降伏外道。所以佛陀的十個名號,不是浪得虛名。最重要的一個意義是:各宗教信徒都以為佛陀原先是"自己人"。佛陀擅長以其人之道,還治彼身。
西藏的佛法教育是承襲那爛陀寺院的傳承。在那爛陀的寺院,除了佛法以外,還有很多的外道教法教學,這所謂的"外道",並非把它們都比了下去。其實這些都是佛教的基礎。但是漢傳佛教,很可惜還缺少這個東西,有待我們去補闕圓滿它。事實上你也可以去比對高僧傳,漢傳佛教早期來華的印度大師,很少人不是精通五明吠陀的。這五明吠陀,都是印度文化,到現在西藏還在教授這些,甚且大陸也已經計畫出版了相關的著作"十明經典",這十明經典,事實上不是源自於佛教的,而是道地的印度本土文化。
但是西藏佛學院教育承襲了那爛陀寺的傳承,它是告訴你,一山還比一山高,各宗教的境界都很高,但是最後最高的,還是佛陀的境界。你如果不通過這個程序,你也許摸不著邊際,人生下來為甚麼就是要成佛?我不要成佛可不可以?
對於印度傳統的瑜珈來說,我已經修到了與大梵天合而為一,這就到了終點站,我可以回家了。印度教最高的境界就是回家。可是佛陀的教法是,你為什麼浪費了瑜珈,不讓自己成為自由人呢?你可以和梵天平起平坐,甚至於可以超過梵天的水準,超越了六道輪迴?但是你要是不懂印度原來的瑜珈體系,你也許會覺得,和印度傳統瑜珈相比,佛教的太枯燥乏味了。
其實佛教的禪法,瑜伽與印度傳統的禪法,瑜伽是密切相關的。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印度的瑜珈要引導你回到大梵天,佛教的瑜珈是要引導你成為自由人。




我之所要提倡學佛從名詞開始,特別要從梵本開始,是因為這樣才能容易理解原本佛陀所說的,經過漢譯以後,很可能因為時代久遠,曾經也許祖師在譯場裡面宣講過,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年代久遠,資料散失了。我舉個例子,佛經裡面有"眷屬",中文的意思是"家屬",我查梵本以後才知道,這個字的意思是"跟隨者"。又如法華經序品裡面有一個字,鳩摩羅什大師翻譯成"八百個弟子",我查梵本,才知道是八百位同住一起的人,不一定就是那位菩薩的弟子,只是很可能那位菩薩說法的時候,這八百人是聽眾。
讀梵本也不是我發明的。早在過去南北朝時代就有祖師提倡要大家讀梵本,並且認為翻譯本不見得能夠充分表達梵本原意。更何況,中國雖然早就接受到佛教,但是到了重要關鍵的時代停了下來,使得後來發展的佛教大學教育體制沒有能夠接受到,這對漢傳佛教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這也就造成現在大家常常在講的:佛法怎麼這麼深?難道不能在淺一點嗎?我查梵本,發現佛法本來就不深,釋迦牟尼佛講經是用白話文講的,問題是在於我們基礎不夠。所謂的基礎並不是我們領悟力不夠,而是基本佛法詞彙定義我們不了解。就拿瑜伽行的論書來講,很奇怪,我過去不曾聽說過,其實卻可以這樣做:為什麼沒有人想到拿印度本有的瑜珈理論來和瑜伽行理論比較呢?
事實上,佛法是科學的,是有知識層級的。就拿瑜伽行來說,其實印度傳統瑜珈的課題,和佛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課題,也是相同的問題,甚且修行觀念是沒有差別的,所不同的地方在於:印度傳統瑜珈目標是要梵我合一。一切教法是為了這個目標而建立的,佛教,是在釋迦牟尼佛修行瑜珈,獲得的成就高出了傳統印度瑜珈的層級,了解了緣起性空的道理。這才重新整理教法,發展了所謂佛教的瑜伽行派思想。事實上瑜伽行派講的東西,就是借用了印度傳統瑜珈的概念去講佛教的道理。佛教在印度講瑜伽,是沒有甚麼好奇怪的東西,印度人都很清楚。但是來到中國,就成了很奇怪的東西。中國過去也只有求仙成道的道家思想有類似的東西,所以一開始佛教的譯經者就拿道教名詞來翻譯佛典,竺法護的正法華經就有這個味道。所以我過去曾經主張我們要讀梵本,就是要講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對於陌生國度的宗教,當你想要傳這個教給他們,請問你要怎麼傳?藏傳佛教來到台灣的時候,還沒有發生過這個問題,因為藏人都從台灣學佛人那裏知道一些漢傳佛教的名相,所以一開始大經大論都不敢開講,你很少聽過仁波切會說:我要開講"華嚴經",對不對?也很少仁波切會說:我就開講"中觀論",是否?但你時常聽見仁波切傳某菩薩的法,或是某某本尊的灌頂,為什麼反而灌頂會比講經論還流行呢?因為問題就出在翻譯上面。你參加法會的時候,你會發現到,明明是藏傳佛教的法會,可是聽起來仁波切很像是我們漢傳佛教法師的開示。因為藏傳佛教的仁波切剛來台灣,用台灣的翻譯,當然就是拿漢傳佛教來格西藏佛教的義理嘛!那你想,大經大論都不敢開講,那無上瑜珈怎麼能開講?
剛開始,佛陀在中國就是被當作神仙來看待的。自古以來,儒家不講修行,講的是"修道",與"修養"。道家與方士才有"修行",所以佛陀最早是被看成"大羅金仙",簡稱"大仙"。但是在姚秦時代,鳩摩羅什很清楚告訴大家,佛教與道教有些不同,所以放棄了過去的以道教來解釋佛教的方式來翻譯,重新再創造一些佛教名詞,這在"出三藏記集"這本書裡面,作者曾經以專章談過這個問題。簡單講,鳩摩羅什開始引進了音譯詞。例如般若,這個我可以確定講,這不是印度傳統宗教的東西,真的婆羅門沒有般若這種概念,是佛教突出於印度傳統宗教的東西。你想中國佛教為了佛教名詞搞了真的很久。這其實和現在仁波切在台灣弘法的情況類似,名詞搞不通,大概經論無法開講,只好傳個咒讓你好好先念一念,或者乾脆讓你或你家小孩先去印度留學當喇嘛,學成歸國,才開始慢慢開講經論的情況一樣。中國佛教開始有法顯,玄奘,義淨這類人物,等於是華梵兩種語文兼通,真正的佛法才開始慢慢讓漢人理解。
我們中國人學佛,喜歡從"經"開始,這是受了儒家的觀念影響。文心雕龍裡面就認為"宗經"是文學最重要的根本道理。佛經與四書有何不同?其實英文的名詞我覺得比較能夠形容:teaching,也就是口頭教誨。佛經的文學體制就是以一時,某人,某處,聽眾等固定形式記載,這表現出佛陀的教誨常常是特定的時空情況下來開講這個法義。這其實對於後人來取捨佛法來說也是沒有甚麼妨礙,都是佛說的話。但是假如眼睛尖的人會注意到,佛陀涅槃以後,第一次經典集結時候,除了經與律以外,還有所謂的"論"。"論",阿毗達摩,就是初階佛門課本。你要說佛教後來有部派出現,其實就是佛學入門課本不一樣。那我們中國常常講,不管你怎麼說,佛陀是老大,佛說才了算數,偏偏常常我們可以在佛說的內容裡面找到一些矛盾現象。法顯玄奘等人就是為了這個問題才做出了西行求法的壯舉。這個你可以對照西藏情況,到了經教教育完備以後,西藏也停止了前往印度求法的行動。所以經教不完整情況下,中國僧人才想到去原產地問個清楚。很可惜遇到了唐朝糊塗皇帝,唐武宗滅佛,大規模的華梵交流停止了。到了宋朝雖然還有幾位印度來華高僧,但是對於中國佛教已經沒有影響。佛教的知識體系建立停頓,講究當下即心解脫的禪宗大行,佛教教育的問題從此就被漠視了。
讀梵本,是漢傳佛教的新希望。從梵本裡面,我們可以探索得到,佛陀此番教導可以從印度的甚麼文化裏面找到線索,這是很重要的。翻譯文學就是有這個特性,莎士比亞是我們中國人說的,但是他的作品翻成了中文以後,恐怕有些原作品的韻味走失。最明白的就是我們中國詩人李白詩歌傳到西方去,到現在李白詩歌的英文版也沒有所謂的"定本",而且常常變成翻譯學界拿來討論的題材。文字與文字的對譯,當然可以找得到對等性質的名詞,但假如你不是強調操作性質的科技類書籍,通常這種文字彼此之間的對等性是模糊的,也就是說一個文字出現在一本書上就常常有其文化背景的意義。這常常是翻譯工作者很煩惱的問題,特別是小說與電影。你看電影,Top gun這部電影,你對全世界講這部電影,究竟怎麼翻譯才能顯出這部電影的真實意義呢?台港地區說那是:捍衛戰士,大陸曾經就翻譯成"好大的一把槍"。同樣都是中文,這兩個名稱是不相等的,但是在內容實質上,是否能夠彰顯男主角湯姆克魯斯的作為呢?
所幸,中國的禪宗提出了一個有趣的作法,那就是你要去"悟"那些經典裡的話,就這樣一筆帶過了幾百年,到現在還是不變。在禪宗的歷史上,許多僧人問了祖師同樣的問題,但總是文不對題。到最後,大家得到的是否是相同的答案,也都是盡在不言中。
中國禪宗到現在提供了世界上的文學題材,但是能否對於佛法,特別是操作上需要的,確實是不得而知。也許這是過去他們向來強調的不立文字,不著文字有關。所以佛法,就成了哲學上的玄學,與文學。
反過來講,假如你把名詞與定義弄得很清楚,佛法可能就不再是哲學與文學,很可能就是科學。但是如果你在名詞上面定義上不清不楚,爭議當然也繼續跟隨下去,沒完沒了。
相對於印度教情況,現在印度教也對於自己教義上做了整理,我新近閱讀的有關瑜珈的書籍,有一本就覺得還不錯:瑜珈哲學十四講(北京,群言出版社),裏頭第一章就提到,瑜珈從研究我們人類的身體組織開始。佛教過去給西方人,或是給中國人一個印象就是玄妙二字,假如你在佛法裡面找不到答案,也許在印度傳統的宗教思想裡面就會看見你想要的光明,也說不定。
那爛陀寺裡頭外常常有很多人在學習,外道不是外道,那是用來理解佛法大海的助緣。










假如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日本佛教,韓國佛教都和我們沒有差別,哪裡讓我們有機會去看看問題出在哪裡?這就是重點了,假如在翻譯的那一關就過不去,那現在你讀的經是甚麼呢?其實,我的想法不是推倒現在的漢傳佛教,而是找尋失去的漢傳佛教,漢傳佛教是否錯誤,我說的不是這個問題,我說的是因為年代久遠,祖師大德講過的東西,很可能失傳了。意思可能被錯解了。中間一個轉折,東西就不見了。各位要了解,我們現在讀經,常常都是用中文解中文,特別是通過了禪宗的不立文字,乃至否定文字的過程,讓你失去了從文字語言內容去了解,那個重要的文化背景,佛教裡面很多思想不是建立在中國,就像前面楊松裕兄所舉的般若是假名為例,如我了解的印度佛教的情形,世尊借用印度宗教名詞去詮釋佛法,當然這就是成立的,奇那教的最高果位是阿羅漢,在佛教裡,假如也說阿羅漢是最高果位,那與耆那教有何分別?事實上確實有分別,可是那是要精通瑜珈的行者才有辦法分別,一般人實在很難去理解。
假如一切都否定文字,這樣也不要讀經了,是不是這樣的邏輯呢?佛教被人批評為迷信,正就是這種強調只要相信,而不細究真理的態度。如果對經教的理解都不正確,果報怎麼會正確?
起碼現在還有梵本,現在還有藏傳佛教可供參考,還有亞洲鄰國佛教可供參考。我實在個人能力有限,只能做這樣的呼籲而已。
經學很重要,起碼儒家已經做到了,讓千年以來的人都能充分掌握住千年以前古聖先賢的人所講的意思。所以現在的儒家講起論語,孟子,都有共識,就是依照十三經註疏可以依循。我們佛教要依哪一本注疏,都還有人可能會批評,因為受了禪宗的影響,要批評你執著文字。對初學者來講,你還是要有文字可以執著,才能接引啊!對於普遍的社會大眾來說,我們要給一個說法,給一個邏輯,讓大家了解佛教不是詐騙集團,這就是我正在努力的方向。




現在我們學佛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我們對於古德高僧的了解,可能比對釋迦牟尼佛的了解還多。我們對於中國佛教的教制了解,確實超過了對印度的了解,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漢傳佛教究竟是中國的佛教,還是佛教給中國化了,對我而言,我希望是後者。起碼你對你的祖先應該有清楚的認識,才知道你後人該怎麼修正方向,追尋先人的步履。
像這個主題:緣起性空,你不覺得很抽象嗎?我看這種題目已經十多年了,一天到晚講的都是名相,然後人家問這是什麼?得到的回答總是:甚深,甚深,你的業障很重,很難了解。這是千篇一律的回答方式。問題是:回答的人自己是否也了解,這也還是問題。隔壁版有位師兄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佛教這麼複雜?這就是社會人士對佛教的普遍印象,但是大家都不敢批評,因為在想:是不是有什麼神明會來懲罰我?佛教並不是靠虔誠來堆疊的宗教,追求真理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一貫的態度,我們可以強調信仰,但不能因此阻止人去理解。
君不見漢傳佛教只存在了"佛",而缺少了"法"。那麼多人要去學藏傳佛法目的為何?就是一個"法"字,一條可以達到理想的道路。我作的學問就是在找這個。
大概要了解佛陀,真的還是要從了解印度開始。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努力把佛經內提到的印度文化,相關的東西做個了解,而且對於梵本名詞作個了解,訓詁,我想這對講經的法師會有很多幫助,起碼漢傳佛教的名相會比較清晰一點,不會那麼迷糊了。大家知道吧,我曾經講過,佛教的梵本,巴利本原來都是白話,淺白地去解析一些東西,可是次第很清楚的。因為世尊是很認真的人,很講求邏輯性,他要你不執著名相,那前面是有一堆次第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經過一系列的訓練,你才能達成"不執著文字"。問題是在於這系列的訓練在中國讓佛號,無厘頭的禪坐給取代了。其實這些次第都還是從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日常生活訓練開始的,這也就是所謂的戒行。
就拿那個禪坐來說吧!大部分我們所熟知的教學方法,一開始就直接去坐了,然後發現自己無法盤腿來坐,然後就放棄了。唸佛呢?一開始就參加法會,然後就唸唸,發現也得不到東西,就放棄了,持咒也是類似情況,那到底還有什麼法可以修呢?其實佛教的教授方式是需要講究教育原理的,佛門裡常說:方便善巧,就是這個。印度教在全世界推廣瑜珈,獲得了很大的成果,結果讓印度教給世界化了。到今天台灣各地都有瑜珈教室,教導這種瑜珈術,瑜珈就是從鍛練身體開始的。婆羅門宗教體系有六大支派,瑜珈是其中的一宗,另外還有小支派的學問:包含醫學,曆算,天文種種,這就構成了大小五明。這大小五明,不只是印度各宗教都學習,連佛教也是強調的,到現在藏傳佛教都還在教導,還在學習,這是世間法,有這樣的世間法基礎才好方便入門。還有佛經裡面的名詞,譬喻,很多都是引用這些印度世間法的文化來做基礎,不是引用中國的文化耶!這些東西,剛開始主譯的印度法師一定有講過,議場內的大德們或許也都知道了,但是代代相傳,原來是要傳譯梵文的中文,久而久之也變成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大多法師講經,很多都是望文生義,就不再去追究原來的義理,雖然中間有法顯,玄奘,義淨等人曾經想要挽回這個局勢。我想學梵文,巴利文,它的意義不是要我們放棄漢傳佛教,而是要把漢傳佛教過去所欠缺的,模糊的名相給具體化,建立教法次第,這就是我想要作的。不要再迷迷糊糊地去探討一些我們不懂的東西,也不要迷失在我們放不掉的迷思裡面,明明白白,踏踏實實地去走好每一步路。我相信佛法是科學,不是玄學,也不是有佛無法,有名無實的宗教。




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這裡有本書名為"巴坦加里的瑜珈經"(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大家如果看到這本書,不妨翻一翻,你會嚇一跳,"哇!這書不是佛教的書嗎?",是啊,你從第一章一直翻到最後一章,尤其是這本書從開始練瑜珈,一直到最後的解脫概念,你要是沒有印度宗教哲學的觀念,或是梵文基礎者,很可能你就認定這本書就是佛教書籍。
書裡面的描述很精采,特別是屬於禪修的次第非常精采,生動而吸引人。這本書分成四篇:三摩地篇,練習篇,成就篇,解脫篇。你看這些名詞,你也許會覺得這是一本密宗書,起碼和西藏佛教有關的書。
很不幸,這是"外道"的書籍。事實上,巴坦加里正是印度教裡面赫赫有名的瑜珈聖人。Yoga Sutra瑜珈經就是他的代表作,他是印度古代非常有名的婆羅門教徒,將印度瑜珈理論闡揚得非常好。
其實,我很喜歡這樣的書出版,因為這本書終於讓我明白了"梵我合一"是怎麼一回事情。這本還是台灣出版的,中國大陸最幾年來也出版不少有關介紹瑜珈的書籍,這讓我對於傳統印度瑜珈的修行方法有比較具體的概念。也幫助我厘清了佛陀當初不選擇去當婆羅門教聖人的關鍵處。佛陀當時確實有機會成為領導印度婆羅門教一代宗師的,佛陀以經成就到了非想非非想天,可以說六道以內再也沒有比佛陀有更高的境界與成就了,但是佛陀還是放棄了,離開了那些印度傳統的沙門僧團,離開了他的上師們,獨自來到菩提樹下,完成他的佛果修行。
這本書的翻譯者我想她不是故意的,因為她是從英文書翻譯過來,但是你看到書裡面用的很多都是類似佛教詞語,特別是輪迴,業果,四禪,尤其還是最後的"解脫"。
我請問:有人來問你這本書的知見是否正確?有人來告訴你:我看到一本佛教書籍了。你要怎麼回答呢?
確實不好回答。尤其對於漢傳佛教的弟子來說,我們普遍只能因為作者是不是佛教徒,而無法就裡面的義理去為大眾剖析。不過我注意到裡面一個關鍵,那就是在"解脫篇"裡頭有一個單字,我特別查了梵文辭典,才知道這個關鍵:
那就是被翻譯成"解脫"的那個字:Kaivalya。
印度傳統瑜珈的「解脫」是Kaivalya,而佛教是Vimoksa或是Vimukti,都是雙方修道的終極目標,但從這裡這就顯示出分別來。從梵文的解釋來看,Kaivalya是形容自己有無邊無際,脫離了一切束縛。這也正是瑜珈經對此字的定義與解釋,而Vimoksa則是完全解放身心,但沒有屬於「人」的那一份感受。換句話說,印度宗教的瑜珈,和佛法的禪修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印度的瑜珈還有「我」,而佛教卻是「無我」。當初佛陀看出傳統瑜珈,追求的目標雖然也是解脫,但因為執著在「我」,眷戀著自己的存在,只是把「我」給擴大到無邊無際,坐禪的目的只是要體驗這種輕靈的身心感受。不知道「心」才是人的主宰,一旦離開了禪定境界,還是得受業輪迴,這樣的修行有什麼意義呢?印度其他宗教就是不知道這一點,所以才要皈依梵天,才要修成「梵我合一」,托身於梵天。這就是佛陀當初為什麼要放棄傳統的瑜珈禪修的主要原因。
所以如果你不能從這種文字的定義上去了解,恐怕會造成理解上的誤會。
事實上過去我在學校社團時,社內一個學長常常為大家解說一本書:來自喜馬拉雅的大師,裡面就是講到了修行瑜珈的"上師",他以為那本書就是佛法書,很熱心為大家推薦這本書籍。其實,裡面的名詞,是台灣的翻譯者參考了佛法翻譯來作的,變成整本書看起來真的很像佛教的書籍。
所以也有人會推薦你閱讀New Age的書籍,介紹到國內來。但因為台灣過去只有佛法是從印度來的,所以就用了佛法去格印度宗教的義理,所以說的東西,和佛法看起來也差不了太遠。假如你不從源頭,梵文開始了解起的話,這對我們來講確實容易招致誤解的。




前面提到,佛教很多名詞是與印度宗教名詞大同小異,例如「佛陀」並不是佛教才有的名詞,在《Samavidhana Brahmana》就有這個字(請見William Monier”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p.733),而「涅槃」,有一本奧義書(Upanisad)的名稱就是用這個(見William Monier”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p.557),可見真的沒有什麼分別。其他的還有阿羅漢,這個字耆那教也是主張要修成阿羅漢。這個狀況,你可以從檢閱威廉,莫尼爾的梵英辭典,這本梵英辭典很特別,他是主張以字源學立場來編辭典,所以你很容易看見這個字在印度傳統裡面有哪些宗教,那些聖典用了它,包含佛教在內,你很容易看到這個字彙的歷史。所以由這裡,我就發現到,原來佛陀講經說法,是用印度已有的宗教觀念,來講佛法。楊松欲前面舉了般若與假名這個問題,正好可以用這個答案來回答。其實佛教大師們用詞很嚴謹,能夠用印度傳統名詞來講的,盡量用傳統名詞來講,這樣講大家都很容易懂。但是不能用印度傳統名詞來解釋的話,佛教就得要自創名詞了。般若,這個字就不是梵文,原因是般若的思維,傳統的印度文化沒有這樣的東西。菩薩,也不是梵文,因為菩薩在傳統印度裡面也沒有這個文化,這等於是佛教特出於當時印度宗教文化的東西。那你說這些是什麼文?答案是,它們來自民間,Prakrit,巴利文正是Prakrit的一支。佛經原來不是用梵文寫成,是從民間慢慢流出來的典籍,經過一些大師的宏揚,慢慢的因為弘法的需要,轉寫成梵文,但是這些特殊的地方性詞語,因為梵文裡面沒有,所以特別保留下來。我現在因為研究法華經的關係,發現到這樣的內容,法華經可說是相當原始的經典,頌偈裡頭有很多非梵文的辭彙,經過證實,頌偈的歷史比散文還要早。
可是你經過漢梵的翻譯,甚至於梵英的翻譯,看得出來這種分別嗎?看不出來的。通通變成了漢文,你怎麼樣也分不出誰比較早,誰比較晚的問題。所以鳩摩羅什很了不起,他很清楚這種關鍵性的問題,就把般若給音譯了,乾脆不翻譯。有些音譯的辭彙不是因為秘密或怎麼樣,而是它在原典裡面,也是音譯,不是梵文的關係。佛典在印度編輯的時候,就有可譯與不可譯的差別存在。現代學術研究也做到了這一點,根據阿育王石碑,可以分得出來這些梵本裡面屬於原始詞彙部分是屬於印度哪個區域的語言,大概可以知道這個概念可能來自印度的哪個區域。所以後來日本學者就提到法華經是屬於印度次大陸的各地文化活動總集這樣的想法。




就拿金剛經來說吧。曾經請教仁波切有關西藏地區金剛經教學問題,仁波切的回答是,對於金剛經,般若經這種經典來說,在西藏是次第很後面,需要做相當的前行,才能閱讀金剛經這樣的經典,否則你會看不懂。金剛經的前行是什麼呢?要從四加行開始,然後俱舍論,這可以奠定你對於佛教基本名詞,與基本教理的定義了解,明白後,繼續接著龍樹菩薩幾部大論,包含中觀論等多部在內,最後才是金剛經。有了前面的名相與教理的基礎,這樣對於金剛經,般若經等大乘經典就能夠有比較正確而清楚的理解。等於說,這是有次第,的系列訓練而成。
所以我過去常常看很多人探討緣起性空這個問題,這篇也不例外,裡面就是很多名相繞來繞去,我感到奇怪的地方是,怎麼一篇文章裡面沒有看到以名相為主的句子堆疊起來,看不出他有什麼屬於自己的見解。所以這樣我就知道,大概其他人也不會覺得奇怪,你看一眼大概沒有機分鐘就"轉台"了,就放棄了。這樣的探討,我常常懷疑,寫文章的人到底懂不懂這個東西。如果作者懂這個東西,我想從文字的描述上面一定會顯示得比較清晰,邏輯也會明顯,因為他要讓大家很清楚進入他的論述裡面,不會迷失,也不會讓你很快就想要轉台,丟開這個東西不看的。漢傳佛教的弟子們都很熟悉,你會喜歡看法師的開示錄,因為開示錄常常都比講經還要淺顯,對不對?所以過去大家都喜歡宣化上人的講經,慧律法師的講經,因為他們是真的懂,所以講得特別清楚。說真的,我是認為要寫這種文章,起碼要有那樣的表達能力,要像宣化上人,慧律法師那樣的表達能力才好。
其實佛法不是一開始就那麼複雜,是我們不照規矩來學習而已。
可別妄想頓悟,佛祖自己都不是頓悟來的,他自己還是透過傳統印度宗教,步步高升修出來的,最後終於在菩提樹下成就的。這每一步都有次第的。




如同楊松欲大德所說的:講真的!靜涵是一位很好的「佛學」學者,但不是真的『學佛者』。
佛法是用來體會的,真的不是用大腦的文字語言去思維的
佛陀的十大弟子周利槃陀,不也是依一句掃塵除垢來證得阿羅漢
從來沒有聽說過證得阿羅漢的人是必先去學習三藏精通才能證果的
佛陀說:無常’苦’空’無我
這是以一定的次第來說
先讓你體驗四大’五蘊無常
然後了解此無常性是苦’無常性故是空’無常性故是無我
佛教在最早是將〔無常〕當做是〔空義〕
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
將彼此能夠互相產生關連的緣起法則當成無常故名性空
並不是後期佛教是將〔無自性〕當成〔性空〕
可以看出佛教的佛法在佛陀入滅後有很大的轉變
但此轉變性是否能夠符合佛說則不得而知
以禪宗來說,禪宗是很重視體會佛法的精髓
若你去向一位學禪的人問什麼是緣起性空
他馬上給你一巴掌(此有),讓你感受到痛(故彼有)
說這就是緣起性空




"從來沒有聽說過證得阿羅漢的人是必先去學習三藏精通才能證果的"
這句話是錯誤的。因為五百大阿羅漢是因為集結三藏,我們才有藏經可以讀,否則大藏經從何而來?
學佛,如果不回歸經典,你要從哪裡學起?這就是我要講的,如果學佛能夠成功,我寧願從一個一個的格子重新爬起。但是,如果我不懂的東西,要強行說懂,也是害了自己。我承認我什麼都不懂,所以從一個名詞,一個名詞重新理解起。就算有需要路過外道,只要是必須要走的路,我也要走看看。
問一個問題:請問怎麼解釋"皈依"?我就從梵文來說皈依好了。
一般講到皈依,從梵文的namas講過來,其實屬於皈依儀式的皈依是Sarana。這個字的意思,從梵英辭典看來是這樣的:
1.protecting , guarding , defending RV. AV. ;(這是吠陀的意義)守護,保護的意思。
2. m. N. of a serpent-demon MBh. ; 佛典裡面一條蛇(也許是龍)的名字。
3.of a poet Gi1t.一位詩人的名字
4. of a king Buddh. 佛經裡面一位國王的名字。
5. f. N. of various plants 植物的名字 ;
6. n. shelter , place of shelter or refuge or rest , hut , house , habitation , abode , lair (of an animal) , home , asylum RV. ; refuge , protection , refuge with ; 一個避難所,一個避難之處。也是吠陀時代的意義。
7.water L. ;指水
從上面幾個意思來看,歷史最久的就是屬於第一個與第六個,這是吠陀時代的意義,由此看來,Sarana被翻譯成"皈依"這個字,原來就是守護,保護,也就是庇護所的意思。
在印度宗教裡面,皈依某個宗教,這大概都是尋常的概念,就是完全把自己生命,讓那個宗教來保護。印度有不少以宗教生活為主的社區,現在也是還有這樣的習慣,聚集一些人,都是以宗教生活為主。這種習俗來到中國,就成了所謂的修行團體。包含了僧團,教團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你投入了那個團體,跟著團體的規矩來走,這是印度的風俗。但是中國比較沒有這樣的風俗習慣,中國都是以家為單位,過著群居的生活。所以說現在台灣也有逐步在走學佛團體化的趨勢,這是符合原來印度學佛的風俗。
其實一般把南無,解釋成皈依,其實西藏的解釋比較正確,常常有法本上面說:敬禮上師三寶,這就是南無的意思,南無就是禮敬的意思。
這個也不是我講的,我發現南傳佛教也是這樣解釋,皈依,翻成英文就是take refuge to,就是將自己接受~的保護。




再來講講所謂的"經",嚴格講起來,梵文sutra,巴利文sutta,和中國所謂的"經"是有點不太一樣。中文的"經"是聖人垂訓,但多半是一大本書,就是所謂的"經書"。而印度的sutra,是指:
1.n. (accord. to g. %{ardhacA7di} also m. ; fr. %{siv} , `" to sew "' (縫補), and connected with %{sUci} and %{sUnA}) a thread(一絲一線) , yarn(紗線) , string(線,繩子) , line , cord(繩線,粗索) , wire(電線,電纜) AV. ; a measuring line(測量的線) (cf. %{-pAta}) Hariv. VarBr2S. &c. ; the sacred thread or cord worn by the first three classes (cf. %{yajJo7pavIta}) BhP. ; a girdle(帶子) ib. ; a fibre Ka1lid. ; a line , stroke MBh. VarBr2S. Gol. ; a sketch , plan Ra1jat. ; that which like a thread runs through or holds together everything , rule , direction BhP. ; a short sentence or aphoristic rule , and any work or manual consisting of strings of such rules hanging together like threads (these Su1tra works form manuals of teaching in ritual , philosophy , grammar &c.: e.g. in ritual there are first the S3rauta-su7tras , and among them the Kalpa-su7tras , founded directly on S3ruti q.v. ; they form a kind of rubric to Vedic ceremonial , giving concise rule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every kind of sacrifice [IW. 146 &c.] ; other kinds of S鎵3ruti works are the Gr2ihya-su1tras and Sa1maya1ca1rika or Dharma-su1tras i.e. `" rules for domestic ceremonies and conventional customs "' , sometimes called collectively Sma1rta-su1tras [as founded on %{smRti} or `" tradition "' see %{smArta}] ; these led to the later Dharmas3a1stras or `" law-books "' [IW. 145] ; in philosophy each system has its regular text-book of aphorisms written in Su1tras by its supposed founder [IW. 60 &c.] ; in Vya1karan2a or grammar there are the celebrated Su1tras of Pa1n2ini in eight books , which are the groundwork of a vast grammatical literature ; with Buddhists , Pa1s3upatas &c. the term Su1tra is applied to original text books as opp. to explanatory works ; with Jainas they form part of the Dr2isht2iva1da) IW. 162 &c. ; a kind of tree DivyA7v.
東西不少,總之,這意思就是我標示的那幾個中文字,大概就是"線,繩子",帶子是用來寫聖人的教訓,一條一條的教條,不一定是一本書。反而外國翻譯成teaching,這個字比較貼切一點。經常"經",都常常以頌偈的情況出現,梵本裡面常常彰顯一個現象,就是頌偈與散文是不同時代的東西。







底下是一個路人發表的幾點淺見:
1.我覺得樓上幾位師兄似乎沒有抓到靜涵師姐話中的真正用意。靜涵(至少就頭幾篇回應而言)並非針對文的內容或作者的立場而發,而是針對文章的表達方式與貼文者在動機上的心理格局層次而發的。靜涵懷疑就這樣一篇全篇僅僅是不斷地引經據典,加上翻譯,以及由一堆名詞所堆砌起來的文章,能夠讓讀者收益的效果有多好?老實說,該文在邏輯層次上的佈局結構也顯得相當地薄弱(只是層層堆砌,沒有什麼演繹)。我相當同意靜涵師姐提到宣化上人或慧律法師的開示為何淺顯易懂,因為只要繞著一個中心主旨,用種種的譬喻或方便讓讀者真正明瞭該旨意涵,這才是行文表達的上上之法。
2.我認為若有人想將名詞弄懂,就亂將此人扣上「著文字相」之帽,其實反而才是犯了四依法中的「不了義」及「依語」。舉凡想將名詞搞懂的這個「行為」就算是著文字相嗎?我們都知道佛弟子不可造說謊的口業,但佛陀也舉過「獵人覓兔」的例子來說明說不說謊還是要看場合的,如果修行者只會死死地守著「不說謊」這三個字,那就是沒有了「義」或依「義」,因為佛陀的意思是希望我們不要因為說謊而造下惡業。一篇文章寫出來當然是希望讀者能明瞭作者所要表達的涵意,故行文者有必要交代清楚一些我們不常見的名詞或是有多種不同涵意的名詞或是容易混淆的名詞在「此處」的脈絡之下所指為何。我們都知道「比中指」這個動作,在現代是指罵人的「三字經」的含意,但是單就比中指這個動作而言,它其實也是佛教中的一個手印啊!一樣東西在不同的場合或脈絡之下,是會具有不同的涵意的。如文中的「沙門」或「梵志」等在「該處」意指為何?二者有何區別?貼文者真的懂嗎?為何一直沒看到這方面的回應而顧左右言它呢?靜涵在此是相當一針見血的提醒,然作者或貼文者似乎沒注意到這個問題。如果因為這樣的提醒,就用對方是學者的帽子加諸對方,本人不覺得算是相當有風度的作法(「學者」一詞本身當然無貶抑之義,不過,同樣地,通常在這種宗教論壇的「脈絡」之下,常被用來指只將佛學當成學問而不實際修行的學究)。
3.本人是覺得,若要轉貼一篇文章,最好是自己真的讀過,而且讀懂了,再貼,這樣是比較負責任的,否則萬一原作者的觀點是偏差的,雖然貼者不是元兇,也間接成了共犯,可是有損陰德的。而若要引用一整段經典,建議能在引用後再加上一些自己的看法吧以明己見,只用顏色標起來,似乎是有點偷懶啦。我對靜涵的理解若有錯誤,請靜涵指正。但我是覺得,如果連靜涵寫的白話文都抓不出重點及主旨的話,我們似乎有合理的理由能夠懷疑:貼文者或引用者真的有能力讀懂這些文章或經典嗎?如果連只是成為「讀者」都有問題的話……當然這只是懷疑而已。
4.我個人是覺得《緣起》該文已經有點玩弄文字遊戲的味道了啦,有點好奇真正耐著性子把每個字看完的看倌有幾何?有關「緣起性空」的概念的清楚表達,「般若文海」中也有許多佳文論及。也許在立場上,不見得會每個人相同,但至少,我覺得在行文的結構或邏輯的表達方式而言,可以學學!
(本文幾點是根據20層樓以前所作回應,要貼文時才發現靜涵又貼了兩篇,但我還沒看。)







先匆匆謝謝路人的意見。
其實,我剛剛舉出印度對"經"的解釋是這個樣子。因為經都是這樣一條一條的聖訓性質,但是你怎麼去理解,去學習,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經有很多,可以說佛祖只要在世,他老人家隨便一句話都會變成"經"。但是因為我們對於聽到的人,或者場景,背景都不了解,所以就必須要有"論"的存在。這其實和婆羅門教的背景是一樣的。就婆羅門教來講,四個吠陀,梵書都是這種"經",但是也同時存在了許多的奧義書,這些奧義書其實都是解釋吠陀典籍的。
那特別是佛陀這種從來不想寫書的聖者來講,他都是隨口開示解決信眾的問題,舉行法會,也是隨緣開示。但是你怎麼能夠成為佛陀那樣的聖者,這就要靠你努力。所以當佛弟子們要教導僧團的後輩弟子,就會從基本的名詞解釋開始說起。阿毗達摩,就是這樣的作品。基本名相,也代表基本教義,有了這樣的基礎,再來就是要學習思惟邏輯,學習佛陀的思考方法,學習成佛的理論,起碼了解你所要修的這個儀軌,原理是什麼,你準備做到什麼程度,過程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後才開始修行,這就是顯教的教學。講經,有講經的法師,講論有講論的法師,講戒有講戒的老師,所以經,律,論三樣東西都精通,就是三藏法師。現在很少這種三藏法師了。我講緬甸,雖然人家還是專制的軍政府,可是對於佛教還有很深的護持。緬甸政府曾經也是獎勵僧伽背誦三藏經典,結果出了好幾位能夠被誦所有經律論的大師,稱為"闇持者"。所以要修阿羅漢,背經典是起碼的修行,怎麼會不學呢!
再說到禪宗,你想禪宗修行是可以不管經典的嗎?沒有啊,百丈清規明明規定禪宗必須讀誦的幾部經典,這才有禪門日課誦本的出現,是否?
我個人覺得佛學,是在太重要了!佛學不明,偶爾可能出現幾個學佛的天才,可是對於佛法要長遠流傳,不是辦法。




我們作學問,不是反對祖師,也不是說漢傳佛教所有的翻譯都是錯誤的,剛好相反,我們是因此更加肯定祖師,也更加清楚當年佛陀講經的真實義。
我前面曾經講過,佛陀(buddha)是我們漢地對他的簡稱。在法華經裡面,要講出像釋迦牟尼佛那樣偉大的佛陀,確實有種不一樣的稱號。我之前不是講過,Buddha這個字不是佛陀發明的,在梵書裡面就有這個名詞。阿含經也是說阿羅漢,然後成"佛",是不是?但這樣一來,就會和釋迦牟尼佛的"佛"是不是相混了?法華經講到某尊如來,如日月燈明如來(初品),就是用"多陀伽多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來尊稱,講到日月燈明如來,就總是用這個稱號: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我翻譯的,原文是:tathagata arhat samyaksambuddha),這是用來區別這尊佛是大乘佛教的佛果成就者,特別的殊勝。其實鳩摩羅什都有翻譯出來,只是我們都習慣說佛陀,佛陀的,以為釋迦牟尼佛就是"佛陀"而已。其實,大乘佛教的佛果,是有包含了阿羅漢在裡面,但是他的成就又是超過了阿羅漢,阿羅漢的成就只是他的功德之一而已。三個稱號,我想應該也包含了菩薩的成就,然後就是正等正覺成就的自在者。
再說"自在"這個名詞,梵文是Isvara:
mfn. able to do , capable of (with gen. of Vedic inf. , or with common inf.) , liable , exposed to AV. TS. S3Br. AitBr. Kum. Hit. &c. ; (%{as} , %{I}) mf. master , lord , prince , king , mistress , queen AV. S3Br. Ragh. Mn. &c. ; m. a husband MBh. ; God ; the Supreme Being Mn. Sus3r. Ya1jn5. &c. ; the supreme soul (%{Atman}) ; S3iva ; one of the Rudras ; the god of love ; N. of a prince ; the number `" eleven "' ; (%{A} or %{I}) f. N. of Durga1 ; of Lakshmi1 ; of any other of the S3aktis or female energies of the deities ; N. of several plants L.
大底上是講有能力,是可以依靠的,大師,當主子的那種。簡單講,也就是可以皈依的,可以受託保護的那種眾生。事實上這種Isvara並不是屬於他人,也不是他人所創造,不受他人約束與宰制的,這和我們現在講的自由自在的那種自在意思有點不同。但是你可以自由自在不受束縛,是因為你是自由人,本來就沒有人約束你,沒有人束縛你,所以你可以自在。但是把自在,解釋成自由,不受束縛,不是不對,只是已經受到中文的本土化解釋,望文生義,脫離了印度大師當初想要表達的那種涵義:"自己本來就存在"的那種"自在"了。
我本來要傳達的是,現代我們要傳佛法,不是再向中國來傳,事實上是世界性的弘法。現在全世界的人學佛,不會再以中國佛法為大乘唯一的法源,英美國家的人學佛,主要法源就是從西藏過來,西藏佛教比日本佛教還有力量,因為有很多修行人,但是他們因為也保存了梵本,大家可能知道,西藏現在可靠統計數字是,大約存有五百部的梵本。中國政府最近正努力發掘,要開始出版,並且保存。這些梵本,其實也是西藏佛教的底子。仁波切也是藏傳佛教另外的底子。我從仁波切那裡知道,不論是拉薩,還是康區,都有佛學院傳授梵文,而且他們也很重視梵本教學,也還有人還在抄寫梵本。
再加上歐美國家其實翻譯的佛經語言,都是那些來亞洲考古的專家,他們本身都有梵文底子,所以現在一些大乘佛教典籍,如法華,般若等英文版,尤其法華經已經有很多國家語言版本,連斯里蘭卡都有翻譯本。但這麼多的翻譯本,主要都還是從梵文本翻譯過來。而中國佛教雖然保存許多漢文佛典,可是大多只能當作是參考資料。只有當梵文本缺少的時候,才會從漢文本翻譯過來。
我覺得,如果要重新振興中國佛教,只有把梵本的傳統接續起來,我倒是比較贊成,我們讀中文佛經,用中文宣講中文版佛經,但是誦持梵文原典,或是巴利原典。套用德瓦難陀法師講的一句話:佛陀不會妄語,念他說過的話最準。事實上,有了梵本,更好的作法就是,你可以白話文翻譯,可以更精確一些。日本人現在就是這樣作的,從梵文翻譯過來作日文版佛經。當然他們傳統宗派還是唸誦漢譯本佛典。




再講一個現在這個時代可以看得見的:
各位都知道印度這個國家,India,可是呢,印度,這個名詞是全世界這樣稱呼它的,但是印度人不自己稱作印度的,而是稱自己是"Bharat",(the Republic of India (properly, Bhārata Gaṇarājya, भारत गणराज्य )所以這個,也是要深究一下才知道的。印度這個國家有三個名稱: 分別是 India, Bharat 與 Hindustan。即印度,婆羅多,與印度斯坦。婆羅多這個名詞和印度最有名的史詩,摩訶婆羅多是有密切關係的。
接著我嘗試打一個梵文字:थागतोऽर्हन् सम्यक्संबुद्ध tathāgato'rhan samyaksaṁbuddha這個就是我前面所說的,那個多他伽多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這個單字。




這個系統好像很不錯,以後我可以再講一些梵文的東西,給大家做參考。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這個題目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括弧裡面那個(修正一些佛學的錯誤觀念),我個人沒有意思要修正什麼,沒有那麼了不起,但只就自己最近一些學習心得提出來看法。我覺得,佛學很重要,尤其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裡,我們更需要佛學。你討論版能說的,就是佛學。佛學充分理解完成,就是要去學佛了,這裡要談學佛,可能就是法訊吧。我對學佛資訊的理解是這樣的。你總是有了行動才會說,你去"學"佛,對不對?
總不會說,只有祖師大德開示才叫做學佛,剛好相反,為什麼?因為現在學者研究佛教,不都是拿這些開示來當材料研究嗎?經典也是研究材料啊!當然研究佛學的人自古以來就不一定是學佛者,過去美國,乃至歐洲甚至於很強調這一點,研究者不能是宗教信仰者,這會與自己研究成果的客觀度發生衝突。但是當一個文化,甚至昇華成全人類的共同資產,是人類值得共享,並且值得保存的東西時,研究者也許就有必要跳入實踐的領域當中。
不過正在進行實踐的人,事實上面對實踐以外的人士,我想只有給予接引與誘導的權利。我們對於這些願意參加研究佛法的人給予關懷。總不好給外界有一種感覺:"實踐是高貴的,研究是次等的"這種感受。當然,實踐佛法確實是比較好一點,這是我一個私人的感受,可以適度表達。但是對於廣大尚未認同的人來講,他們需要的是更多的解說,好讓他們能夠早日認同,早日進入佛法這個大花園裡面。所以我花了很多力氣來學梵文,甚至要把佛法從頭學起,一方面是要求真求實,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中國佛教能夠承接梵本,原始大乘佛教的傳承。這是我希望為我們的佛教作的一點小小的貢獻。
希望我們的佛教不要再讓靈異傳奇或是玄之又玄,來纏繞著我們。







有關"契經",宣化老法師講的根據,這裡已經找到了,在佛光大辭典有引用大毗婆娑論裡面就是這兩句話,所謂:上契諸佛的理,下契眾生的機。是這樣來的。
但是這個問題是這樣:契經的"契"字,有很多意思,最早是指刻在龜殼上面的甲骨文,也是指那個刻甲骨文的鑿子。我想翻譯成"契經"的情況,有可能是因為修多羅本來就是條列式的東西,一條,一條的,這上面可以是一份Menu,菜單,也可以是聖人講的話,總之就是條列式的東西,就是"經"。不知道怎麼樣,中國對於"經"是很崇拜,有崇拜的意味。但是印度不一定,菜單也可能是sutra,後來確實也是針對聖人講的東西,引申成了sutra。變成sutra就是指原典的意思。
但是這裡我就是講,什麼是觸動了望文生義的盲點?意思就是,我們過去古人講經,常常引經據典,可是引的內容全是中國文化。就sutra來看,原來就是文體,稱為sutra。不一定就是"聖經"的意思。契,這個字原先是指的是那個文字記號,或者是指"竹簡"那種一片一片的。一條一條的,那就是修多羅的意思了。但是,同樣都是"契","契合"的"契"是指合約書,那你把這個文書的記號,說成了是合約書去了,然後把它講得"變了樣子",看起來也是佛法沒錯,可是已偏離主題了。這就是我講的"觸動了望文生義的盲點",經你這樣一講,把所有的中文"契"字全部連了上來,梵文的修多羅就有了中文"契約"的意思了,事實上到今天,印度的修多羅還是沒有這個意思。這就是望文生義可能發生的訛誤。
再說,為何我說"契合"是偏離主題的詮釋?照這樣解釋,所有的經書都是用來上契佛理,下契眾生。契合佛理可以說得通,但是下契眾生,這就說不通,因為不用說信仰了,就連看得懂都有些困難,哪裡能說得上是"契合"呢?經書是因應當時的眾生而說,可不見得迎合後代眾生而說的。至少你要看得懂佛經,還是需要一些前行的基礎才可以的。
所以我也希望有機會讓我閱讀一下大毗婆娑論的梵文原典,讓我看看原文是怎麼樣寫的。我是有點不太相信這樣的翻譯方式,用上~下~這種句型是十足的中文,好像"法師上下",這是只有中國佛教才有的風俗,國外,如印度就沒有那個上下的。所以你問外國法師法名就不能說:What is your name's up and down?那會鬧笑話的,他們沒有這樣的規矩。
但不知道原文是怎麼樣,怎麼被翻譯成這樣的,我很好奇,希望能夠看得到。
道安大師過去提倡要去除格義,意思就是不要用道教,或是道家的意思來理解佛經,推而廣之,也是不要用佛法以外的東西來理解佛法。當然我們生在中國文化的圈子裡,免不了一定是要用本土的文化來了解外國文化,這是難免的,也是必經的路程。只是呢?因為我們沒有閱讀原典的習慣,導致有些翻譯,本來是藉著本國文化的方便來說明原本的意思,但是日子久了,加上文化的發展也有劇烈變化,例如咒語音的變化,這是眾人都知道的事情,那你想,經文的意思會不會也有這個問題?所以在唐朝曾經很流行的梵文佛學名詞的字典,什麼一切經音義,翻梵語等等在大正藏第五十四冊裡都看得到。唐朝時代,對於佛法名相是非常注意的,佛門對於"音"與"義"也非常注重,可是到現在幾乎都不流行了。




隋唐時代的佛教,往往對象是講給社會菁英份子聽的,所以註疏都很用心,也有很多工具書出爐,到今天我們研究佛學都還是用他們寫的東西。可是隋唐的文化,畢竟和今天已經有很大不同。
我的想法是這樣,一方面還是不斷閱讀原典,一方面查單字,另外一方面同時來閱讀那些過去的佛學辭典,像是翻譯名義大集,這是一本西藏做的,專門為了藏文與梵文對譯所用的工具書,所以非常有權威性,後來該書流到俄國,然後日本人發現這本書,就抄回來,加上了中文與日文。變成四體合為一書的東西。其實,我們可以從這裡看見一些東西。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梵文的辭典,我推薦最好要用梵英辭典,暫時不要用梵漢辭典,或者梵英為首,梵漢為副,這樣來研究比較容易看見梵文原典的原來風貌。為什麼我強調最好要用梵英辭典呢?因為梵英辭典收納的不是佛教的意思,是婆羅門教與印度教所使用的意思。這樣就看出佛教當初為什麼要用這個字來書寫在經書裡面,這就看出了印度人如何把佛法介紹給印度人的想法來。原產地的人是這樣來詮釋佛法,很容易我們就看見我們自己所承接的傳承,裡面是否有發生偏離的問題來。
這是一個訓詁的工作,不是推翻舊譯,而是在舊譯上面加上新的注解,新舊都保留,該肯定的就要肯定,不幸發生錯誤了,就該更正。而且,你會產生一份更好的,更精確的白話文翻譯,就不必再去爭執什麼文言文,還是白話文的問題了。
不是反對祖師,也不是不相信祖師,而是針對我們中國文化年代太過久遠了,將近一千年那種不立文字的傳統,讓大家看輕了知識與文化。佛法不是給文盲信仰的,知識分子也需要佛法,中產階級也需要佛法,大家都需要佛法。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才這樣主張的。




學習任何事物都是需要次第的,不是只有學佛而已。
我有個朋友是基督書院英國文學系畢業的,但是他的英文實在是讓我有點......不曉得怎麼說(有點不曉得他是怎麼畢業的)。舉例來說,助動詞後面還會接had,或者將完成式後面的過去分詞放成過去式動詞。所以每次跟他msn都超痛苦的,我糾正他,他就會告訴我那些大文豪寫起英文都是不照文法來的,要我不要拘泥在文法上。問題是這不可混為一談啊!! English writing要到達那種境界,好歹也要經過一些最基礎的階段,才能到達以書寫藝術超越文法的境界,尤其對我們這些英語非母語的人來說更是如此。並不是只要犯了錯,就通通把它歸為「我不執著在文法的相」上了,這才叫「著了『不執著文法』的相」。
我們都知道禪宗有不立文字的傳統,但不立文字有它的用意在,目的是想避免掉使用文字會產生的缺點。但並不代表只要不立文字就「等於」在修禪了。「有」或「沒有」文字一樣都是一種「相」,我們唯有去瞭解這些宗派的祖師們「何以」要如此行,實知其背後的用意與苦心,才能真實地行出這種方式所欲帶來的效果,否則就會像我那位朋友一樣,令人哭笑不得。
「佛學」本身是中性的,本身沒有好或不好,那些都是後人所賦予的意義。個人認為學佛要學好,佛學的基礎當然相當重要。若什麼都不懂要怎麼修?盲修瞎練一通,入了魔道都不曉得呢!正確地利用佛學的資源,將會在我們成佛的過程中對我們有莫大的助益。我們看從古代天台宗的智者大師一直到最近的宣化上人、印光祖師、淨空法師等等非常有成就的修行者,哪一位不是佛學大師呢?相反地,若只是當成學問來研究而不實際修行,那就未免太虛擲光陰了。因此這就是佛學的「空性」,萬法皆空,其實不只「佛學」,萬事萬物皆是如此。「佛學」能帶給人什麼,並非取決於它本身,它本身也沒有好壞,關鍵是在於使用者的根器如何。
提到禪宗,我們常會講到「當下頓悟」或者「即身成佛」,但我覺得這並不會違背次第的概念。六祖慧能能在不識半字的狀況下,聽到金剛經的偈語就開悟,各位會覺得這是偶然嗎?甚至世尊在29歲出家,僅經過六年的時間就證悟成佛,這會是偶然嗎?如果有任何人有這種想法,我覺得只是看到事情的表面。君不見這些我們所見識到的覺者,不知經過了多少累劫累世的修行,而終於在今世因緣俱足的狀況下,才得以「頓悟」,才得以「成佛」。
附帶一提,佛教中有很多的普傳咒語或修法,但也有不少的法門或咒子是強調除非有上師的傳承。這些密法,就算自己在網上或是透過其他途徑取得了法本、儀軌也不得自行修之,我想原因也是跟次第有關的。它的嚴重性不是只是「盜法」而已。如果自己的狀態尚未到達一個合適的階段,不自知而貿然試法,跟落入魔道的風險比較起來,「盜法」恐怕只是九牛一毛吧。諸佛菩薩都已證果了,難道他們會在乎你去偷這個法來學?我想這是他們為了我們的好處,這是諸佛菩薩的慈悲與苦心。近來爭議頗多的「雙運法」也是個很好的例子,看倌可以多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