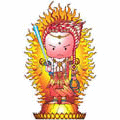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我的祖父、我的上師》——雪謙•冉江仁波切憶念頂果•欽哲仁波切
摘自《明月——頂果欽哲法王自傳與訪談錄》
第一部分
雪謙·冉江的母親是頂果·欽哲法王的女兒企美·旺嫫(出生於仲噶)。項果·欽哲法王在他年幼時便極為鍾愛這個孫子,並親自督導他的教養與精神修為。雪謙·冉江是尼泊爾波達納斯暨康區的雪謙·滇尼·達吉林的住持。
有一次當頂果·欽哲仁波切在前藏朝聖時,他的隊伍在一處地方紮營。夜深人靜時分,突然有名女子進到帳棚裡,從衣服裡取出一支天鐵金剛橛,說道:“這應該是你的——我找到的。”說完就走了。康卓(仁波切的法侶)試著追她,想給她一些茶,但根本毫無踪影,她應該是位女護法神。
在朝聖後欽哲仁波切就沒再回過家了。反而在噶瑪巴離開後不久,就從西藏到了不丹;當時他四十九歲。在他到了不丹後,就從收音機裡聽到欽哲·確吉·羅卓在錫金圓寂的消息。在他前往錫金的路上,大部分的家當都在西里古里搞丟了。在錫金時,他主持了欽哲·確吉·羅卓的荼毘大典,並建造了舍利塔。他在卡林邦和錫金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並在隆德寺,從噶瑪巴處接受了《噶舉密咒藏》和《教訣藏》。
欽哲仁波切和十六世噶瑪巴很親近,他們不只是精神上的師徒,也是朋友。他們倆都來自丹柯。他們會花上好幾小時,談論上師的生平、教史等等。有時他們會從早上一直聊到傍晚。他們很喜歡彼此作伴;噶瑪巴嘲弄仁波切,仁波切則報以一堆笑話。有時傍晚欽哲仁波切才剛回到他的房間,噶瑪巴就來找他繼續聊。有一天晚上他們談到了鬼:我還很小、怕得不得了。我是睡在仁波切的身旁,當我約八、九歲大的某一天醒過來時,噶瑪巴已經在欽哲仁波切的房間裡談天了。因為我還睡在床上,就不敢起來,只得假裝還躺在那裡睡覺。
在我還沒出生前的一次談話中,欽哲仁波切問噶瑪巴說:“你覺得我的上師雪謙·康楚、雪謙·冉江和雪謙·嘉察仁波切怎樣了? ”噶瑪巴說他們很可能都死了。所以欽哲仁波切要求說:“你已經認證了那麼多的轉世,請告訴我他們投生在哪裡。”噶瑪巴告訴他說:“你不需要去找他們,他們正在找你呢。”
在說完這番話後一段時間,欽哲仁波切徒步去尼泊爾的南無·布達朝聖,這是釋迦牟尼佛前世捨身餵飢餓母虎和小虎的地方,距離加德滿都約一天的腳程。那天,仁波切覺得非常開心,因為據說這是佛陀初次生起最珍貴菩提心的地方,菩提心是為了他人而證悟成佛並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達成此目標的利他之心,但他也覺得悲傷,因為這麼偉大的菩薩捨棄了他的性命。
當晚他回到加德滿都,在波達納斯佛塔附近,做了一個夢,夢見他正在爬一座高山,山頂是一座小寺院。他進了寺院,見到裡頭,一個挨一個坐著的,是他已故的上師、雪謙寺的三位主要喇嘛——雪謙·嘉察、雪謙·冉江和雪謙·康楚,他們全都在六十年代初期卒於監獄中。欽哲仁波切在他們面前向他們行大禮拜,並唱著哀傷的詩偈,詢問他們如何遭受荼毒。他們也以詩偈異口同聲地答道:“吾等生死如夢幻,勝義境知無增減。”欽哲仁波切表示想要很快在淨土和他們相會的願望,因為他覺得繼續留在世間並沒有多大的意義,法教迅速式微且大多數的上師不過是唬人的騙子。這時,雪謙·康楚目光凌厲地盯著欽哲仁波切,說道:“你得辛勞地利益眾生與維續法教,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為止。我們三個會合而為一,到你的身邊成為一個轉世,幫助你完成你的目標。”最後他們全都融為一體,融入了欽哲仁波切。
當仁波切醒來後,他將這些詩偈寫下,暗示他們三個人將會投生在他家中。後來他告訴了噶瑪巴這個夢,並給他這些詩歌。噶瑪巴說這個轉世就是他女兒企美·旺嫫的兒子,他就是雪謙寺三位喇嘛合一的轉世。已故的涅瓊·秋林仁波切、烏金·托傑的父親,當時也在場,說既然三位祖古合而為一,他便建議以三位當中最高階的那位來替我命名,就是雪謙寺的主要住持雪謙·冉江。欽哲仁波切覺得他寧可用雪謙·嘉察的名諱。因為嘉察仁波切是他最親近的根本上師,而且他自己也曾被認證為雪謙·冉江,欽哲仁波切真的很想要把我叫做雪謙·嘉察。
當烏金·托傑告訴我這個故事時,我不太相信;但在欽哲仁波切圓寂後,當翻閱他的所有文獻時,我發現了在一方錦緞中他親自手寫的紙張,記載著關於他三位上師的這個夢,所以我就相信了。
當我在1967年出生在昌第加時,我母親,他是欽哲仁波切的長女,正在一座難民營中當護士。在那些日子裡,因為西藏難民的極端困境,很多藏民小孩都被捨棄、送給西方家庭領養。欽哲仁波切當時正在不丹,一接到我已出生的書信時,就捎訊給我母親,要她不可將我送出讓人領養。
不久後,仁波切就到昌第加看我,帶著他的侍者阮竹;我還只是個小嬰孩,大聲哭鬧著,甚至還撒尿在阮竹的膝上。從那時候起,欽哲仁波切就把我帶在身邊,並以無法蠡測的仁慈養育我長大。
後來我在朋措林和我祖母康卓·拉嫫生活了一段時間。當我還呀呀學語時,她就讓我跟著她念文殊咒的每個字母,複誦了十萬遍的文殊咒。有一天阮竹被派來接我,祖母說我們那天正要吃蒸水餃,通常我都會跟祖母共吃一盤,但那天我堅持要用自己的盤子吃,即便事實上我還是把我的盤子擺在一旁,吃光了我祖母的那盤。祖母問我為什麼不吃自己的那一盤,我解釋說有一位很重要的客人會來,我要留那一盤給他。果不其然,阮竹在午餐過後就到了,所以我就給他那盤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