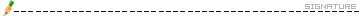戚繼光是明朝中最有才能的將領之一,他順遂的仕途有賴張居正的相助,他的晚景淒涼也和張居正脫不了關係,成敗皆是同一人,但張居正生前死後身分不一樣了,前者還是精明幹練的內閣首輔,後者已成為一個表裡不一的權臣。除了張居正,戚繼光的落寞還來自明朝的矛盾制度,明朝文官對於武官的輕視幾乎已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1],他們一則輕視武將無墨一則又懼怕武將造反,便想盡各種方法壓抑武將,於是在總督、巡撫以下設有「兵備使」、「海防道」,雖名為監察,然實握調度大權,人事任免、交通各項亦皆由文官所把持[2]。可若真要論起來,或許戚繼光已是幸運的,曾與他一同並肩剿倭的俞大猷宦路起伏與其比較就顯得更加顛簸[3]。但是隨著張居正的殞落,戚繼光的不朽似乎也已在那時畫下句號。
戚繼光留下了兩部名垂後世的兵書和數不盡的勝戰但他晚年卻不能得志,究竟他是劇變的犧牲者,或者他的形象只是後世史書塑造出來的假象,在剛直堅勇之外的戚繼光,他的操守被人質疑,他的迷信為人詬病,導致他晚景淒涼的原因必與他的思想與作為有密切之關係。
戚繼光的落寞
萬曆十年(1568),張居正結束了五十七歲的人生,但一場政治風暴才要開始。群臣對張居正的反撲也是其來有自,使作為一個權相,適要做到公正不阿、言行如一的無瑕才尚可得免朝臣指謫,而張居正顯然未達這個高懸的標準,攻擊的焦點莫不集中在他的德性上,當然這些非難的根源也是來自他的專權與跋扈。陝西道御史楊四知直言張居正私底下貪婪奢華,在官場上安插自己的親信與結交朋黨,他的「奪情」是不孝的忘親行為,其他還有欺君蔽主的罪行,林林總總共十四條[4]。幼時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忌憚,隨著年紀的增長,此時竟也化成了厭惡[5],更遑論那些因故被張居正給調走的官員,一些倚靠張居正提拔升任的官員與反對派在朝中展開了拉鋸[6],但擁護派始終居於劣勢,清算行動在江西道御史李植彈劾馮保時達到高潮,萬曆皇帝下詔列數馮保十二罪狀,直指馮保苟同張居正欺瞞聖上、禍害國家,本應誅殺,但念其為先皇所託,才從寬將他遷謫南京[7]。
當中國南方倭寇不再猖獗時,戚繼光被調往北方練兵、修築城牆,他的計畫因張居正的支持皆得以順利。例如他與譚綸初築禦敵臺時,朝中謠言紛傳,說這會使軍隊勞累,且砍伐樹木有損國土邊界[8],幸好張居正適時的幫忙才使得此計畫能夠繼續,到了隆慶五年(1570)秋天,禦敵臺修成,堅固雄偉,在二千里的邊塞上連綿,穆宗對此感到非常滿意,賜予戚繼光許多銀幣和世代蔭庇的特權[9]。
張居正逝世時,戚繼光的心情想必是十分難過的,但此刻政局丕變,他並沒有在文集中留下哀悼摯友的詩文。果真過不了多久京師內就蜚語遍佈,據稱散佈者竟是他一手提攜的陳文治[10],給事中張鼎思藉口戚繼光的戰功多在南方,北方反而無所發展[11],於是上疏將戚繼光請調南方。萬曆十一年(1583)二月,朝廷將他南調廣東,這項決議使戚繼光很不能諒解,他心情抑鬱寡歡,上奏求退但卻未准,最終在萬曆十二年(1584)還是給事中張希皋彈劾了[12]。
戚繼光要南下時,薊州的鄉親感到非常不捨,紛紛請奏留下戚繼光,但當局仍不為所動。當要走了那天,市集歇業,百姓們都擁到了街上,流著淚為戚繼光送行,更有人不捨依依地送到了境外才返鄉[13]。還記得隆慶二年(1568)戚繼光請奏招募南方兵自成一軍[14],南方浙江士兵三千人到了以後在郊外列陣,適逢大雨滂沱,浙江兵竟然還能夠從清晨至黃昏筆直站立不動,讓原本戍守邊軍大為驚駭,從此才知道軍令的嚴肅[15]。但曾幾何時,保衛社稷的干城竟變成了國家的威脅?
五十六歲的戚繼光,經歷過太多大小的戰役,為國為民不遺餘力,現在的他長相依舊挺拔[16],不同的是歲月在他的兩鬢上沾上白霜。南下的路途中,他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鄉,放舟於蓬萊閣下,「日月不知雙鬢改,乾坤尚許此身留。從今復起鄉關夢,一片雲飛天際頭[17]。」回想自己的功業,他還想要有一番作為。戚繼光並未在家鄉久留,七月就啟程南赴廣東,過了長江到達江西與廣東的邊際梅嶺時,他又想起了從前的塞外種種,寫下:「北去南來已白頭,逢人莫話舊時愁。空餘庾嶺關前月,猶照漁陽塞外秋[18]。」到了廣東,戚繼光有志難伸,他將他的不滿寫在〈引退疏〉裡面[19],可是朝廷並未准許他的辭退請求,過了一年他又因病在上奏求退,此時朝中對張居正清算未艾,張居正的家產方被查抄[20],給事中張希皋便罷去了戚繼光的官職。
自從戚繼光遭革之後,他的名字在朝中已有意無意的被群臣所淡忘,在他死前監察御史傅光宅曾向神宗提出重新起用戚繼光的建議,結果遭到皇帝奪俸二個月的處份[21]。隨著戰友俞大猷、譚綸;部將陳大成、王如龍相繼死去,其他的親信也被南調[22],除了還與幾個文人來往外,戚繼光生前廣為人知的親友已所剩無幾,就連他的元配王氏最終也與他反目,將他僅剩的財產帶回娘家,使得戚繼光醫藥不備,病況每下愈況[23]。
戚繼光還有幾個文人朋友的原因來自他的文學涵養,這也是他比起其他武官更具優勢的地方。他卓異於眾,幼時就喜愛讀書,對於經史大義皆能通曉無礙[24]。因他非無謀的莽夫,所以在明朝文武相輕的風氣下[25],隨著官階越來越高,文官竟也樂於將之視為同類,當作能夠倚賴與交際的對象,時而飲酒賦詩、往來酬對。在戚繼光返鄉後,當代的文豪王世貞還與他保有來往,不但在他生日時為他寫壽文,還為他的書作序[26],就連曾任福建巡撫的汪道昆在他死後也為他撰寫墓誌銘。
晚年還有這幾位文人朋友,戚繼光應已感到滿足了。看著家鄉蓬萊的喬松峨然,他不免有些感慨。「松若有心情,能忘利與名。人非松,松非人,古來那具千年身,龍爭與虎鬪,轉盼即成陳。松兮人兮奈爾何,搖筆且放奇松歌[27]。」盛年激昂的壯志現已被流逝的韶華磨的平潤[28],今生活到六十歲,對於國事、軍事如今早已看淡。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夜半[29],戚繼光的病又犯了,不同的是這次發病比平常還劇烈,他曉得這一天遲早要來的,只是他也許從未想到自己晚景竟會如此淒涼。戚繼光平步青雲的仕途仗著首輔張居正的大力提拔,而張居正早在萬曆十年時已經先逝,如今他也要駕返遊九泉與他的老友相會了。時間方過五更,家裡的人眼看戚繼光大去在即,囑他交託後事,可他已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了[30]。此時屋外傳來幾聲雞蹄[31],就在這天色將明之際,戚繼光呼出了最後一口氣,就此與世長辭。回首他一生的功業,也有毀,也有譽;抗倭戍防有幾分自豪,也有幾分未了的遺憾,然而這一切都隨著戚繼光的作古畫下了休止。
附論
戚繼光的文學涵養,確實為其所勝於其他武將之處,雖然《明史》列傳只提到《紀效新書》和《練兵紀實》,刻意忽略了其詩文集《止止堂集》,顯然是因他的作品在恢宏文海中尚且不夠格,他自知文學素養尚不高明,將篇名命名為〈愚愚稿〉[32]謙抑自處,能夠如此謙沖以自牧,足以見其涵養,不過戚繼光已稱得上是武將中的一朵奇葩。明朝開國以降文武相輕,試想戚繼光若為吳下阿蒙,豈能有文官對他倚賴信任[33]?
對於戚繼光迷信鬼神這一點,無疑是後人評價他感到最難以為情的部分,從《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題要》記載:「繼光有平倭功,當時推為良將,詩亦伉健,近燕趙之音。而雜說中乃多及陰騭、果報、鬼怪之事,不免偏頗[34]。」可見一斑,但這所反映的是與文人或武夫溝通上根本的差別,試想若以戚繼光的文學修養,又怎會陷入對神仙鬼怪的盲目信仰之中?故予一合理解釋,即戚繼光的迷信是作戰時的一種手段,或以神蹟激勵士氣,或以鬼怪給予警惕罷了!此法早有前例,如北宋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傳聞其神甚靈,狄青遂取百錢與神約:「如果戰事能夠大捷,則我所擲的錢幣字面皆會朝上。」擲後百錢果真字面皆朝上,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其實此錢係為兩字錢[35]。這種激勵手段後來為兵法中之一環,清高宗敕撰之《續通典》中特有一篇〈假託安眾〉詳述此法。戚繼光本諳習兵書,〈愚愚稿〉中有多篇兵書摘題[36],孫子嘗言:「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37]。」帶兵尤重士氣,戚繼光不可能不知,況且他對付倭寇時還曾言:「在頭盔上裝飾金銀色的牛角與五色長絲,讓樣子像鬼魅一般,可使敵軍感到驚駭,士氣盡失[38]。」
再者,《止止堂集》中的悼念死者的墓誌銘、祭文中幾無迷信成分,如〈王烈婦墓表〉中戚繼光記述王氏不侍貳夫投繯而死,僅表其忠烈為「嚴寒之柯,中流之砥[39]」。在〈祭殤女〉中雖有「汝父母平生無善狀,罰弗及躬,輒貽於汝,豈不冤歟!」的果報字句[40],但這係為中國傳統之民間信仰云爾,而帶有迷信色彩的多為戎馬時之祭告,如〈祭城隍〉中就提到:「倭夷干紀,屢犯孤城,咸保無虞,允神之庇[41]。」又〈祭馬神廟文〉中戚繼光感念「神之丕績,開右我三軍[42]。」在〈告旗纛廟文有歌〉曰:「赫赫神明,載之令典。國家禋祀,視昔丕顯。追惟南伐,實神之靈[43]。」這些都還不為過,在〈誓詞〉中他竟寫道:「我已經虔誠的告祭神明了,但報應未來,使得人皆無所忌憚,我憤憤神的懈怠,也恨隸人的不力,頹弊沿襲到現在都未改……希望神明能夠明鑑,降下天災、瘟疫等,使那些人死亡,滅子絕孫[44]。」
太多不理性的存在,甚至會使人不得不懷疑戚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深信不疑,這種可能確實存在,但可以確定的是他會表現出這樣的迷信是有其原因的,因為戚繼光除了撰寫祭文之外,還表現於行動上,他主持歃血為盟的儀式[45],設計帶有宗教寓意的圖案的軍旗、盔鎧,在對下屬訓話時也時常帶有善惡的輪迴觀念[46]。可以想見的是,英宗時後兵部左侍郎鄺埜欲倡議的武學,經大學士楊士奇等研議後,所授內容雖包含儒家經典與武學兵法,但原則上每日教授不過二百字[47],效果自然不彰,他除了嘆道:「此間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辨魯魚[48]。」也上疏請求將遵化、密雲、永平三地依舊有的武廟基礎上改制為武學[49]。教育樹人為終身之計非一蹴可幾,戚繼光面對於現實之無奈,以鬼神神秘之力量撫馭軍心也不足為奇了。
在品格方面,《明史》沒有太露骨的描述,只隱隱約約的用俞大猷來與之相比,結果是「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50]。」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因為就中國史書而言,一個人的事蹟被記載至列傳是一種褒揚,而他較負面的形象往往就會被輕描帶過,戚繼光的好友王世貞在〈張公居正傳〉中有就一段描述到戚繼光「操行不如」的事蹟,即譚綸把房中之術傳授給張居正,而戚繼光則花了大筆的錢購買「千金姬」作為禮品進奉給張居正[51],王世貞的攻擊對象當然是張居正,戚繼光只是配角,且我們不能排除王世貞還對張居正暗諷他「才人見忌,自古已然。吳干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52]。」還耿耿於懷,不過,王世貞與戚繼光關係既密,可以想見的是戚繼光必然有類似的事件發生,否則怎會有此空穴來風之說,且在沈德符所著的一本名為《萬曆野獲編》筆記中又可找到相關資料,只是戚繼光變成了進奉陽藥的角色,《萬曆野獲編》寫道:「媚藥中又有膃肭臍,俗名海狗腎……出山東登州海中。昔張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專取以劑藥。蓋薊帥戚繼光所歲獻,戚即登之文登人也。藥雖奇驗,終以熱發,至嚴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雖承命賜煖耳,無一人敢御,張竟以此病亡[53]。」如果這些指控皆屬實那戚繼光的完人人格就蕩然無存了。
張鼎思曾言戚繼光打仗在北方時不如南方輝煌,故要將他南調,就政治上而言這是藉口,但在軍事上來說確實也有一部份事實。戚繼光在南方訓兵時,編制、武器、戰術都有一番革新,他在編制上多了一名「火兵」,就是俗稱的伙夫,帶了一個廚師後,平時行軍紮營就不必拘泥於村莊距離了[54]。且左右對稱的「鴛鴦陣」讓隊中各種武器協同配合。在此之前,軍隊重視的是個人武藝,此一陣隊是團結合作的有機體,鮮少有個人突出的機會,因此他招募部隊的原則是只收樸實的農民而拒收城市居民[55]。
為農民而設計的鴛鴦陣在後來被加以改進用來對付蒙古。《明史》中對付倭寇多載經過及戰果,反而沒有提到鴛鴦陣的陣法,但是在對付蒙古軍時的陣法有十分詳細的記載,可以看出此種陣法即是在鴛鴦陣的基礎上改良而成,鴛鴦陣是以步兵為主的戰術,薊州軍鎮要防禦的則是蒙古騎兵,故陣法上載有「佛朗機」戰車運用,搭配備有钂鈀、單刀及藤牌的步兵迎敵[56],戰術雖然精緻完備,但戚繼光戍守邊疆不久後明朝便與蒙古人和談,所以究竟這種戰術能不能經過嚴酷的戰爭考驗,也似乎還是個未知數。
參考文獻
檔案史料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臺北:華世書局,1976)。
紀昀 總纂,《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87)。
孫武,《孫子》(臺北:臺灣商務,1988)。
張廷玉 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張居正,《張居正書牘》(上海:群學書社,1917)。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
戚繼光,《止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戚繼光,《紀效新書》(臺北:廣文書局,1976)。
戚繼光,《戚少保奏議(北京:中華書局,2001)。
焦竑 編,《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書局,1991)。
溫體仁 編《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蔡絛,《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專書著作
范中義,《戚繼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2004)。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聯經出版,2001)。
黎東方,《細說明朝》(臺北:傳記文學,1990)。
謝承仁、寧可著,《戚繼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