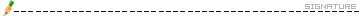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我出生於1927年貧窮的蘇北,貧窮,倒不是嚴重的事,國家、社會加諸窮人的苦難不斷才是艱辛備至。例如北伐戰爭,軍閥到處抓兵抓伕,土匪隨時出沒搶劫,即使一無所有,他們也是要向你敲詐一些財物。
此外,苛捐雜稅更是擾民,就算你擁有幾畝田地,所有的收成全部繳給各級政府,還是無法抵償各種巧立名目的錢糧稅捐。原本一貧如洗的家庭,如李密〈陳情表〉所說「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人丁單薄,再加上父親老實忠厚,經商倒閉,再怎麼辛勤耕種都不夠繳納。
再有,每天還要應付一批又一批的難民路過。他們為了果腹而奔離故鄉,被稱為「逃荒佬」。地方人士都會出來提供他們一餐飯,他們倒也謹守分寸,吃飽了以後就規規矩矩的離開了。
貧困本身帶來的窘迫也還罷了,窮苦的鄰人甚至把死屍抬到我家,說是我父親打死的,要我們賠償人命。好在最後還有一點公道,冤屈得以洗刷,讓我們能苟延殘喘地存活下來。
接著中日抗戰長達八年,每天兩軍交鋒,白天,飛機不時轟炸,機關槍凌空掃射,砲彈從四面八方呼嘯而來;夜晚,游擊隊和日本兵對抗。百姓外出,都要隨身帶一面日本的太陽旗,遇到日本兵還得彎腰鞠躬,通過他們的搜身檢查,才准通行。
有時為了躲避日本軍的捉拿,不得已睡在死人堆裡;有時為了討生活而涉江,不小心掉入冰窟之中……還是幼童的我,就已經歷九死一生,所以後來即使無端被抓,關進牢獄,乃至於綁赴法場,面臨槍斃之際,我都沒有半點畏懼,每天生活在動盪不安之中,不知道人生有什麼快樂,對於死亡,更不覺得有什麼痛苦了。
《禮記.檀弓篇》說得好:「苛政猛於虎。」滿清帝制雖已滅亡,太平天國以來的戰亂餘波未息,在動盪不安的局勢下,人民紛紛逃命,我也參與了「逃荒佬」,跟著他們四處流浪逃亡。
十二歲出家後,每天被打被罵,可以說,那種嚴苛專制的教育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也因為貧窮,飽受社會人士的歧視,屈辱的眼光、傷害的語言,無日無之。見聞覺知,盡是貧窮引起的痛苦,雖是幼年,已深切體會到亂世裡實在難以生存。
一個從來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的兒童,連學校都沒有看過,聽到的都是譏笑、嘲弄或謾罵;環顧四周,整個社會都沒有法制的保障。生命像蠶絲般細微脆弱,沒有作繭也會自縛,你說,哪裡還有什麼尊嚴呢?這樣不算是生於憂患嗎?只不過,對這許多加諸身心的苦難,早已習慣而不去計較它了。
及長,新四軍即與國民黨的軍隊衝突不斷,光是在我家鄉不遠處發生的「黃橋戰役」,就不知死了多少萬人。經常在家裡,只要聽到外頭「碰」的槍聲一響,就知道一條人命沒有了。雖然後來在抗日戰爭中,中華兒女獲得最後的勝利,但國共內戰又起,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真是情何以堪。
後來我抵達台灣,又逢戒嚴,行動沒有自由,連外出都要到警察局請假;半夜三更,還經常給警察叫起來詢問。甚至不知道什麼理由,出家人也被牽連,惹來牢獄之災。
慢慢地,想要為佛教做一些弘揚佛法、淨化社會人心的工作,卻經常要跟警察捉迷藏。甚至據警備總司令部的員警告訴我,密告我的人寫來的文書不只一兩尺高。我不知自己身犯何罪,也不曾結怨何人,這樣窮苦困頓的人生,佛教裡說「業不重,不生娑婆」,不禁慨嘆:生逢此世,真是業障深重,從而砥礪自己要在人間建設喜悅的淨土。
說起來,要感謝這許多憂患的歲月,養成我從小對生死無常無所畏懼,對生活的貧窮、對生命的磨難也沒有什麼慾望、期待。所以,我常說:苦是人生的增上緣,因為苦,成就我生存的力量,讓我在艱難中不覺得痛苦,在貧窮時不感到匱乏。
就這樣,我從台灣東北角的宜蘭來到南部高雄,在白色恐怖寸步困難的時期,終於有了機會建設寺廟,安僧弘道。哪裡知道,壽山寺才剛剛建好,附近的要塞司令部就下令要把它拆除,說我這棟五層樓的建築超高,妨礙軍事目標。
與我有關的高雄佛教堂,由於當時的社會仍處在動亂的氛圍中,信徒倒不是分南部人、北部人,而是分成台南派、高雄派、澎湖派等,互相排擠,彼此鬥爭。我那時候也很感慨說:「你們的地域觀念既然這麼重,最好把釋迦牟尼佛也請回印度去!」
及至佛光山開山,最初由於土地貧瘠、破碎,不好利用。歷經千辛萬苦,才慢慢將深溝填平,在上面興建房舍。那時候我還不懂工程,一場豪雨就引起山洪暴發,夾帶泥砂滾滾而下,把我的道路、建設毀壞了。像一座幾百坪的觀音放生池,就給大水沖倒三次;寶橋旁的一塊邊坡,眼看著就要被洪水沖走,不得已,只有發動早期跟隨我開山的徒眾們,把棉被、床單都拿來阻擋大水的沖刷。
比起人心的難測,對治大自然的破壞力還屬容易,人事才是困難。由於地方上的民眾不喜歡外省人在此建寺,相約不可以出售土地給外省和尚。加之,四、五十年前,由於佛光山位於山區,還不需要建築執照,才蓋好幾間房舍,縣政府就給我們出了另外的難題,命令我們必須購置兩部消防車、養活百位消防人員才可以建寺。當時的我,連想要買兩部摩托車都沒有辦法,還有錢財買兩部消防車嗎?還有餘力養活一百人嗎?這就是高雄縣政府最初對我建寺的指示。
好不容易,才把淨土洞窟、朝山會館建好,又有人說我匿藏長槍兩百支,其他的短槍、手榴彈、炸彈不計其數。可憐那時候的我,連兩百根棍子都買不起,哪來的兩百支長槍呢?
自古以來,一個地方的鄉鎮公所,本來都應該歡迎寺院、教堂前往建設,來協助安定社會人心;但我們在荒山建寺,好像對他們有很大的妨礙,所以竭盡心力給予阻撓。尤其,那時候我還算年輕,隨著佛光山的創建,佛化事業開展,卻引起治安單位的懷疑,一直注意我的動靜。好像我年輕的年齡就是我的罪業一樣,就是他們的敵人似的。有人說共產黨贊助我建寺,也有人說佛光山是印度祕密與我們交往的所在,甚至有人說國民黨為了利用我,出資讓我在這裡發展等等。其實,這一切子虛烏有的罪名,都是別人替我訂立的。
可憐的佛光山,光是一個寺廟登記就申請了十年,高雄縣政府遲遲不肯答應。鄉公所一次又一次行文,要我們在寺廟中心開闢一條產業道路(現在朝山會館旁的菩提路),讓給農民運輸農產品之用。奇怪的是,這是我在山區私有的土地,為什麼硬要叫我讓出來做產業道路呢?
甚至鄉民為此用鐵牛車圍山,不准我們進出。當時也有幾百名員警前來,都在那裡袖手旁觀,既不阻止鄉民鬧事,也不讓我們出入山門。不禁納悶:難道政府要讓幾百個佛光山的住眾活活餓死在山裡面嗎?
在都市裡的道場,以超高為由要你拆除;在郊區的私有土地建寺,也被團團包圍,硬是要你開路。你說,這還有公道嗎?
我一生沒有跑過政府,但我曾跑過多少次警察局;我從來沒有和民眾吵過架,但我卻數度在路邊與警察大聲理論,彷彿我也像那些流氓惡霸、黑道大哥一樣。但捫心自問,為了佛教的長存,為了眾生的慧命,我確實不能沒有這樣的道德勇氣!
想到過去三武一宗的滅佛逐僧,太平天國的排佛焚經,基督將軍馮玉祥發起的「毀佛運動」、教育人士邰爽秋提出的「廟產興學」,還有文化大革命時期見廟就燒等,可憐的佛教,為了建寺安僧、弘法渡眾,就要受到如此摧殘嗎?
當然,世間是變化無常的,自從蔣經國主政之後,兩岸開放交流,白色恐怖也成為過去,總之,人民的一條小命,還是得在法律的保障下,大眾才得以生存。儘管近幾年來社會風氣混亂,黑道橫行,殺人、搶劫等事件時有所聞,讓人憂慮不已,總體而言,人心普遍善良。時至今日,雖然在自由民主體制下,兩黨惡鬥紛歧,民間吵吵鬧鬧,令人感嘆這許多的前因後果,究竟要由誰來負責。
雖然歷經多劫,我從來沒有想過憂患的可懼,也不曾因為受到迫害而自暴自棄。我從小倡導喜悅的人生,一直以來最大的願心,就是將佛法、歡喜布滿人間,用慈和淨化社會,把惡劣的環境、紛擾的人事擺在心外,讓人人都能夠彼此尊重,共存共榮。我也深信,有佛法就有辦法,在我內心還是歡喜地為大眾服務。
像我創辦的育幼院、養老院,在種種艱困下都一一成立了。五十年來,我培育的兒童,已經成家立業的,至少八百對以上;在高雄佛光精舍、宜蘭仁愛之家的長者,本來都是希望住到這裡來,往生時有人為他們念經,不意住下來後都活到百歲高壽,讓我有機會奉養他們幾十年。你說,這些還不值得歡喜嗎?
在政治的壓迫下,過去的電視台不准播放佛教節目,我不斷奮鬥,今天的台灣,不是有很多的佛教電視台了嗎?以前民間禁止辦報,十六年前,我特地選在四月一日愚人節創辦《人間福報》,因為我覺得:做一個難得糊塗的愚人,用一股傻勁成就美事,不會痛苦,還會另有一番喜悅。
幾十年前,政府限制私人興學,經過鍥而不捨地努力,現在有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普門中學、均頭國中小學,均一國中小學,幾十所幼兒園和在海外五十餘所的中華學校,也在美國洛杉磯、菲律賓馬尼拉、澳洲雪梨分別創辦西來大學、光明大學、南天大學。我們也有五十部雲水書車,在偏遠鄉間巡迴,推動閱讀運動。每天學子的讀書聲遍布各地,怎不令人歡喜呢?
早期台灣的佛寺只在節慶時才開門迎眾,還處處打壓佛教,政府對於民間社團的成立也多所限制。一甲子以來,我奔走呼號,在海內外建立的寺院已不只二百座以上,國際佛光會數百萬會員遍布全球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每天光是信徒、會員,就不只千人、萬人一起聚會用餐、談法辦道,我還不該歡喜嗎?
所以經常有人問我一生有過什麼困難?實在說,一時也答不上來。我之所以不覺得有困難,大概是我向來抱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心態順其自然,所以還會有什麼困難呢?在九十歲的當今,我的一生應該可以用十二個字來表述,那就是:生於憂患,長於困難,喜悅一生。
五月十六日是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紀念日,我將此文發表於《聯合報》、《人間福報》,同時也在《人間佛教學報.藝文》雙月刊陸續刊載。借此機會,我要告訴萬千的信徒:謝謝你們,跟隨這麼一個傷殘的老僧,是你們給了我許多好因好緣,你們要與我共同歡喜。因為,憂患可以長養我們的身心,困難能夠增加我們的力量,而唯有喜悅,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寶藏。
轉眼間五十年過去了,事實證明:支援佛光山的,不是印度佛教,不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而是佛光山許多默默奉獻的功德主們。由於你們不計較名位,或把小錢集合起來,廣結善緣;或以力量布施三寶,護法衛僧;或用智慧供養大眾,普及教化,成就各種利生事業。實在說,你們這許多的信徒護法才是佛光山最強大的後盾。
不僅如此,即使是外國人士、佛教之友或政黨人士能夠給予一點助力,也都是好事,都值得感到歡喜,因為有了大家的共同付出,這世間才會更加美好。更何況我們既沒有貪贓枉法,也沒有私相授受;既沒有侵占國土,也沒有逃漏租稅;一切都是為了給人歡喜,為了公益,又有什麼罪過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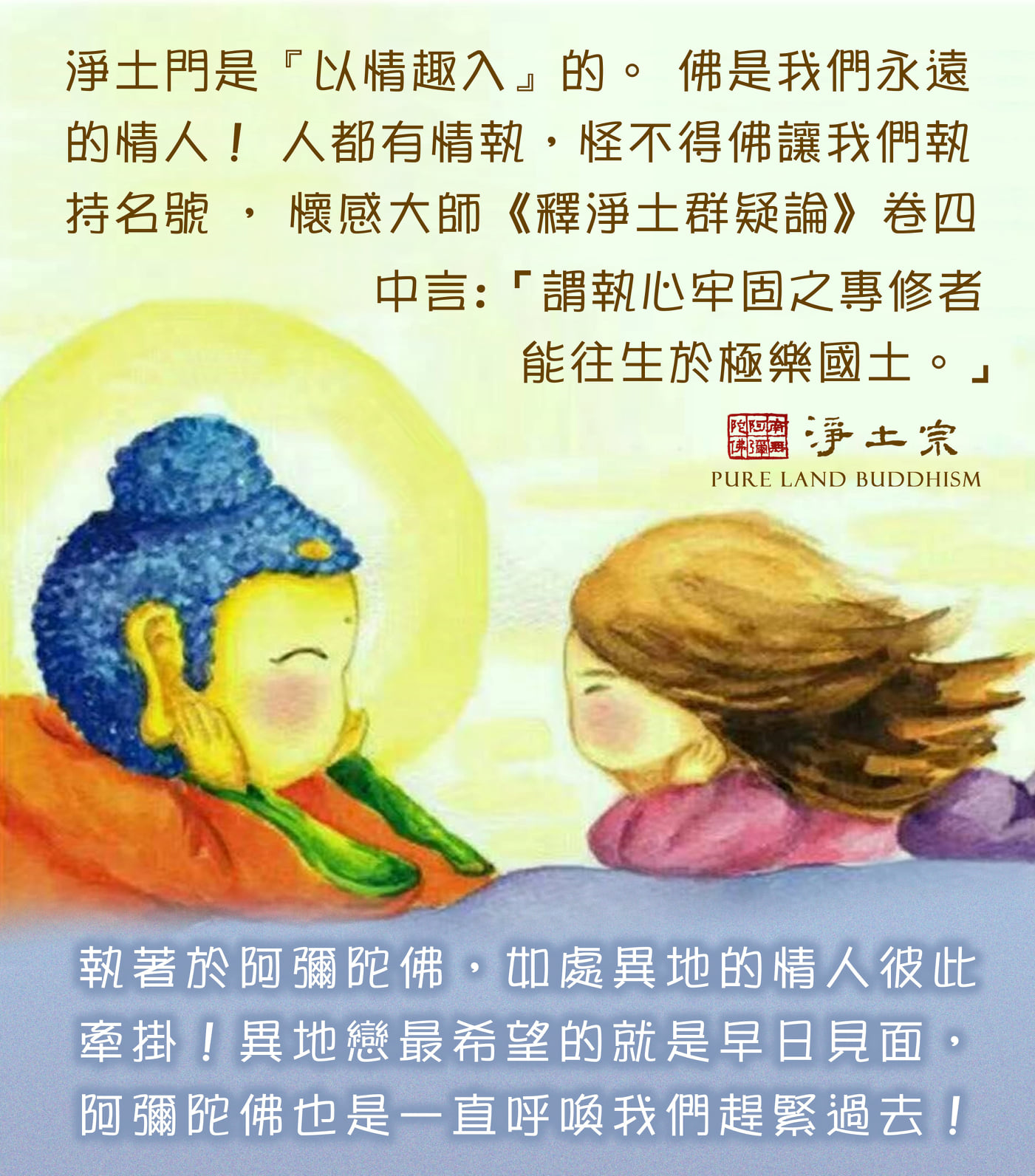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