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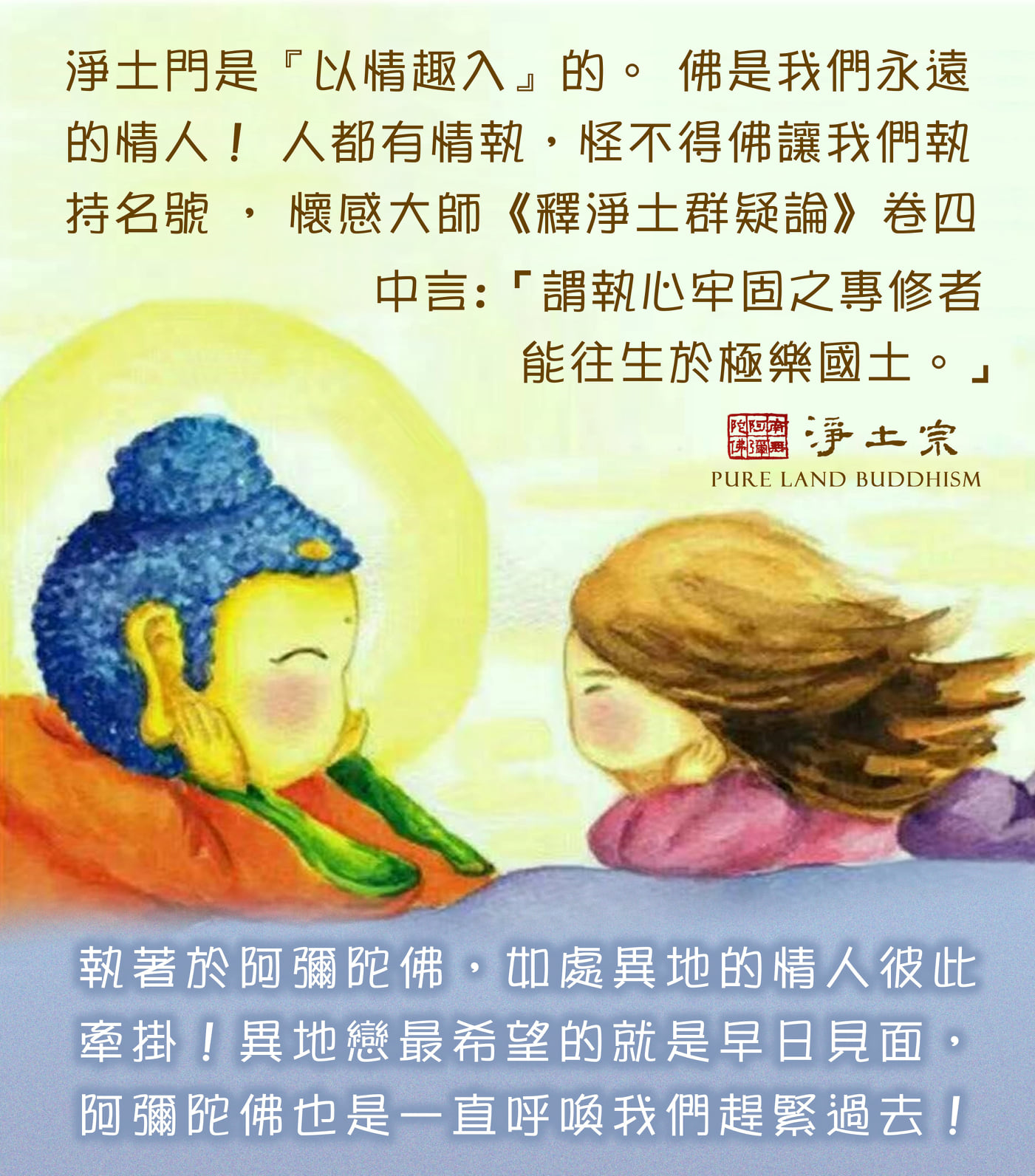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革了文化的命,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文革期間,因為破四舊的緣故,多少文物遭劫,恐怕已經難以統計,地面建築,除了幾個特別著名、由軍隊保護的,基本上都化為瓦礫。至於雕塑、牌匾、器皿、書畫等等,被踐踏、搗毀、焚毀者根本沒法計算。
文革也是個全民焚書的歲月。納粹德國的焚書,也無法與之相比。舉國上下,沒有什麼書是可以倖免於火神爺祝融氏的,中國古代的書,是封建主義的,外國書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蘇聯的書是修正主義的。1949年以來出版的書,是中國修正主義的。封資修三字標籤一貼,掃蕩一切。能倖免的,除了馬列選集,就是魯迅的書。但這也要看地方,有的地方,擁有馬列的書也有問題,因為,你為何重視馬列,輕視毛的書呢?
在文化革命中,最慘的是文化人。從舊社會過來的,不用說,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有留學經歷,哪怕從蘇聯東歐回來的,都是特務。就算你根正苗紅,又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也照樣資產階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過衝擊。大學裡的專家、教授,則無一例外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戴高帽子上街的。如果臉皮薄受不了,那就死路一條了,自殺,還要最後一次被批鬥,說你是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
文革剛結束的時候,文革的這種革文化的命的現象,被稱之為文化蒙昧主義。給文革的文化大破壞定性,這樣的說法,當然並無不可。但是,對於文革的發動者而言,他們為何要這樣人為地製造蒙昧呢?這種掃蕩一切文化傳統的革命,是要達到什麼目的呢?文革雖然瘋狂,但發動和操控文革的人,卻並沒有發瘋。他們在打到封資修的名目下掃蕩了一切文化,目的是要建設一個全新的文化。用他們的話來說,是有破有立。立的成果,最典型的,就是迄今還被稱為紅色經典的樣板戲。
客觀地說,集中了當年文藝界精兵強將,花費大量時間磨出來的樣板戲,從形式上,的確有可觀之處,主抓樣板戲的江青,也不是不懂戲。但是這樣的文藝作品,卻沒有絲毫的人性在裡面。所有的男女角色,都沒有配偶,《杜鵑山》里的女主角柯湘,好容易有個老公,但沒出場就已經死掉了。《沙家浜》里的阿慶嫂總算有個阿慶,但卻去上海跑單幫去了,始終沒見人影。《智取威虎山》里,連作為配角的老常寶,連想一下被土匪殺害的老婆都不能。不僅沒有男女之愛,連親情幾乎也沒有。《紅燈記》里的家庭,三口人來自三戶人家,仔細論起來,彼此也只有革命情義。所有的樣板戲,只有革命,革命戰爭,沒有人性。人性,恰是這場大革命所在文化領域重點掃蕩的對象。
這樣對人性的絕然摒棄,跟文化傳統的決裂(還好,沒把文字也一併廢了),即使30年代已經相當革命的普羅文學運動也沒做到。那時候中國、日本和蘇聯的普羅文學,至少還有人的情感,人的感情活動,最革命的,也有親情。顯然,這樣沒有人性的文化產品,不能稱之為文藝作品,沒有任何文化意味,只能是革命宣傳品。這樣的宣傳品,也只是旨在動員和推動革命。在某種條件下,的確可以做到讓人頭腦里只有革命,沒有作為人的基本屬性,這樣的革命,持續下去的話,當然也只能走到非人的世界裡去。
其實,當年的樣板戲,如果在正常的社會裡,基本上不會有市場。即使在文革前夕,中國政治空氣已經相當左的條件下,樣板戲也沒有多少人樂意看。可是,一旦把所有的文學和文藝作品都禁錮起來,再把樣板戲拍成電影,電台成天播放,農村的大喇叭成天唱,各地文藝團體通盤複製,讓人們眼裡看的,耳朵里聽的,就是這些樣板戲。
你還別說,就當年而言,還的確真的起到了存革命,滅人慾的效果。讓很多天真的革命青年,腦袋裡只有領袖,只有革命。爭先恐後,為領袖去死,為革命獻身,爭當樣板戲裡的革命英雄。當年的過來人,經過這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灌輸,眼睛一閉,樣板戲的畫面就會浮現出來,一張嘴,就是樣板戲的唱段。文革結束多少年了,只要一唱樣板戲,過來人還是有人會手舞足蹈,跟着哼唱。其實,除了少數人之外,多數人這樣的表現,只能是癥狀,被強迫精神吸毒成癮的心理癥狀。
當然,我們知道,人其實都有人性。人性可以被壓抑,但無法徹底擯棄。無論古今中外,只要能流傳下來的文藝作品,文化遺產,或多或少,都有人性的內涵。被壓抑的人性,只要接觸了這樣的東西,就很可能被點燃,重新復蘇。文革後期,很多人就是偷看了一點點文革的禁書,甚至粗劣的手抄文學作品,就會導致“思想混亂”。要想維持革命的純粹性,在文革的發動者來看,唯一的途徑,就是維持革命宣傳品的純粹性。這也是為什麼文革後期,按照樣板戲的創造原則弄出來的一些電影和小說,還是難逃被批判下場的原因。
當然,這樣的純粹的文化掃蕩,文化建構,並沒有生成一個純粹的革命。人性美好的東西被擯棄了,但人性陰暗的一面卻在革命中大爆發,這場革命對人和人性的摧殘,至今還令人心有餘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