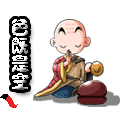不願意吃虧其實是不會修行, 吃了虧就消了業. 這是我的經驗之談.我是個老老實實的人, 多說兩句話臉就紅, 當當家, 沒人願意聽我的也沒甚麼成績, 但我知道人家要
佔你便宜就給他佔就好了, 我們多忍耐一點, 吃虧就是占便宜. 但是心裡不能放不下, 放不下就沒功德可言了.
臨時大殿還沒拆的時候, 有一回, 一個從這邊出去的比丘尼回來, 在大殿裡罵三罵四, 說這個道場怎麼樣怎麼樣壞, 雖然她沒指名罵誰, 但就我一個人在那裏, 她不是罵我
罵誰? 而且她的話都不講理, 我聽了很生氣, 但是我回不上嘴, 光站在那裏忍耐她的數落, 雖然心裡有瞋念, 但起碼沒跟她回來回去.
後來我上地藏殿旁的寮房坐, 望著窗外, 窗戶外面是大悲樓的空中花園,對面是雙象山, 忽然我把山看穿了, 整個臺北盆地一覽無遺. 眼前明明是翁鬱的青山, 怎麼突然
消失了呢? 這境界證明忍耐,吃虧是有功德,有希望的. 前途一片光明, 連牆壁,山都擋不住.
我們如果相信吃虧就是占便宜, 遇到境界時比較不容易起心動念, 意見不一樣時也比較能遷就別人. 自己吃虧的事情不願意做, 基本上就是有人我分別之心, 一計較即生
貪嗔癡, 即落於世俗, 六道輪迴都是分別心造成的,如果吃了虧心理不起心動念, 那就修成了, 在修行上要月老實越吃虧越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悔法師」是一代大師「廣欽老和尚」的高徒,承天禪寺第二代住持,傳悔老和尚一開始喜歡讀書看經,禮拜法華經也得到殊勝的境界,可惜心還是無法安定。
後來聽從廣欽老和尚的指導,發心為常住做事,修苦行,專一念佛,終於得到心安,在佛法的實證上有了不可思議的成就。
有佛住世龍天喜,
無僧說法鬼神愁!
辛已(紀元二零零一年)春節期間,驚聞土城承天寺住持傳悔老法師,已於年前臘月二十八日安詳示寂,頓時心頭一片愕然與無限哀慟;感歎業海浮沉的芸芸眾生,又失去一位以身示教的善知識與克繼祖業的菩薩行者!傳承廣欽老和尚「念佛、修苦行」的道風,傳悔法師被推崇為「自力往生」的大修行人;而十多年來承天寺大力捐款贊助慈濟、華梵、玄奘、佛光及法鼓等佛教大學的建校經費,更成就了「若要佛法興,除非僧讚僧」的隨喜功德!
傳悔法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三十又四;法名普過,俗姓柳,民國十二年(紀元一九二三年),生於山東膠縣柳家屯。父啟泰公務農為生,母王氏則操持家務。師自幼喜好讀書,十歲入私塾習讀儒書,直到十六七歲。由於受到當地民間信仰的影響,少年時代對於修道即懷有興趣;十歲左右,因讀古章回小說上的一首詩:「何日空巖下,跏趺入定真。籐蘿繞瘦骨,虎豹護枯身。永入無生路,長為不滅人。茫茫堯甲子,天地幾回春。」小腦袋瓜便經常思索:「如何才能永入無生路、長為不滅人?」心中不禁嚮往出家修行的生涯。
民國三十一年(紀元一九四二年)師二十歲,父親不幸死於土匪的亂槍下;加上時局不靖,家鄉已無法安居立業。師遂於這年,兩次負笈異鄉求學;惜因戰亂,學校相繼被迫解散。民國三十三年(紀元一九四四年)冬,師二十二歲,奉母命迎娶鄰村農家女呂琮為妻。翌年春旋遠赴即墨縣,通過日本偽軍的小學教員甄試,初任教職。該年秋,對日抗戰勝利,師與友人計劃至外地讀書;臨行前,夢見家鄉風俗象徵「一去不回」的白公雞,雖然心裏因此不舒服,但「時間到了,我還是上路了,只是心頭上懷著這件事離家,而且它還影響我後半生的決定。」師日後曾如是說。其後因地方匪徒鬧事,先是任職於膠縣縣政府政工隊;繼而在民國三十五年(紀元一九四六年)春,流離至青島,投考五十四軍政工隊員,棲身於即墨縣。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參加青島陸軍普建班訓練,結業後擔任三十二軍指導員,開始軍旅生活。一九四九年轉任準備指導員,該年端午節,隨軍自青島登船撤退台灣;不久,移防海南島。一九五零年調防澎湖;一九五四年,師三十二歲,乘海輪自澎湖抵達高雄,徒步行軍一週後,至成功嶺,接受軍事教育。一路上,彼等士兵不只要忍受刺骨的風吹雨淋,還要咬緊牙關,拖著早已起泡破皮的雙腳,勇往直前!此番長途跋涉,帶給師如下的啟示:「碰到不如意的事,除了忍耐之外,沒別的法子,勉強自己走,也總是走得下去的,忍耐過了就沒事了!」
白公雞的夢境,激發師時時反芻生命的意義;又因為認知返鄉無望、後路已斷,逼得 「自己不得不尋找解脫的途徑」。是以在部隊十幾年中,師「一直在尋找出家的因緣 」。在成功嶺受訓期間,師利用假日,前往情教台中蓮社的李炳南大居士;惟當時善根尚未成熟,對念佛法門自覺十分不相應。一九五七年,師隨軍駐防台中新社鄉,無意間認識精通佛法的張姓居士,從而埋下隨後皈依、茹素、戒煙等因緣,總算如願步上學佛之路。次年,師於台北松山寺,認識道安法師,出家之心益形迫切。一九六三年秋,師四十一歲,自軍中退役後,即到松山寺親近道安法師,接編《獅子吼》雜誌;約十個月後,轉往花蓮師專特師科,接受師資培訓,預備畢業後教書。孰知一年後,卻因一偶發事故,促使師決志離俗出家,便積極托人介紹修行的道場。
一九六五年,透過性梵法師的引薦,師至土城承天寺常住,預備出家,時年四十三歲。師一到承天寺,住持廣欽老和尚故意擺出一付極度不歡迎的臉色,彼此不僅言語不通,所採取的修行門路,更是南轅北轍!抱著隨順因緣的心理,師勉強按捺自己安住下來。由於一向認定「傳統的修學佛法就是看經嘛!」師對於廣欽老和尚:「你念佛就好,不要看書!」的開示,壓根兒聽不入耳,私心所在乎的,不外是「如何利用為常住作務之餘暇研讀經典?」及至圓頂(一九六六年臘月十五)、受戒(一九六七年農曆十月),師始終抱持這般心態。倒是打從師出家後,廣欽老和尚一改先前的態度,對師格外器重,並委以當家一職;然而師以恐耽誤看經為由,不敢從命。雖然師曾當著廣欽老的面,發願住在承天寺,但終因「心不安定」,乃於一九七零年,離寺至外地參學,先到五指山閱藏五個月,再轉往獅頭山閱藏、拜經,前後五年。
一九七五年春,返回承天寺;復於同年夏季,二度離寺至日月潭,親近道安法師;半年後重返承天寺,時為一九七六年春。師自認為:「過去我是發心不夠,不願做當家而出去參學,現在人雖然走頭無路回來了,可是心還沒完全改變,事實上也不是那麼容易。」話雖如此,卻也願意「考慮考慮、慢慢地」接受廣欽老「念佛就好,不要看書!」的建議。不久,因夜夢右手心有只白老鼠,師漸漸領悟到:「我修行的正途,確實不在讀書、寫文章上。」而在正式受命為承天寺當家前,師即遵廣欽老的囑咐,每晚領眾念佛共修一支香;此「慧命香」遂成為該寺住眾人人必修之常課。
一九七七年六月中旬,原任承天寺當家不告而別。眼看七月法會就要登場,沒人當家總責其事,怎麼成?為顧全大局,師硬著頭皮答應廣欽老和尚,願:「盡心盡力!」挑起當家這個重擔。復由於當時已深切認清楚出家的真義在於「修行、消業障」。過去十年,自以為看經就是修學佛法,就一味學別人看書、讀經。而實際上,道業進展有限,業障依舊未消。於是,師斷然「改弦易轍,回頭完全接受老人的指導:念佛!為常住發心做事。」
既然為修行發心接當家,師便要求自己「拚命把心放在常住上,犧牲身命都不計較! 」從一九七七年七月至一九八零年七月,師「依教奉行」的結果,明顯感應到與當年在獅頭山拜《法華經》同樣清淨的境界,驗證了廣欽老的法,是正確的!從此以後,師心悅誠服地實踐廣欽老的教法,「把書本完全丟開,為常住做事,一邊工作一邊念佛,心裏很安定,很法喜」。師「轉迷為悟」的欣慶之情,充分表露在其「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已幸聞。明師又示成佛路,三大勝緣集吾身。」之詩作中。
師擔任當家時,正值承天寺進行殿堂重建工程。白天忙著搬石頭、鋸木頭、割草、劈柴、挑砂石、處理寺務,晚上領眾共修;即使夜晚安板養息,身體雖躺臥著,只要未闔眼,心裏照樣盤算著如何做好常住的事。師自云:「同樣用心,會用功的發心為別人,為別人即是戒定慧,為自己就是貪嗔癡,雖然在鋪上躺著,但用心在常住上,也是修行。修行是在心裏,不是在外相上!」如此一心一意,專注在工作上,內心則不忘念佛,凡事忍耐,不與人計較,不分別、不覺得吃虧,全然將一己佈施給眾生;幾年下來,師不但不以為苦,反而感到身心更安定,消了很多業障。
師曾將平日得自廣欽老的開示,以四句話綜括:「夢是顛倒,行依經論。苦作道緣,韋陀擁護。」對於「苦作道緣」一句,師有獨到的領解,他認為,吃苦不是專指做甚麼苦差事,也不光是勞心、勞力,而是「遇到困難要勇敢地面對,為了大眾的利益犧牲自己,不要把自己擺在前面,大乘佛法看重為別人、為眾生吃苦,為大眾服務才有意義!」佛陀也告誡弟子:「無益之苦當遠離。」而在通過了大小難關的考驗後,師堅信只要真心修行,碰到困難時,「佛菩薩都會護持,都能夠逢凶化吉,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九八六年春,廣欽老和尚圓寂於高雄六龜妙通寺,師依老人指示繼任承天寺住持,除秉持廣欲老遺教,維護承天寺苦行、念佛道風之外,更發大心,鼎力護持國內外佛教教育機構、道場興學、修行。師以隨喜功德之心,廣行佈施,並曾表明:「我們只負責捐款,不過問錢怎麼用法,依你們的需要建設即可。」坦蕩的心胸,令受捐助的單位,真個是感激萬分,又敬佩不已!
一九九三年夏,師之色身一度情況極差,腿腫與左肩風濕痛,尤其厲害,雖歷經中、西醫診治,仍然未見起色。師卻因此「向上一著」,提醒自己是出家人,應把心放在佛法,不要把病放在心上,「出家人的時間很重要,小病又死不了人,不要為了小病浪費時間。」平常除了處理重要寺務外,師將大部份的時間都用來念佛。「念佛時心是佛」,師勉勵學人:「平日用心念佛、用心做常住的事,累積清淨因,將來必得清淨果,身壞命終時,阿彌陀佛必現前接引往生,在修學佛法上,要一輩子念佛才好。」
師晚年死心蹋地念佛,也勸人勤念「南無阿彌陀佛」「多念佛,經藏就在心裏」,師步廣欽老和尚後塵,印證了這句話!
最後,謹恭錄佛光山心定和尚,於傳悔法師圓寂後所作的輓聯一首,以示追悼之情;並祈師乘願再來,廣度眾生!輓聯云:
傳揚淨土,如今前往蓮邦依彌陀;
悔入涅盤,何日再來娑婆度眾生。
(文據陳秀慧著《高僧行誼》)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