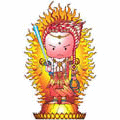學佛二三事
寂光寺
每日面對許多繁瑣的事、面對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在這緊張的生活中修行?
有一位蓮友見師父每日都長時間的應對信徒,而且不厭其煩地開導,見師父用很多時間勸說學佛、吃素對自己與他人的影響,雖是如此仍見師父精神奕奕,一點倦容都沒有;可是自己整天面對顧客卻很沒有耐心,於是請問師父是如何做到的?
師父說:身忙心不忙。
蓮友問:如何做到?
師父說:幫他人忙時不要想到自己的辛苦。
師父年輕時經常到某道場,也很受道場裡師父們的照顧,尤其一位年長的比丘尼。老師父很喜歡和師父說話,但老師父卻慢慢出現失智的現象,每次師父去看他便很高興,但老師父卻同一個問題會一連問了好幾次,比如:你吃飽了嗎?你在**道場,那裡的人有沒有欺負你?……..
照顧老師父的侍者,每到這種情形都會對師父說:某某人,你不要理他,他常常這樣。
師父就對侍者說:某某師父,你去忙你的,把茶留下來就好,我陪老師父說說話。
對長期陪伴失智老人這事,有些人真的會覺得很煩,因為覺得這個失智的病人很「花」(台語,意指在重複的事情上打轉)。但師父覺得我們把心調到遇到很煩、很瑣碎的事時,先不要想到自己會很辛苦,不要先覺得對方很「花」,這樣就不會覺得煩,同樣也能幫失智的病人解決問題。
第二個例子:
當我們還在牙牙學語時,做爸爸的人會抱著我們,要我們開口說:「叫爸爸,叫爸爸」,我們的爸爸可能要教我們念幾十次或更多聲「爸爸」後我們才會含含糊糊地叫聲「爸爸」。
當爸爸聽到我們叫他時,他會非常高興,也會抱著我們向他人炫耀。可是當父親老了,我們卻對他的呼喚或叮嚀變得沒耐心。
第三個例子:
寂光寺還剛在建造中時,一位素昧平生的女眾在師父回國的機場上供養了師父一筆巨款當建築用。
幾年過後,師父認為道場已有初步的規模,想到當初從不相識,但一次就供養巨款的捐贈者,便想透過第三者邀請她回來看看。
負責聯絡的第三者轉告師父的意思後沒多久,就有一位也是捐贈者平日親近的居士打電話給師父,對方的意思是認為師父還想再一次從那位女眾身上募到金錢,於是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數落師父,並說師父會下十八層地獄。
師父對提問的蓮友說:我當時並沒有生氣,我只是把電話筒放在桌上,我繼續與信徒說話。
蓮友問:師父您當時為什麼不生氣?
師父說:我又不是他罵的那種人。如果我是他所罵的那種人,他不用罵我,我還是要下十八層地獄,如果我不是他罵的那種人,他罵我,我會下十八層地獄嗎?我建這座道場時,我都在每個設計、每個材料的細節上斟酌很久,該怎麼做才不會讓以後的人有收不完的爛攤子,該怎麼做才能把每一分奉獻人的捐款用在最正確的用途上,我所想的都是如何把每一件佛教象徵的器物,讓生產者成為他今生最登峰造極的作品,我所想的都是這些,所以我沒有時間為那些無聊的事、無聊的話所苦惱。雖然我不為那些事苦惱,但我依然要檢討自己是不是有做出讓人苦惱的事,這樣才能真正去煩惱。
第四個例子:
有一天,東坡居士突然靈感來了,隨即寫了一首自許為不朽的五言詩偈: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他再三吟詠,感到非常的得意,認為這首頗具修持工夫的創作,如果讓佛印禪師看到,一定會讚不絕口。於是趕緊派書僮過江,專程送給佛印禪師去欣賞印證。
誰知禪師看後,不禁莞爾而笑,批了兩個字,便交給書僮原封帶回。
蘇東坡在期待中接回「佳音」,總以為禪師會讚歎一番,急忙打開一看,只見禪師寫了「放屁」兩個大字。
「豈有此理」!蘇東坡忍不住這一招,隨即叫書僮趕忙再備船過江,要親自到金山寺去找佛印禪師興師問罪。
船才靠了岸,便發現佛印禪師已站在江邊相迎了。
東坡一見佛印禪師,怒氣沖沖地吼道:「佛印!我們一向相處得很好,縱然我的文字不夠水準,你是一個有修養的出家人,怎可隨便惡口罵人?」
禪師若無其事的問道:「我罵你什麼」?
東坡一聽,臉都脹得通紅,已氣得說不出話來,只顫抖著手,指著「放屁」兩個字,讓佛印自己去看。
禪師不禁哈哈大笑道:「大學士!你不是自誇『八風吹不動』嗎?怎麼一屁就把你打過江來了呢」?
蘇東坡到此才恍然大悟,只好低頭不語,唯有慚愧而已!
如何身忙心不忙:真正忘了自己,沒有小我,只有大我。
雖然很難,可是如果身忙心跟著忙,雖然嘴上不說、不抱怨,但心裡卻是鬱悶的,我們這個「心」設計師,就根據心裡的鬱悶畫出設計圖來,這張設計圖又根據自己說出的話、做出的行為,表現到外部世界,於是我們抱怨什麼,那些我們抱怨的人事物就出現在我們身邊。這樣心反而會中毒越深。
因為「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