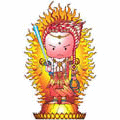一位抑鬱者的自述
編者語
沒得過這種「病」的人,無法理解患者失去活力的絕望,而患者們被困在情緒的城堡中,實在突圍不出去,往往選擇結束生命。無論擁有多麼顯赫的身份、富裕的生活,他們都願意以死的痛苦,來卸下生命的重擔。也許,我們對生命的真相瞭解的太少了。
本文作者通過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我們展示了突圍的另一種可能。假設你身邊有患抑鬱症朋友,亦或陌生人,請給予理解、耐心,並示以愛和真誠。倘若那真是他生命的關口,我們的尊重與努力,很可能會幫助他突圍成功。
抑鬱症之癒
在過去的兩年,作為抑鬱症患者的一員,我經歷了此生最難堪的一段時光。心尖上刀光劍影的日子,使我不時想放棄生命,並差一點成功。
後來,我擺脫了抑鬱症的折磨。此中滋味,如今細細回味,像場大夢,又像一部開頭悲劇而結尾喜劇的電影。
謹以此文,獻給您,獻給幫助過我的醫生和朋友,獻給抑鬱症朋友們。
一、精神科重症患者
「六號就診者,請進4號診室。」
2010年8月的一天,在人來人往的候診區待坐了一小時後,終於輪到我了。這裡是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分析研究所,一位主任醫師的診室。
能預約到這位專家,我等了一周。住在繁華的大都市,以前只知道身體上的病,掛號難,看病難,現在才知道看「精神病」的人也特別多。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周圍的人們覺得我越來越不靠譜:有時一整天都不說一句話;朋友們聚會,我答應他們一定參加,卻在出門前不得不考慮如此艱難的事的每一個步驟,不停地換衣服,拖到時間都過了,開了門,又關上門,走下樓,又上樓,還是不能走出去,最後只好撒謊說「有事去不成」;一看到電話進來就很緊張——他們為什麼要給我打電話?我該說什麼?於是很少接電話。家務活已很久不做,因為我不知該如何去完成掃地、抹桌子這類事。總之,我越來越害怕,卻不知怕什麼。
而且,哭泣成了生活的主要內容,睡醒哭,坐車哭,上班哭,下班哭。那時流的眼淚,真的比前三十年流的所有眼淚都要多。
一位好友看了一期節目,一位患抑鬱症的歌手接受採訪。她於是對我說,「你是不是也考慮找醫生診斷一下。」我仔細看完了那個節目,歌手患中度抑鬱症,治療了八年,還得繼續治。他的症狀,我較之更甚。
預約掛號,才知道得掛精神科。
「請坐。」隔著寬大的辦公桌,嚴肅的醫生開口了。
我想,自己當時的狀況,一定令這位醫生感到不適:瘦若枯枝、黑眼窩、灰暗的氣色,用朋友後來的話說,活活像剛從棺材裡爬出來的。
「請談談你為什麼要到這裡。」他的語氣平緩而專業。
「醫生,我最近心情不太好……」
「你的飲食和睡眠情況怎麼樣?」
「我基本上是晚上十二點左右睡著,兩三點鐘醒來就再也睡不著了,半個月瘦了十多斤。」
「你有沒有想過自殺,如果想過,有沒有想過怎麼實施?」
「我想過怎麼實施……」
「說說你的家庭和成長經歷吧。」
「……」
「女士,別哭了。你後面還有別的病人,我們已經超時了。」談話在我不停的哭泣下進行了一個多小時。
「大夫,我是不是真的得了抑鬱症?」我一邊抽泣,一邊問。
大夫無奈,卻肯定地說:「你不僅是抑鬱症,而且是重度抑鬱,需要住院治療。」
我呆若木雞,重度抑鬱?這怎麼可能。
大夫看我遲遲不願接受這個結果,口吻近乎是下命令了,「你的情況需要住三號四號病房,我現在給你開住院條,你交給住院部,然後等我們通知來住院。」
看著眼前這位嚴肅溫和理性沉默的專家,我再次淚如雨下。
為了證明自己根本沒有這麼糟,我用殘存的理智問道:「什麼是三號四號病房?」
「全封閉式的,不能自由進出,一周接受一次親友探視。所有的個人物品都得交出來,包括手機電腦鏡子梳子……」
我的大腦裡迅速出現了對精神病醫院的所有印象——封閉式病房。不能逃跑!——此時的我,混亂了。
「大夫,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我不能住院啊,我得工作,沒人照顧我的貓……」
看得出,醫生是以極大的忍耐力解釋說:「你不要以為是個人來看病就安排住院。我們醫院的床位非常緊張,要等有空出來的床位你才能住進來。很多病人家屬要求住院,我們都是不同意的。之所以叫你住院,是考慮到你的病情和生命安全。你懂嘛?」
「我懂。可是……」可是了半天,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在等床位的這段時間,先給你開藥,早晚一定要吃藥。」
拿著醫生開的住院條,我去了住院部。我終於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了,和別的醫院不一樣。住院部的視窗裝著鐵柵欄,護士動作麻利地讓我填寫個人資訊。輪到家屬簽字一欄,她說:「這裡需要家屬簽字。」我答「沒有家屬」。
還記得,雙手冰涼冰涼的,走出醫院大門的那一刻,我開始頭暈。從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出現在人多的地方就會渾身發抖,四周的物體在我的視線裡發生遙遠的彎曲,眼珠經常盯在一個地方。
恐懼和希望交織著,回到家翻開病歷,上面寫著「……內在驅動力不足,對人生失去希望……建議入院治療,防止實施自殺。」
病歷翻來覆去看了很多遍,想起了醫生的話:「你一個人住,太危險,很多患者因為一時想不開就自殺成功了。如果身邊有人陪伴,會好一些。」
可我的婚姻失敗了。
夜晚怕黑,每晚開燈睡覺,醒來即被悲傷和恐懼包圍,流淚到天明;朋友、同事,沒人能理解我的痛苦,甚至比我自己還不能接受醫生的診斷——「別開玩笑了,你會得抑鬱症?」
是的,這和他們印象中的我太不同了。但是,最近幾個月我每時每刻都在尋找答案:八歲那年,父母以激烈的方式離了婚,彼此為仇並各自再婚,母親則和我形同陌路,我覺得自己是被拋棄的、十分不可愛,這種感覺在我心裡滋長了二十多年,直到離婚了才發現,卻已像老藤,纏繞著每根神經。醫院可以給我答案嗎?還有什麼路可走?
禍不單行,幾天後我又失去了工作。領導示意會有人來接替我的職位,因為得了這個病,永遠不能再回到原來崗位上,即使回去工作,薪水也只能是原來的三分之一。——果然是我不可愛。
茫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小屋,我關上了所有的窗,遮罩了所有的人,唯一未關的窗,抓住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是——心理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