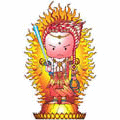智慧天女
我經常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和益西拉姆(智慧天女)的不可思議的相逢,我無數次想:那是偶然的嗎?
多年前,我從成都到瑪律康,因前方公路塌方,等了一張去阿壩的車票,準備從阿壩繞道色達。
車開了兩個小時,中途,被一個藏覺姆攔下。她搖搖晃晃,走到與我隔了一條過道的空位坐下。整個車廂,只有這個位置空著,等著她。
得知我去學院,她告訴,去年五月,她和三個出家人從觀音橋磕長頭到拉薩,每天磕十公里,歷時九個月。
她自然,大方,聲音不高,音聲柔美,發自她溫煦寬厚的胸懷。
她們四人沿著川藏公路,經過甘孜、石渠,進入西藏。卡車卷起長長的塵土和嗆人的黑煙,有時,她們磕到晚上十二點,有時到淩晨二點。一位師父發心推車,帳篷、鋼爐和糌粑都放在那輛小車上。沿途,常有人供養她們食物,表示對她們的崇敬。途中,她們還遇到五明佛學院的丹增活佛的車,活佛下車來,供養了她們五百元,送給益西拉姆一張名片。
前方堵車,車上的人都下來休息。路邊,是一望無際的綠色牧場,遠遠地,遍滿黑色點點的犛牛,有三頂牧人的帳篷,幾條狗在犛牛間追逐。益西拉姆一手伸到背後,溫和地拍了一下我的背:
“你為什麼不出家呢?”
“會的,”我笑著說:“會的。”
“什麼時候?”她說:“出家好,好耍得很。”
在遼闊的夏日高原上,她雖然身穿冬天的僧衣,可她是那麼無拘無束,鬆弛,自在。
她告訴我,她磕頭到拉薩,遇到一個漢僧,三十來歲,穿一件百衲衣,鬍子垂到胸前。他專注地看她,說:“好像在哪裡見過你?”
“我從來沒有見過你。”她說。
“不對,”他笑:“是在哪裡見過你。”
她也笑:“是不是我前世見過你?”
“你好聰明。”
他們相視大笑,笑了又笑,忘了身邊遊人如織。
她和師父面對面坐了三天。師父在五臺山閉關二十年,他要求她在五臺山閉關十年,授記她將是比丘尼的師父。
“我沒有聽師父的話,”她喃喃:“我現在非常後悔。看到你也我覺得特別親切,也許我們倆前世有緣分,你說呢?”
長途汽車中午到阿壩,我們在一起吃了一頓簡便的午飯。高原溫差巨大,她脫了厚僧衣,袒露右臂,披單搭到左肩,看上去健康、勻稱、獨立,令人仰慕。席間,她兀然離去,我去她離開的後門口張望,見到一副不真實的圖畫。
後門外的小路上,她和一位二三十歲的喇嘛正在說話,喇嘛打一頂紅傘,看上去不同尋常,他膚色白皙,莊嚴美好,安詳而沉靜。在炫目刺亮的正午的陽光下,他們的笑容絢爛美麗,宛如天人。
益西拉姆帶我去附近一座著名的寺廟,等在阿壩縣的柏油大路邊,兩輛三輪相繼而來,她牽起我的一隻手,笑盈盈回頭望了我一眼,與我上了前面的那輛三輪。她的笑容那麼美好,令我深深感動。
從寺院回來,我們進了一家茶館,要了一壺茶。我們用極小的碗碟喝著滾燙的大茶,她勸我第二年五月和她一起從觀音橋磕頭到拉薩。她說,她會武功,幾個人她完全能夠對付,沿途不用害怕。“如果你不能磕頭,”她說:“幫我推車也可以。”
她從口袋掏出幾百元,小聲問:“你身邊的錢夠不夠?我有。”她想給我錢,她的這一舉動讓我吃驚和感動,我連忙謝絕。世事無常,我不敢承諾,說,如果她準備加入她的拉薩之行,明年五月,我將會趕到瑪律康,和她相會。
益西拉姆搶著付了茶錢,我們手牽手走在大路上。一輛自行車從我們身邊飛騎而過,車上的喇嘛說她什麼,她立即反擊。
“喇嘛說什麼?”我有點猜出來。
“說我們。”她說。一定是說我們兩個女眾手牽手吧。
暮色降臨,分別的時刻已近。我拿出相機,給她照了幾張照片,益西拉姆擔心不能得到這些照片,拉著我到處找照相館。
“我想和你一起照一張相,”她說:“我可以在這裡取到。”但是,我們沒有找到照相館。
她赤腳穿一雙皮鞋,腳痛得一瘸一瘸,我堅持把她拉到一家鞋店,供養她一雙鞋。剛出鞋店,她飛快地奔過大街,一轉眼,她又穿過大街,回到我身邊,她手上那雙舊鞋不見了。
“我把鞋給了一個人。”她解釋道。
我們在阿壩的大街上流連。
“一想到馬上就要和你分開,”她對我說:“不知道今生還能不能見面,我的心都痛。你說,你們還會見面嗎?”
我不知道這一天發生了什麼,如此迅速,不可思議,我對她那麼眷戀,可她的話還是令我吃驚。
我們在一家小飯館坐下,希望還能擁有一段面對面的時光。
益西拉姆慢慢吃著面,說:“你和我一起磕頭到拉薩吧,然後,我們一起去印度,你就在印度出家。”
我不置可否。她沉吟:“你真的有出家的緣分!”
“什麼時候?”
益西拉姆說了一個時間,和學院空行母授記我出家的時間相同。
她似乎非常悲傷,低目,很長時間,她慢慢地對我說:
“如果你想我,你就到拉薩,到了拉薩,你就能見到我。”
“你在拉薩有聯繫地址嗎?”我有些驚訝地問。
她欲言又止,沒有說話。
她在路邊招手,一輛三輪車疾馳而來,她上了三輪,她的臉在暮色中白皙而迷蒙。她右手手心向上,向我致意。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種問候的方式,那麼優雅、高貴,令我砰然心動。三輪車載著她消失在漸深的暮色中。
我到了學院,立刻就出家了。益西拉姆曾經給我家中打過一個電話,我打回去時,是一個出家男眾的聲音。他聽到我的名字,非常歡喜,似乎他對我熟悉已久。
“我是益西拉姆的師父,”他說,“你等一會。她馬上過來。”
我眼前浮現那位在五臺山閉關二十年的穿百衲衣的出家人,懷疑我是否聽錯了。
益西拉姆接過電話,我告訴她我已經出家,她沒有絲毫驚奇。我說我不能和她磕長頭到拉薩了,我將留在學院學習。
她一時無聲。後來,她說話時,聲音很輕,非常失望。
我忘記了她說什麼,後來,我再也沒有找到她師父的那個電話號碼。
也許,有人能夠告訴我,為什麼我們會相逢?我橫穿整個國土,改變行程,在前往阿壩的途中,益西拉姆兩手空空,站在一望無際的公路上,向我坐的那輛車招手。
益西拉姆不住在拉薩,為什麼她說,只要想她,我就可以去拉薩,到了拉薩,我就能見到她?
她溫厚,寬和,如無所不包的天空,我多麼希望和她一起,沐浴在她無所不在的溫暖和慈愛的光輝裡。她光芒四射,莊嚴動人。她的面容和菩薩的雕像如此相象,可她是那麼真實,和她在一起時,我感到自由,生命充滿活力,仿佛大地與我同在,沒有懷疑。
也許,有一天,奇跡會再一次降臨。我們會穿過大地和人群,穿過無數世,再度相逢。她會牽上我的一隻手,笑吟吟回頭望我,和我一起坐上三輪。藏民到拉薩是為了朝覺臥佛,也許她就是覺臥佛,看見覺臥佛,我就看見了她。或者,她是觀世音菩薩,見到了布達拉宮,我就見到了她。
一位活佛看了我和圓空的合影,沉吟:
“她是你前世的上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