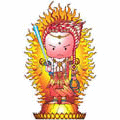為什麼我們現在很忙,或者你感覺到你很忙。你把你的生活、你每天的日程排得很滿,然後你被很多事情所纏繞、所追逐,好像有很多事在後面追趕你,一天到晚都很密集。我講的這個「忙」是時間安排上的,其實它也是一種心理感受上的。這種心理感受就是內心沒有閒,所以忙的反面就是閒。從現象上看,安排的事情、工作越多的人,他的心也會越忙。事情越少或者沒有事情的人,他的心就會很閒。
其實即便有時候你什麼事情都沒有,你的心仍然會很忙。如果我們在寺院裡打禪七或者念佛七時——打禪七就是在禪堂裡靜坐;打念佛七就是重複念一句「阿彌陀佛」——算是夠閒的,工作、生活、家庭都放下了,什麼事也沒有。但是在禪堂、念佛堂裡面,你的心是閒的嗎?剛到禪堂裡靜坐的人,他的心可忙了,可能比在外面奔波還忙。因為他心裡有很多的妄想、雜念,這就會讓他感到心很忙、心不閒、心不放鬆。但是,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往往我們在事務層面、現象層面很忙,同時我們的心也很忙,心也不能閒,乃至於很多人都習慣了一種生活狀態,把每天都排得滿滿的:上班排得很滿,在辦公室裡也要用電腦把那個空閒排滿;下班後還要安排聚會、吃飯,把時間排滿;週末也要排滿……似乎大家已經習慣了那種把一切排滿的狀態。所以很忙包括了外面的事情多,但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心理狀態。
我覺得在這種心理狀態的背後起碼存在兩個問題。有時候到柏林寺的人,我會勸他們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背會。《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只有260個字,是釋迦牟尼佛大智慧的濃縮。玄奘大師從中國走到印度,一路上遇到很多磨難,他就靠誦《心經》給自己輸入能量,戰勝外面的挑戰。所以我經常推薦人們把《心經》背會,背一遍只需要一分鐘。很多時候他們會跟我講:「師父啊,我很忙,我沒空。」我就跟他說:「假如現在有人把你關在一個房子裡,只有你把《心經》背會了才能放你出來,你保准有時間。」寺院有活動時,我們會邀請居士來參加,如果是在夏天,有的居士會說:「哎呀師父,今天特別熱,從北京開車到柏林寺很熱,高速公路地面很燙。」有時候我會跟他們講:「如果在柏林寺有一個商業洽談會,你到這裡來可能會簽一張1個億的單,那你很快就不覺得熱了。」所以在「很忙」的背後它有一個重要性的問題——就是在你的人生中,有很多事情,你要把它的重要性排出來。這是我要講的關於「忙」的第一個要點。
我們有沒有在心裡面排出這種重要性來?有的人沒有時間去看望父母、給父母打電話,他說他很忙;有的人沒有時間陪自己的子女共度一個週末,他說他很忙,沒有時間跟家人在一起。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在這些事情重要性的排序上,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個誤區。其實人生有一些事情是不能逆轉的。比如說在子女小的時候,你陪伴或者教育他們,用一些時間和他們共度週末;或者你去看望父母,跟他們一起吃飯。這樣一些事情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很重要的責任,而這些責任在人生的長河中不可逆。比如,你的孩子長到了20多歲,你再想帶他去兒童遊樂園,可能他就不會跟你去了;或者是當父母變老生病離開了我們後,你想再陪他一個晚上,也不再有機會了。當然,在我們的人生裡還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比如說鍛煉身體。像這些人生的基本責任,包括對家庭的、對親人的、也有對自己的,我覺得應該把它們往前排。
在「忙」這個問題的背後有一個價值觀,就是哪一些重要,哪一些不重要;哪一些有價值,哪一些沒價值。也許我們大家都覺得錢值錢,其實錢是最不值錢的。當你已經把你的身體透支了,用來去換很多錢,之後你想再用錢去買一個健康回來,也很難。有一個說法叫「先用身體換錢,再用錢換身體」。用身體換錢比較難,用錢換身體好像更難,不僅難而且痛苦。所以我們要在一些事情的排序上反思重要性。
重要性涉及到我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責任。我把它分成三種。第一種是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生物的人,是一個自然的人。作為一個自然人,我們有一個責任,我們要延續生命,要吃喝,要繁衍後代。我們也是一個社會人。社會人的責任往往是家庭責任、社會責任。家庭責任裡面,夫妻之間的責任,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子女對父母的責任。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我們也有對這個國家應該擔負的責任。我們納稅,我們勞動,我們參與,我們貢獻我們的意見和建議,這些都是社會責任。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還是宇宙人。宇宙人的責任就是我們生而為人,我們也要考慮這個生命最終極的意義是什麼,最高的價值是什麼。我們得到這樣一個人身,可以用它去擔負社會責任,也要用它去思考、去探索宇宙人生的奧妙。
佛法認為生命無始也無終。在無始無終的時間長河中,我們最高的價值是什麼?佛陀告訴我們,生命的最高價值就是覺悟。我的師父淨慧長老講了兩個詞:覺悟和奉獻。作為宇宙人的這種最高責任,其實跟我們作為自然人、作為社會人的責任是分不開的。在這個層面上就涉及到了信仰,涉及到了我們要思考人生的最高價值。過去我們上學的時候會問家長:「為什麼我要上小學?」父母說:「為了上中學。」後來上中學,我們再問父母:「為什麼要上中學?」父母說:「為了上大學。」到了大學,我們問:「為什麼要上大學?」我們問自己,也問別人。為了要畢業,最後找一個工作。等畢業有了工作,你可能還會問自己:「我這麼忙,這是為什麼?」你會有很多回答。但是你也會發現,這樣一種追問沒有窮盡。最終是為了什麼?這就是生命的意義、生命的價值。你發現你會碰到一個死角:最終這個意義和價值從哪裡來?這就是宗教要解決的問題。不同的宗教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解答。
有的宗教把人生最高的價值和意義賦予一個超越的神——認為由於他的存在一切才有意義。如果跟他把關係搞好,供養他,令他歡喜,甚至把生命奉獻給他,才有價值。乃至於有可能走到極端:認為自己是以他的名義在做這件事,做那件事,甚至做傷害別人的事。佛教不這麼認為,佛教主張生命最終的價值和意義並不來自於外面有一個超越的、主宰我們命運的神。佛教認為:生命最終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在外面,而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也許你會問:「每個人的內心是什麼?我的內心現在只有貪嗔癡,有很多煩惱。」
佛已經告訴了我們一個答案。如果你肯信,你能接受,你在生活中去體驗它,你生命的一切也就有了意義,有了一個最終的、最直接的意義。佛告訴我們的答案就是:所有眾生的心本來都是覺悟的,所有眾生的心本來都是佛。佛就是覺悟,圓滿的覺悟。而我們現在的煩惱,也是那個我們本來就有的那種覺悟能力的一種表現。也正是因為我們沒有認知到我們本有的那種覺悟能力,我們才會把我們的心跟生活、跟工作、跟外面的事情的主客關係搞顛倒。這就是我講的關於「忙」的第二個要點。
「忙」的第二個要點還涉及到我們的主客關係:我們的心在我們所忙的事情裡面是否居於主導,也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在自覺自願的忙。自覺自願的忙和被動的忙是兩種不同的忙。自覺自願的忙可能忙中有閒。我以前看毛主席的詩,有一句叫「山舞銀蛇,原馳蠟象。」他描寫紅軍長征所經過地方的景色之優美。大家可以想像,在那樣一種戎馬生涯中,他的內心如果沒有這個閒,是沒有心思注意到他所路經的這些自然美景的。他能看到,他能欣賞,說明他的心很閒。可見,忙和閒是相對的。如果你的心是主導的,你是自覺自願的,你可以很忙。這個居於主導有不同的層次。
每時每刻我們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境界,在各種外面的境界跟前,關鍵是你的心是不是主導的,是不是自在的,是不是覺的——就是清醒的。所以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很忙,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忙,找不到價值感。我們老是覺得很欠缺,要用很多東西把自己填滿,把的心填滿,把我們的擁有填滿。我們有了房子還要有汽車,還要有這個那個。由於我們不斷地要用這些東西填滿自己,卻又不知道為什麼,所以這種忙就顯得沒有意義。
我們概括一下關於忙的問題。忙從根本上來說涉及到價值。要把你的人生做一個價值的排序。在這些排序裡,我們要想辦法解決那個很根本的價值問題——為什麼。這個「為什麼」就是意義。怎麼解決這個「為什麼」,讓它有意義呢?可以通過信仰。信仰有很多種,像佛教的信仰就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關於價值、意義的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儒家也能對我們有所幫助,特別是宋朝以後的儒家思想,它能説明我們認識我們的心,認識我們內心本有的那種能力:良知良能。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裡所有的忙碌,都能與這個良知良能相適應——順著我們的良知良能,符合我們的良知良能。那麼所有我們忙的事情就會有了意義和價值。
在今天這個時代,你想完全不忙外面的事,恐怕很難,包括我們出家人也是如此。中國古代是個小農經濟時代,很多出家人在山裡住,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在山裡住的出家人的那種閒。我記得有一個住在山裡的出家人寫了這樣一首詩: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意思是:「到頭這個白雲也不比自己閒,雲它忙啊風把雲捲走了嘛。」這個和尚,他在山上只有一間破屋子,他沒有汽車,沒有電腦,也不可以上網,更沒有不斷地用很多東西把自己的時間填充,把感官佔據。但是通過這首詩,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對自己的那種生活狀態感到很滿意、很愜意。如果沒有這種滿意,沒有這種愜意,他寫不出這首詩。他對他的狀態很欣賞,這就是我講的閒。這說明我們要讓自己感覺到有意義,不一定非要佔有很多東西,也不一定非要忙很多事情。有一種狀態叫「工作狂」,我覺得這種工作狂狀態的背後是一種價值的空虛感。他要不斷地用各種各樣的事情把自己的時間填滿,來找到一種意義。有時候似乎跟別人說自己很忙,心裡才安穩。這就要反省了。
剛才講到的那個和尚,他在山裡面只有一間破屋子,他的意義是從哪裡來?說明他的意義不是從外面來,而是從內心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一個心。當我們把自己內心的這種滿足感、這種自在開發出來時,你的心是主人,你吃山珍海味香,你吃菜根也會香;你佔有很多的房子很滿意,你住一個很小的房子你會滿意。因此,我們日常生活中要知道重要性,而重要性就是一個價值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一方面在事情中忙,一方面要在忙中不斷地發現我們內心的那個意義。
累往往是指的身體,跟心理也分不開。我們出家人也很累。大家可能會奇怪:我們在家人累可以理解,每天都在為自己的生計,為自己的事業在那裡忙,在那裡累;你們出家人都出家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怎麼也會累呢?這裡面是有區別有學問的。有的時候我們雖然累,但是很充實,儘管累,但覺得有意義。所以有一種說法叫「累並快樂著」。我覺得真正讓我們感到有壓力的累是不知道為什麼累,或者說,很多時候是由於不知道為了什麼,而讓變得更累。我們的累有時候是累上加累。事情多,已經有壓力,那是累。我們還會經常跟別人說或者自己暗示自己「我很累」,這又增加了一重累。再者,由於我們內心沒有那種意義,體會不到我們累的這個事情的價值,那麼累又會加倍。
我們現在來觀察一下我們的累是為了什麼。我有接觸並觀察很多為社會奉獻的人,比如那些慈善家、那些高僧大德。前不久星雲大師到保定來,我聽了他老人家開示。他歲數那麼大,還忙了一上午,下午又在這裡講課,但他顯得還是非常自在,我們聽的人也很法喜。大師講完到後面休息時我去看他。一見便知道他在臺上講的時候是鼓著勁兒的,到了後面他把鼓著的勁兒松了下來,就顯得非常疲倦了。像星雲大師這樣的高僧大德,他們很忙也很累,以前我的師父也是這樣,但是為什麼他們能夠一直堅持,甚至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呢?這就是剛才我講的那個問題,有很多事情你累著,但你並沒有在裡面找到快樂;而這些高僧大德,包括那些為社會奉獻的人,他們找到了。
在座的諸位在生活中或許也有這樣的體驗:你很累,但是你很開心。有的母親為了子女能上學,省吃儉用,很勞累,但是她很開心。所以不管是為別人奉獻的人,還是只為自己的人,都會累,但這兩種累是不一樣的。當我們的累有利他的因素在裡面,或者就是完全為了利他的時候,這個累就不累了。這就是我理解的「累並快樂著」。
我們人的一生,百年三萬六千日,其實都在忙碌中,都在累中。怎麼樣讓我們的累有意義,讓我們的累在我們內心產生安樂、產生喜悅,這是一個大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答案,釋迦牟尼佛已經告訴了我們。他說:所有的痛苦都來自於要給自己帶來快樂,所有的快樂都來自於要給別人帶來快樂。我們把這個答案濃縮一下,就是我們要讓我們的累是利他的——利益他人的,利益社會的,對別人有意義的。我們的忙累如果有這樣一個意義,你的主觀、你的客觀都是為了要給別人帶來快樂,結果就是你自己會更快樂!這是一個辯證法:你越在乎自己的快樂,越是想為自己的快樂去忙去累,結果很有可能你越不快樂;你為了給別人帶來快樂,為了幫助別人,為了利他,你發現你自己會越來越快樂,你得到的快樂也許比別人還更大。這是一個人生觀的問題——我們整個的人生要建立在一個怎樣的基石上。
大乘佛法的人生觀,概括地說就是自利利他。你們也許聽說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句話,但是在佛教裡,剛開始並不這麼說,而是自利利他——給自己帶來利益,給別人帶來利益,在利他中自利。當我們的境界到達一定高度的時候才有可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自然,那個時候的利他就是利己。佛門中有位高僧叫本煥長老,他生前經常講這樣一句話:「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我每次見到本老的時候,感覺他都是歡天喜地的。他這兩句話的背後有一個秘訣就是:他說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眾生也因為他而離苦了;他不為自己求安樂,結果他最安樂。這個辯證法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你直接為了自己去求,往往自己什麼都得不到;你把自己無私地奉獻給別人,你反倒會有安樂。所以在佛法的修行裡面,六度的第一度就是佈施。佈施就是放下,就是要舍,有舍才有得。我們都希望自己很有福報。福報是什麼?福報就是心量。福報就像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就像一個容器,我們能倒出多少就能裝進多少。如果我們的心像虛空一樣,能把整個世界都倒出來(倒出來就是放下),實際上我們什麼都不會失去。
因此,在「累」之中,我們也要時常檢查一下我們的人生觀。損人利己的事不要做,最起碼也要利己不損人。如果能做到利己又利人,真正對自己有好處,對別人也會有好處就最好了,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人。
累往往是因為煩而來的,煩也會因為累而變得嚴重。如果一個人很忙、很累,但是他自己覺得有意義,一般來說他的身心健康是不會出問題的,除非他超出了自己身體的生理極限。最容易出問題的往往是:你很忙,你很累,你又很煩。我相信累是累不死人的,但是我相信煩能把人煩死,所以我們會經常聽人說「煩死人」。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得癌症。醫學家告訴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癌細胞。癌細胞有很多成因,食物的原因,環境污染的原因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原因都不一定會導致癌腫瘤。癌細胞的因數要聚集成一個能量體,與我們身體其他細胞之間的關係發生顛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內在的免疫力,而這個內在免疫力是跟我們的心態直接掛鉤的。如果你經常灰心、壓抑、焦慮,或者長時間處在鬱悶、憤怒等負面情緒下(也就是我們說的煩),我們身體中那些癌的因數就容易發生突變。所以,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