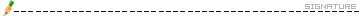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初,明代宗朱祁鈺病重不起。而朝中皇儲位置尚且懸空,究竟該立何人為新帝,皇帝朱祁鈺和帝國首席重臣、兵部尚書于謙,在皇統繼承問題上各有主張,分歧甚大。
這對曾經彼此知心、配合默契,令大明帝國度過建立百年來最大一次危機的君臣,此時已經是貌合神離。
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朱祁鎮被俘虜,京師三大營損失過半,瓦剌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皇長子朱見深尚在襁褓,而且並非正式冊立的皇太子,一個嬰兒根本沒有辦法去凝聚危城人心。
年輕的監國親王、皇弟朱祁鈺手足無措,孫太后病急亂投醫,在國難時一片迎立賢王聲音中,打算迎立「諸王中最長且賢,眾望頗屬」的皇叔、襄王朱瞻墡。
此時,是于謙力主的「立朱祁鈺為帝,朱見深為太子」之議,既符合國難立長君的現實需求,又最大限度保證了朱祁鎮、朱祁鈺兄弟的父親明宣宗朱瞻基一系的權益,使帝位不致落入旁支,對得起明宣宗當年對於謙的君臣之遇。
否則襄王朱瞻墡有多名成年子孫,他若得立,則帝系轉移變成定局。豈料這令此時淪為瓦剌俘虜的明英宗朱祁鎮懷恨在心,認定是于謙勾結明代宗朱祁鈺謀奪了他的皇位,並最終導致了于謙奪門之變後的遇害。
其後,瓦剌首領也先以朱祁鎮為人質,屢屢要挾明廷,于謙堅決主張社稷為重,嚴詞拒絕一切寇虜妄求,才令也先手中人質失去利用價值。同時又是于謙苦口婆心勸說現任皇帝朱祁鈺「天命已定」,打消其疑慮。朱祁鎮因而得還,不用在漠北吃沙子到死。
【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
于謙為何既擁立明代宗為帝,又力主迎回英宗?正如數百年前的南宋岳飛舊事。
岳飛之所以干冒武臣涉政之忌,上書宋高宗趙構求儘快立儲,正是針對金國欲立宋欽宗之太子趙諶為傀儡的圖謀。
趙諶雖曾是大宋帝國正式冊立的皇太子,本身也並無什麼罪過,但經歷「靖康之變」後,在包括岳飛在內的南宋文武重臣心裡,他就只是個辱宗廟罪人之子,絕不當立,亦不承認他是帝國皇儲,因此只以「丙午元子」稱之。
【近諜報,虜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謀沮矣。】——張戒《默記》
甚至對宋欽宗,岳飛隨著政治上的成熟,也從早年的「迎回二聖」,改口為「迎回天眷」,只認可他是現任皇帝的親屬,身陷虜庭是國家恥辱,理應救回,而絕不認可這種辱國罪人是值得尊敬的先帝。
因此,當瓦剌人被迫送還朱祁鎮時,大臣商輅希望朱祁鈺在皇帝正殿文華殿賜宴,以示皇帝和上皇兩宮同心,彼此無間。朱祁鈺大怒,認為此言等同於逼他馬上讓位,憤然道「我不曾要做皇帝,你們眾人勸我做,如今又要怎麼?」
大將石亨一直包藏禍心,慫恿朱祁鈺索性大開殺戒,又是于謙一句「大事已定,但要事體得宜」,暫時安了朱祁鈺之心,安了滿朝百官之心。
【鑾輿既還,護送虜使同至,眾議先一日於奉天門賜宴,次日就南內賜宴。公曰:「虜人此舉實仗大義,若令進南內宴,彼見另居一處,未免退有後言。不若兩宴俱就文華殿,示以彼此無間之意,庶可服其心。」太監興安以聞。景廟大怒,急詔公等赴文華殿,面詰曰「我不曾要做皇帝,眾人勸我做,如今又要怎麼?」眾皆不知,俱不敢言。石亨曰:「有什麼說話的,碎碎砍了他。」於公謙曰:「大事已定,便有一言半語俱不必聽,但要事體得宜便是。」】——《商文毅公言行錄》
表面上,整個景泰年間,朱祁鈺對於謙是言聽計從,極為禮敬,屢加封賞,多次探視,遠遠超出了一個皇帝對臣子的限度。而景泰初年的朝政大事,也都由於謙一言裁決,名為兵部尚書,實為帝國的實際首相。
兩人最值得稱道的一段佳話,是御醫給於謙困擾已久的痰疾開了方子,說要用竹瀝(竹子經火烤後所流出的液汁)做藥引子。當時北方地區竹林很少,竹瀝不易取得。朱祁鈺便帶著隨從到到萬歲山,親手為于謙伐竹取瀝。
【素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制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明史·于謙傳》
然而,身為一名專制帝王,身為朱元璋的子孫,秉承了歷代大明皇帝的雄猜本性,朱祁鈺也不可避免地對於謙有所猜忌和牽制。
當政敵上書彈劾于謙恃權結黨、舉薦私人時,朱祁鈺一方面稱「于謙專兵政,舉人亦其所宜也」,另一方面又不免敲打于謙「已往者置不問;今後如假公營私,必罪以祖宗成憲,不宥」。
對公而忘私、日夜辛勞只為國憂的于謙而言,這種敲打不啻於人格污辱了。
于謙奏請裁革太監監軍之制,朱祁鈺不允,命內臣監軍如故。石亨、羅通等將領心胸狹隘,嫉恨于謙的威望和大功,屢番詆毀於謙,朱祁鈺卻不顧于謙反對,將他們委以重用,參贊軍權,其目的很明顯,就是用來牽制于謙。
最後石亨等發動「奪門之變」,迎朱祁鎮復位,於朱祁鈺而言,誤信小人,身死位廢,也是自作自受了。
「奪門之變」時,于謙作為景泰一朝的實際執政者,手握中樞內外大權,當真要阻止本是輕而易舉。但他卻沒有任何自保舉動,正是為了帝國社稷,大明江山。
朱祁鈺病重不起,其太子朱見濟已死,卻為了自己面子,不願復立朱見深為太子。
朱祁鈺身邊那幫當年力主廢立的近臣,生怕朱見深繼位後會反攻倒算,謀劃著另外迎立藩王,選中的還是那位素有賢名的皇叔襄王,此議被于謙堅決抵制。
于謙和商輅等內閣重臣商議,由商輅援筆《復儲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而當時宣宗子裔,僅剩包括後來的明憲宗朱見深在內的,朱祁鎮的幾個兒子。
朱祁鈺願意接受此奏議,復立朱見深固然好。否則等他歸天,群臣只需上書孫太后,讓朱見深以血緣最親近、年齡最長的皇侄身份繼位亦可。
【十六日擬寫二本,伏闕投進,本稿系臣在禮部朝房內寫,主事俞欽抄謄。本內有云: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助理庶政等語。姚夔、鄒乾等皆稱善。因寫二本,大小官員僉名數多,封進不及。】——《商文毅公文集》
然而如果朱祁鈺復立朱見深為儲;或是朱祁鈺死後,朱見深正常即位;雖然是最符合朝局穩定,社稷安寧的大局,卻絕不符合朝中那些權奸宵小、如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人利益。
他們謀劃奪門,不止是為撈取迎立之功,亦是因他們深恨的于謙在朝中主持中樞,他們就沒辦法為所欲為,得到朝中大權。
而對於謙這樣望重天下的社稷大功臣,想要致他於死地,就必須換上一個對於謙有深怨而銜恨的皇帝,並栽贓以謀反罪名。所以前太子朱見深不行,非太上皇朱祁鎮不可。
就在《復儲疏》呈於禮部,還未上報給朱祁鈺的當夜,石亨徐有貞曹吉祥們聽聞風聲,迫不及待聯合朱祁鎮,發動了 「奪門之變」。
于謙同樣已發現奪門一黨的串聯端倪,以他當時如日中天的威望、掌管軍政的權柄,若登高一呼,撲滅此亂本是輕而易舉。但如此一來,朱祁鎮這個謀逆罪人或死,或廢為庶人;
而包括朱見深在內的所有朱祁鎮子孫,都同樣將作為罪人之子,宣宗朱瞻基一脈將永遠失去皇位繼承權。而代宗朱祁鈺已然不治垂死,迎立其他藩王,必致國勢動盪。
為了大明社稷的穩定,為了回報當年宣宗的知遇之恩,于謙最終選擇了犧牲自己,按兵不動……
【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公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
病重的朱祁鈺以己度人,是萬萬想不到于謙這般幾近聖賢的高尚節操的。他聽聞變起,第一反應是「于謙耶」,生怕于謙要學王莽司馬懿,奪大明江山,自己從此成為朱氏皇族末代國君、千古罪人;
等聽說是朱祁鎮政變復位,方長舒一口氣「哥哥做,好!好!」。他被廢去帝號,繼續躺了一個月後,不明不白死去,明人筆記里說,是被明英宗派太監蔣安,用布帛勒死。
明英宗朱祁鎮,和奪門一黨達成骯髒的政治默契:一方得皇位;一方得朝權、殺于謙。
因此朱祁鎮復辟後,迫不及待將于謙及許多景泰重臣下獄。其謀害於謙聖旨曰:
「于謙……這廝每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石亨)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搖動宗社……欽此」
商輅原系朱祁鎮東宮舊臣,本不在逮捕之列,朱祁鎮還讓他給自己起草復位詔書。可商輅為于謙力辯絕無迎立外藩事,舉此時仍在禮部的《復儲疏》為證據。
豈不知朱祁鎮對此本就心知肚明,為了完成與奪門一黨的約定、為了讓這場政變變得師出有名,他才非殺于謙不可;是以索性將商輅也下了獄,其後從寬改罷官歸鄉,終其在位之日,不復召還。
是以,《明史》和通俗讀物《明朝那些事》中「朱祁鎮受徐有貞、石亨矇騙,才害死於謙,事後悔悟」一說,何其荒謬?不過是後來的明憲宗給於謙平反時,為其生父遮醜諱過,才做的官樣文章。
本質上,朱祁鎮就是殺害於謙的頭號罪魁禍首,罪證確鑿,不容抵賴。
于謙家產下令被抄沒,家無餘資,只有正屋裡緊鎖著朱祁鈺賜給的蟒袍、劍器等物。當日,血不曾冷,風孰與高,天下冤之……
【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或言寵謙太過,興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及籍沒,家無餘資,獨正室鐍鑰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明史·于謙傳》
又過了許多年,憲宗朱見深在位期間,不但給於謙平反昭雪,並在此時被召還為內閣首輔的商輅力主下,追復朱祁鈺「恭仁康定景皇帝」帝號,並以帝皇之禮重修其陵寢。
平心而論,朱祁鈺雖然本身能力有限,性格上也頗有心胸狹隘和優柔寡斷的弱點,但能以朝政大局為重,絕大部分時候都對於謙充分信任,鼎力支持,已經算是個相當不錯的皇帝了。
明朝能安然度過「土木堡之變」的危機,集合一群殘兵敗將,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除于謙是護國功臣、中流砥柱外,朱祁鈺作為患難天子,也同樣功不可沒。
只是汲汲於一己之利、一家一姓之私的朱祁鈺,始終難以真正理解于謙的高尚人格和偉大襟懷。
于謙和岳飛這對「西湖雙忠」,皆是以「社稷為重君為輕」為信念的華夏社稷之臣,他們真正忠心的從不是某家某姓皇帝,而是整個華夏文明和億兆蒼生。也真因如此,方值得我輩後人,永世敬仰。
西湖于謙墓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