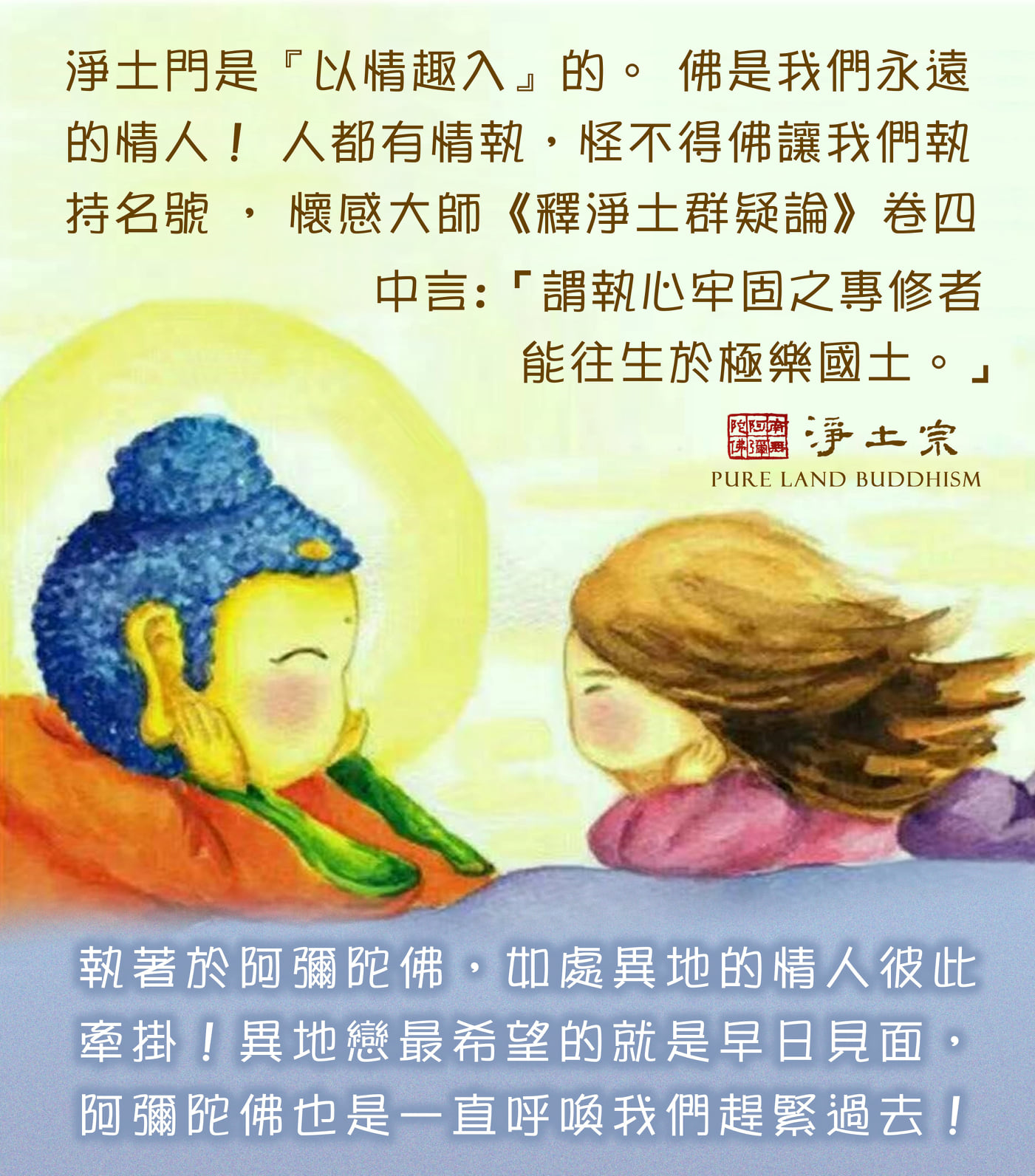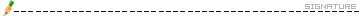2019-12-05 06:54聯合報 林谷芳
人生苦短,所以我很少談自己的過去;成就不大,更就不須談自己的過去。不過,看到許多朋友在報上寫「我的五○年代」、「我的六○年代」,還是覺得滿有價值的。
小有江湖情懷,所以也當風凜立。
滿有價值,一是因為這些朋友都乃濟濟英才,他們的生命歷程固奪人眼目,更可為世人榜樣。但滿有價值,更在於這時代變化太快,屬於那純樸靜態年代中的種種,就像一面鏡子,正好讓我們照見自己。當然,人人都有年少,寫年少就回到那生命的輕狂純直,讀者由此再來看今天的文章主人,其中就能有生命最可貴、最真純的連接。
也就是這樣,看著看著,我竟動起了寫的念頭。
寫,是被撩起的。但撩起是緣,緣之前總得有個因。真寫,就要給人有另一向度的觸發,而非僅是自己情懷牢騷的吐露。
這因,是我與這些菁英走了完全不同的路。而這路,雖是個人的緣分與選擇,但也映照著那時代台灣某些隱微,但深具吸引力,且有一定意義的塊面。談台灣的過去如漏了這一塊,看到的,也可能就只限於經濟發展與人文追求這人盡皆知的一面。
五、六○年代是個怎樣的年代?國府遷台,最初百廢待舉,正一片孤臣孽子之心;但及至稍有安定,也就思及發展。六○年代就是這樣的年代,稍稍站穩了腳步,人就有了更多的想像。
但說想像,當時畢竟仍是相對封閉的社會,所以想像也很單純:鄉下人知道到城市就有發展;南部人知道到北部就有發展;在國內的知道到海外就有發展。五○年代末、六○年代初的歌曲已逐漸擺脫了早年〈港都夜曲〉似的悲情,更多是到都市打拚的心聲。一般民眾如此,對知識分子,則一句「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就說明了一切。
當時台灣剛脫離一窮二白,經濟還沒真正起飛,但出國留學風氣之盛,卻就是如今難以企及的。我一九七二年大學畢業,隨即至陸軍步校受訓半年,但不到一個月,就已有好幾位同學寫了文藝腔的明信片過來:林谷芳,當你收到這信時,我已在飛往美國的太平洋上空,祝軍旅生活順利愉快!
接到這種信,真是百味雜陳。當時雖已不那麼強調反攻大陸,但兩岸關係依舊嚴峻緊張。步校結訓後會有三分之一的人抽到「金馬獎」,中獎者也多霎時臉色蒼白。而平時訓練哪有含糊的!拳打腳踢雖已少見,但天天給你出戰鬥操、洗戰鬥澡,體能心力都處在緊張壓抑的狀態。讀這文藝腔的信,難免會想:幹嘛就我要保家衛國,妳就去追求美好的前程!
當然,追求美好前程是生命的權利,男女狀況情形固不同,思路卻還是一條線的。因此,絕大多數須花二到三年保家衛國的菁英,待得退伍,一樣也迫不及待地搭上穿越太平洋的飛機,追尋他們的美好前程去了。
正是這樣,五○、六○年代的菁英,絕大多數是留洋的;少數沒留洋的,基本也是從南部到北部。這是當時的氛圍。而也正是這樣一條線,開啟了七○年代一堆秀異分子的回歸與集結,從而創造了台灣之後的黃金年代。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1966年台北外雙溪:武俠、修道對許多人只是小說,但對林谷芳,卻是生命中的實然,所以與同伴會有這樣的畫面。
相比於從南部到北部、台灣到美國的這些菁英,我則不同:生在北部,又不留洋。而會如此,固因於自己的生命情性,也因於當時的某些社會條件,讓我能有不同於其他人的生涯出現。
這條件不是屬於世間法的。國府遷台,傳統各大宗教與明清時期出現的本土宗教的宗長都到了台灣。這些人來台,有些固跟國府素有因緣,但幾乎全數而來,則因為他們擔心政權易幟後教派就在大陸消亡。而事後也證明這憂慮是對的。在「破四舊」中,宗教基本不能倖免,更不要說後來更激烈的文革。
就因有這種存亡絕續的危機感,所以他們不僅渡海來台,更就在那一窮二白、物資艱困的五○年代初期,就將自己教派的經典盡皆印刷成書;有些甚且就免費流通,希望更多人得以親近,以續命脈。
那時,比較有規模且公開發行這些宗教——尤其是實修書籍的出版社,有真善美出版社與自由出版社,所出的道書、佛書,主要是原典,如《伍柳仙宗全集》、《景德傳燈錄》等,不僅佛道皆攝,還夾雜一些「五術」:山、醫、命、卜、相之書。
而除了宗長與經書外,更直接的是:大陸各地的修行人也匯聚到了台灣。
這些教派、經典、行者,與一般大眾生活無關,但如果你醉心於修行,那就是個千載難逢、不可再遇的時代。
五○年代末、六○年代初,我年紀尚小,按理說,不該與這些有任何接觸,但正如佛法常說的夙世因緣,我「六歲有感於死生」,於是就接續上了這些生命。
六歲那年,有天與一群同伴在稻埕上玩,旁邊小屋外、長板凳上就躺著一個中年男性,往前一看,只見他嘴巴微張、舌頭微吐的僵直在那,其他同伴繼續高興地玩著,但看到這景象,我心情卻蒙上了一層陰影,再無玩興,就獨自沉重地走回了家。
那段路,記憶中好長,像走了一下午般。在十六年後我再次回到那裡,才發覺它只有短短七十公尺左右。而會有這樣不成比例的印象,就可見當時心情的沉重。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死」,在小孩子身上從概念到形象都是模糊的,他分不清離開與消逝、不動與死亡的不同。但就在當下,我竟直接感受到死亡意味著幻滅。沉重的心情在六歲小孩只是一種難以言說的「莫名」狀態;到大,才知真要描述,就只能用這話來形容:「死若烏有,生又何歡?」
的確,死如果是一切都化為泡影,眼前擁有的既必然指向此處,那生又有何歡呢?正是這樣的心情,從小,當大家在那「反攻復國」的年代都崇拜民族英雄時,我的英雄卻就是《西遊記》裡的孫悟空。
小孩子都喜歡孫悟空,喜歡他的神變、他的猴頭猴腦,但他對我最大的吸引,是他的「不死身」。天兵天將砍他不死,老君用爐火煉他不死。即便被佛祖壓在五行山下,吃的是鐵丸銅湯,五百年後從山底躍出,也仍舊是觔斗雲一翻就十萬里的齊天大聖。
畏懼死亡,讓我最初欽羨孫悟空;而在稍長後,也就醉心於「長生久視之術」。因著修真書的出版,小學六年級我自己就看書盲修瞎煉的煉一些道術。
說是「術」,的確!就是「術」。那時哪曉得背後還有究竟的性命大道,一心就想煉成超人。當時房居都還粗陋,洗澡,就在屋後搭個木棚,用炭燒水倒到大鋁盆裡,人就蹲在鋁盆外洗。我每次洗都要費時甚久,家人以為我特愛乾淨。其實,我是在棚內用線綁了一個小小的棉球,冷水沖澡後,就赤裸地蹲在鋁盆旁,作「念力」練習,要用念力讓那棉球動起來。
信不信由你,基本它還真動了起來。是不是「念力」不知,但確定不是風吹的!這點修行的「如實」我從小就有,要真修得不死,一點都欺瞞自己不得。而也正是這徹底的如實,才讓我之後走入了「兩刃相交,無以躲閃」的禪家修行。
盲修瞎煉遇到瓶頸,就翻書找答案,但書中的答案卻常彼此不同。因此只能找活生生的修行人來問,就這樣開始了我的「訪道」生涯。
上初中,開始打聽哪裡有高人、哪裡有真功夫。但當時的機緣不算殊勝,許多時候就是道聽塗說地在公園裡聽教拳、練氣功的扯。而到了高中,機緣就來了。
機緣來,一是因年紀較成熟,門路摸清了些;二來,更直接的,是讀了建國中學。
談到建中,這被許多人認為台灣最好的男子高中,一般人想到的,也就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秀異青年。的確,當時的建中,大家唱的是洋歌,對傳統東西總覺得老土。年少輕狂,更就以鄙夷的行動直接表達自己就是跟腐朽不同掛的。
我高一時參加國樂社,國樂社當時的水平當然不高,但校慶時,各社團總有掌聲,可只要司儀一報「國樂社演出」,頓時就滿場噓聲。一首江南絲竹〈歡樂歌〉四分多鐘,滿滿的噓聲就從沒斷過。還記得樂曲要開始時,笛子主奏的同學問我怎麼辦,年少自負的我只回答了一句:「莊嚴地奏完它!」。這經歷基本上是六○年代許多菁英不曾遇過的。而我後來有段戮力於傳統文化的生涯——尤其對中國音樂美學的建構,就與這經驗有直接關聯,裡面也不免有著「孤臣孽子之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