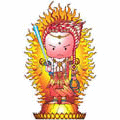唯有德的人,才能有福。當人類的平均壽命減少後,一切都隨之減少。當道德日趨墮落時,人類的福報也逐漸減損了。
簡單地說,像七寶逐漸隱沒,五谷逐漸欠收,衣食逐漸艱難,容貌逐漸丑陋,資賦逐漸昏愚,精神逐漸衰弱,風俗逐漸驕慢,六親逐漸不和,賦稅(或工作)逐漸繁重,水災、火災、盜賊、暴力及色情逐漸猖獗,宗教和佛法逐漸凋零,善人逐漸減少,真正飽學的儒士逐漸稀少,謗佛的人逐漸受到推崇,富人逐漸低俗而且吝啬。
世俗的文章,有時會不准確或不靈驗,但如果出自內典(佛經),則字字有根據。
夏朝、商朝和周朝三個朝代,都使用黃金和白璧(玉),動則以多少萬镒(一镒為二十四兩)和百雙來做計算單位,未嘗純用白金。到了漢朝,才參用白金。許多小國都有夜光的璧玉和照乘的寶珠,不像現在那麼罕見。明清時代鑄造錢幣和器皿采用較低品質的銀(低銀),就是將赤銅參雜在銀裡,這表示銀已經不足夠了,到後來,便又完全改用銅錢,這難道不是七寶逐漸隱沒的征兆嗎?
古人所說的「百金」,就是一百錠金子,每一錠金子有五兩或十兩重,宛如現代人所說的「條塊」。漢文帝說:「平均十戶人家便有一百錠金子。」蘇子說:「興兵十萬,每天要花費一千錠金子。」如果一錠金子,只有一兩重,則漢代一般家庭只有十兩金子,而每一位士兵的飲食、刀械、器物,每天只用了一分銀子,有這個道理嗎?(《陰骘文廣義節錄》上卷第四十二頁)
周朝的一百畝田地相當於清朝的二十二畝,這二十二畝土地的收成,足可供給九位粗壯的農夫食用。古人每一餐飯必定吃了一斗米,一個人整年所吃的米糧,約等於(清朝)七十幾石。九個人應當有六百五十石左右,這表示每一畝田地可以收獲三十石。我小時候的所見所聞,我們家鄉每畝田地可收脫粟三、四石。從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以後,從前每畝能收三石多的田地,都收獲不到三石,這不表示五谷逐漸欠收嗎?
明穆宗隆慶末年及明神宗萬歷年間,有人重修昆山的薦嚴禅寺,取出瓦間所填塞的稻束,好像是隋唐的故物,它的稻穗長達一尺多,估計當時的收獲量,每畝田地,必能收獲十余石,現在稻穗的長度已不滿四寸。
(注)經濟學上的「土地報酬遞減定律」說:土地會因為不斷地耕種,而產生養分減少、收獲量遞減的現象。
古代的國家沒有十年的積蓄,叫做「不足」。沒有六年的積蓄,叫做「急」。漢朝和唐朝的極盛時期,還能夠跟古代的「不足」相比。現在縱使想求「急」,也已經辦不到了,這不是衣食艱難的征兆嗎?
古代的王公貴族,不恥下交住在巖穴的野人和隱士;縱使地位像卿相那麼崇高,亦不畏辛勞,非必要不乘坐馬車;現在有許多新官一上任,便藐視故友,收受賄賂,仗勢欺人,而且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這不表示風俗驕慢嗎?
古代的高僧遇見天子不必報名,皇帝下诏書給出家師父一定稱呼對方為「師」。唐太宗為三藏聖教寫序,極為尊敬和推崇,玄奘法師圓寂,唐高宗告訴左右大臣說:「朕失去國寶了!」而且還罷朝五日,以示哀悼。(詳見《高僧傳》)景龍二年,中宗皇帝敕高安令崔思亮,迎接僧伽大師至京城,皇上及文武百官都自稱「弟子」。(詳見《金湯篇》及《佛祖統紀》)
宋朝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興隆大法,他們有時親自駕臨寺院,有時請僧侶到宮中說法,現在的官吏和士人倨傲,時常有看見佛像不參拜,遇到高僧沒有禮貌的現象,這豈不是佛法凋零的明證嗎?
孔子和顏子建立儒家的義理,只貴身體力行,而不尚言說,厚於自治,而薄責於人。孟子批評楊朱和墨子,是出於萬不得已;譬如大黃和巴豆,良醫偶而用它,並非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現今有些人,只撿拾幾句來毀謗佛法,便說自己是程子和朱熹再世。那些謗佛的人,有著一種誇張自大的習氣,講不了幾句,便排斥別人的說法,而堅持自己的見解才是絕對真理,這不是真儒稀少的征驗嗎?(《陰骘文廣義節錄》上卷第四十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