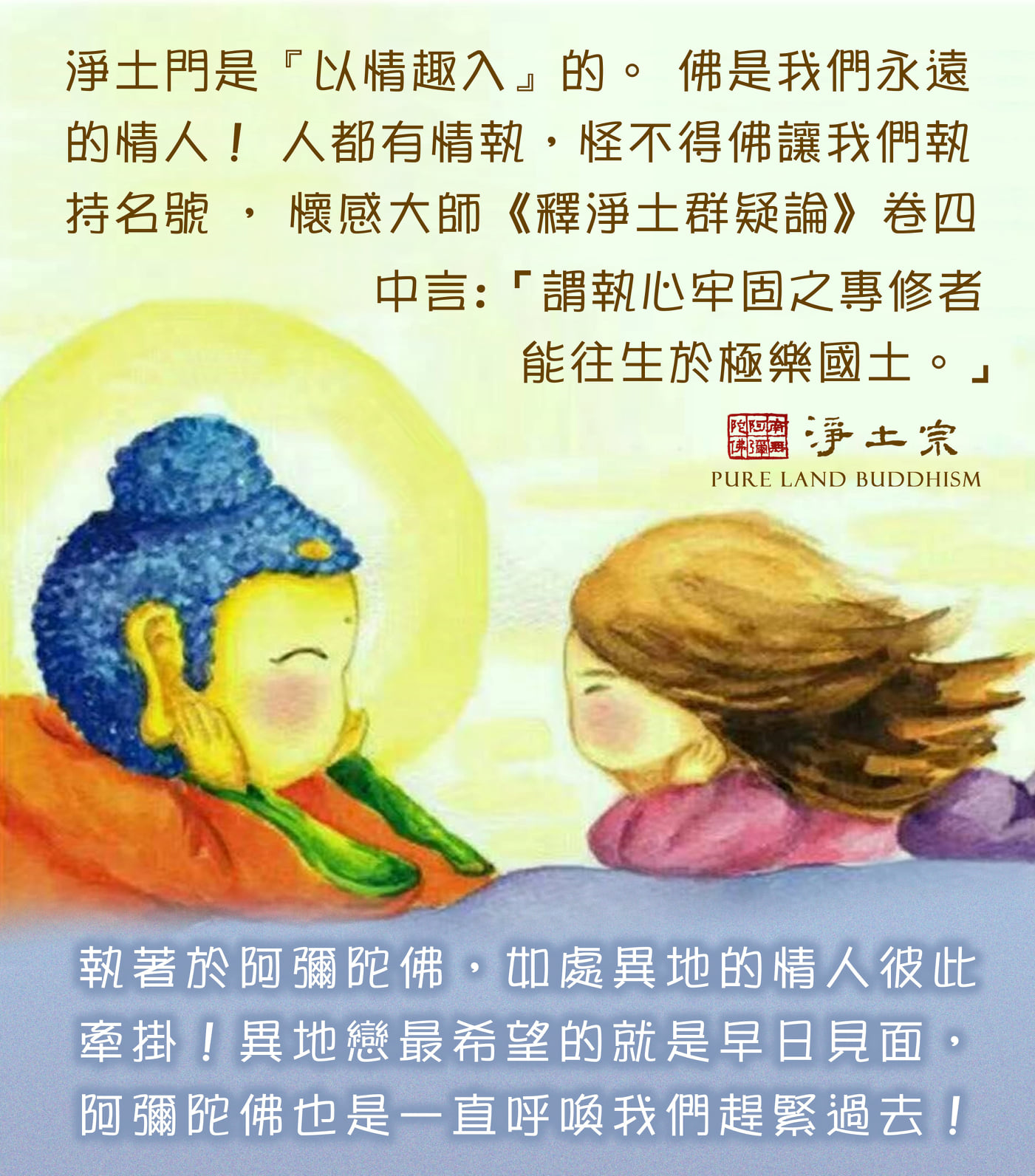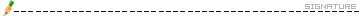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在清季宣統末年中秋節過後的第二天,南京城延齡巷的「金陵刻經處」內,客廳中有許多人在開會。他們都是南京佛學研究會和金陵刻經處的人員,開會的目的,是要選出一位新會長。老會長臥病在床,病情日重,所以授意他們選出一位新會長來。其次,就是老會長如果一旦不諱,如何維持金陵刻經處的存在,並使刻經事業延續不輟。
下午五點鐘,會議尚在進行的時候,內宅傳出了消息,金陵刻經處的創辦人、佛學研究會的老會長、一代佛學大師楊仁山文會老居士,已經安詳往生了。這是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七日,西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楊仁山享年七十五歲。
兩天之後(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末幾中華民國誕生,由秦始皇以後歷時兩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專制政體終告結束。
楊仁山,名文會,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石埭,後來改為石台縣。他於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的家中。
文會的父親朴庵公,於道光十七年文會出生之前,鄉試中了舉人,接著又添了兒子——在五個女兒之後的第一個兒子,可算是雙喜臨門。更可喜的是,在生兒子的第二年——道光十八年戊戌,朴庵公上京會試,殿試中了進士,這可是喜上加喜了。中了進士,授職京官部曹,一家人遷到北京居住,所以仁山自幼是在北京長大的。
文會三歲時,他的父母就為他訂了親,對方是石埭鄉間蘇姓人家的女孩,大仁山六歲。那時民間習俗,男孩訂親,女方總要大幾歲,一來可以照管丈夫,二來可以為家庭增加人手。習俗如此,並非楊家一家為然。
數年之後,文會已八、九歲了,石埭鄉間蘇家寄來書信,告以蘇女因出天花,面上落疤損了容顏。蘇父在信中說∶「我女已殘廢,汝家可另婚娶。」
這時,文會的母親孫太夫人,就以此事徵求兒子的意見,不意文會卻說∶「訂婚在前,出天花在後,不應改變婚約。再者,在人道上,殘廢人我若不要,則以後她將嫁何人?」
既然兒子這麽說,婚事就定下來了。
文會十一歲時,朴庵公帶他去見曾國藩——朴庵公與曾公是戊戌科同年,頗有交誼。文會在曾公面前應對快捷,有問必答。曾公奇之,對朴庵公說∶「此子天資聰穎,可及早安排他去應試。」
朴庵公尚未回答,文會卻接口說∶「我何必在異族人手上去取功名。」
朴庵公聞言大驚失色,曾公則微笑不語。
臨別時,曾公說∶「此子將來必有大用。」
這以後,不論朴庵公夫婦如何勸說,文會終生不曾下過考場。〈楊仁山居士事略〉稱∶
居士童時,示現遊戲,條理秩然。九歲南歸,十歲受讀,甚穎悟。十四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唐宋詩詞,時一瀏覽,間與知交結社賦詩為樂。性任俠,稍長,益復練習馳射擊刺之術。
這就是文會青少年時期的縮影。
文會十六歲那一年,父母為他在家鄉完婚。新婦進門之後,夫婦和睦相處,文會並沒有因妻子面丑而不滿,而蘇夫人也確是治家能手,把家務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是她和所有的能幹女人一樣,性情剛烈,脾氣很大。她絕不因自己貌陋而有所自卑,她處理事情果決明快,就是不大遷就別人。
朴庵公夫婦總覺得兒子受了委曲,朴庵公勸兒子可另行納妾,孫太夫人勸兒子要振夫綱,莫要事事順從妻子。文會對他的父母說∶「我的妻子本來醜陋,別人已經看她不順眼了,我若不敬她愛她,說不定別人就要欺侮她了。至於說納妾,我的妻子只要能夠孝順父母,料理家務,生男育女,這也就夠了。要說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須由我自己選擇,兩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愛才行。如果只在容貌上計較,那不是娶妻,那是玩弄女人。」
朴庵公夫婦被兒子說得啞口無言,此事只得作罷。
就在文會完婚的前兩年——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事,九月占據了蒙山縣,定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咸豐二年,由廣西進入湖南,在岳州得到清初吳三桂起兵時留下的大批軍械,太平軍順流而東,下漢陽、武昌、繼續東下,破九江、安慶、蕪湖。咸豐三年,攻下了南京。
這時,受了戰爭的影響,文會一家十多口也開始轉徙避亂的生活。他們一家人由安徽而江西,而江蘇,而浙江,最後在杭州安居下來。
大約在咸豐八年,文會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到曾國藩的軍中去效力過一段時間。趙楊步偉在〈我的祖父〉一文中,有如下的敘述∶
曾國藩邀祖父去辦軍務,屢次很得奇功。一夜,祖父到曾處談時事,說到滿清之腐敗,祖父提議說我們何必自相殘殺,為異族犧牲?曾公微笑不答。第二天,對祖父說∶汝父年已老,並且後方軍需也非常重要,現派汝去辦理一切軍需,可是你不能置我於危險地位,切記!切記!祖父明白他的用意,當時就回到杭州。
文會回到杭州,大約是二十三、四歲的年紀。楊家在杭州是逃難性質,租賃的住宅並不寬大。後來,楊家隔壁遷來了一家鄰居。這家鄰居的住宅,前面與楊家隔壁,兩家各有門戶,而後面院子卻無牆可隔,和楊家共一個院子。這家鄰居,也是外地遷來避難的,只有姑嫂兩人帶一個小孩。即與楊家是共院的鄰居,難免和楊家婦女有往來。有時和楊老太太閒話家常,有時向楊家借點零星東西。兩家只有文會一個人是年輕力壯的男人,遇有什麽重工作,楊老太太就會找文會為鄰居幫忙。就這樣,天長日久,文會和鄰家那位姑娘牽引出一段情緣。
鄰家那位姑娘不但知書識字,還會作詩填詞。她每天除了看護侄子外,就是讀書吟詩。人也落落大方,不躲避男子。文會和那姑娘接觸多了,才發現她不僅粗通文字,而是一個極有成就的才女。
文會在十幾歲時就曾說過∶「要說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須由我自己選擇,兩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愛才行。」現在果然被他選擇到了。他愛慕那位姑娘,那位姑娘也愛慕他。兩人情苗漸長,愛意日深,周圍的人自然也感覺得出來。那位嫂嫂示意小姑,可以做文會的「並妻」。
文會以此事和父母商議,朴庵公十分贊成,楊老太太卻說∶「遲遲再說。」原來她的兒媳——文會的蘇夫人此時有孕在身,楊老太太說遲遲再說,意思是等兒媳生產,若是男孩,文會就不必再娶;若是女孩,文會再娶,兒媳也就無所抱怨了。就這樣,這件是就擱置了下來。
不意蘇夫人十月懷胎期滿,一舉得男。這一來,楊老太太站在兒媳這一邊說話了∶「妻已生子,無娶並妻之禮,若娶妾則可。」當然,這也是蘇夫人要說的話。
問題是,那個姑娘也是出身書香人家,哥哥在外省做官,斷無為人做妾媵之理。即使她願意,文會也斷不會讓他心愛之人受此委曲。
在宗法社會中,妻與妾之間,差別極大。《白虎通》謂∶「妻者,齊也。」妻與夫站在平等地位,而妾媵只比丫頭的身分高一點,是要受大妻管束的。「並妻」則不同,並妻俗稱「兩頭大」,彼此地位平等,不得互相侵犯。文會既然敬慕那位姑娘,斷無委曲她做妾之理。因此,斷然的對母親說∶「寧可不娶,也不能以此女為妾。」
趙楊步偉在〈我的祖父〉一文中說∶「由於雙方固執不讓,婚事之議遂未成功。」
想像中,這是一場極大的家庭風波。蘇夫人才幹出眾而個性倔強,文會則果斷而又執拗。朴庵公和楊老太太也意見分岐——朴庵公支持兒子,老太太維護媳婦,兩老之間也難免不有所爭執。這件風波的結果,文會和那姑娘的婚事自然是不了了之,而他和蘇夫人之間,也難免不以此而拉遠了夫婦的距離。
至於那位鄰家姑娘呢?想像中自然也是十分傷心。但她是否由此不再和文會見面,還是遷居他處,甚而終身不嫁,黃卷青燈,以了餘年,原始資料中沒有說明,於此也就不敢妄加推測了。
文會心中以後是否還有那位姑娘呢?〈我的祖父〉一文說∶
「經此一次打擊,祖父更覺世事無聊,就終日在西湖邊散步。一日,在湖邊書店裡發現一本《大乘起信論》。···忽悟當中要旨,頓覺愛情家事國事都不願過問了。」
趙文在「都不願過問了」一語下面,打了個括號,注釋說∶「或不盡然。蓋以後孫媳婦中,據祖父說三嫂最像該女,而對三嫂寵愛勝過別人。可見一個人情恨斬斷不是容易的事。」
楊仁山居士早期的傳記資料,有《楊仁山居士遺書》中的〈楊仁山居士事略〉、沈曾植撰〈楊居士塔銘〉、張爾田撰〈楊仁山居士別傳〉、歐陽漸撰〈楊仁山居士傳〉等,都不曾提到上面這一段「情緣」,也許是「為賢者諱」。但是,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歷。如果沒有這一段情緣,或這段情緣有了圓滿的結果,也許就沒有以後的佛學大師楊仁山居士了。
文會遭此打擊,一時萬念皆灰,更感到世事無聊。他丟開公事家事,終日到西湖邊上,徘徊遣愁。
一日,他在西湖邊漫步,在書肆中發現了一本《大乘起信論》,當即買下,置之案頭,家居無聊,讀別的書俱不愜意,拿起《起信論》來讀,不覺間不能釋手,一遍又一遍的反覆閱讀。讀了若干遍之後,忽然悟得論中奧旨,頓覺國事家事、愛情事業都是過眼雲煙。由此開始,他到處去求購佛經,埋首閱讀,他竟在佛經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處。
另有一說,謂∶「先是有不知誰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剛經》一卷,懷歸展讀,猝難獲解,覺甚微妙,嗣於皖省書肆中得《大乘起信論》一卷···。」
關於這一點,趙楊步偉在〈我的祖父〉一文中特別辨明∶
一日,在湖邊書店裡發現一本《大乘起信論》,(一說在安慶購得,乃誤,在安慶購得者乃《金剛經》)買回閱讀,日夜不離手,忽悟當中要旨,頓覺愛情家事國事都不願過問了。
文會自從讀了《起信論》後,就開始到各書肆、寺院中去求購佛經。遇到親朋往他省者,就託人家在外省找。遇到行腳僧,就詢問人家來自何處寺院,寺院中有沒有佛經。他「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學。」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
朴庵公和楊老太太見兒子對佛經著了迷,心中憂愁,但又無可奈何;而文會的蘇夫人,是個剛烈倔強的女性,她對丈夫這般行徑,只有一聲不響,保持緘默,希望由時間來沖淡那一段家庭風波。
轉眼到了同治元年,文會二十六歲。洪楊的太平軍自道光三十年起兵,到現在進入第十三年,已成了強弩之末。是年,曾國荃大破太平軍,光復蕪湖,進圍南京。安徽全省秩序漸漸安定下來,楊家一家人就遷回安徽省會安慶居住。文會到了安慶,仍是埋頭在佛經中,不過問世事。
同治二年夏天,衰邁的朴庵公病倒了,並且病情日益沈重。楊老太太眼見老伴臥病,而兒子鎮日裡念佛求道,不問世事,不由得心中憂急,忍不住責問兒子∶
「你父臥病在床,一天比一天加重。我和奶媳婦是婦道人家,你的孩子還小,似你這樣丟下家務不管,整日裡念經求道,我們這一家老小,將來可有何依靠?」
文會回答他母親說∶「我現在落身世界中,必盡我的天職,雖不求奢望,總能家人溫飽。我並非落髮為僧,不過是研究佛經,將來能廣大流傳,就是我的願心了。」
由夏入秋,天氣轉涼,朴庵公的病並未好轉,終至撒手西歸。一家人按照禮俗舉哀盡孝,做完七七,已屆寒冬。開春之後,文會全家把朴庵公的靈柩運回石埭,擇吉安葬。事畢回到安慶,趕上時疫流行,文會感染了時疫。病癒之後,適曾公國藩檄委他任米穀局事,他為了負擔家計,不得不出山任事。
同治三年,曾國荃攻克南京,忠王李秀成被擒,太平天國滅亡。隔年,李鴻章署兩江總督,當時南京城殘破不全,遂委文會「董江寧工程之役」。這樣,文會一家人由安慶遷居南京。
文會自咸豐末年開始學佛,四、五年來,只是個人摸索,沒有善知識可資請教,沒有志同道合朋友共同研究,甚至於找一本佛經都十分困難。要問江南文物薈萃之地,何以佛經如此難找?原來洪秀全起兵,是以「上帝教」為號召。太平天國統治下的軍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強迫信奉上帝教,不得信他教,拜他神。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曾說∶
嗣是所過之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
太平天國之亂,前後十五年,太平軍所過之處,寺院經像,蕩然無存。這就是楊仁山學佛的那個時代,佛經難求的原因。及至他主持江寧工程局期間,局中有一位同事王梅叔先生,於佛學頗有研究。二人一見如故,彼此切磋佛學。由王梅叔的介紹,又認識了邵陽魏剛己、武進劉開生、嶺南張浦齋、長沙曹鏡初等人,都是有志學佛的人。他們不時聚會互相討論,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才能普濟眾生。這時江南佛教文物經典毀於兵燹,如能刻印佛經,廣為流傳,實是弘揚正法、續佛慧命的不二法門。於此,文會的學佛,又進入一新的境界。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文會在南京約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別勸募經費,創辦「金陵刻經處」。選覓善本、刻印經書,金陵刻經處刻印的第一部經書,是魏默深輯的「凈土四經」-即《無量壽經》、《十六觀經》、《阿彌陀經》,及《妙法蓮華經·普賢行願品》的合刊本。
魏默深名源,默深其子,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生,早於楊仁山四十三歲,他和龔自珍是同一時代的人。默深少有才名,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以屢試不第,三十四歲時從杭州禪宗學者錢東圃學釋典,潛心禪理。五十二歲中進士,數任縣令,六十歲致仕,專修凈土,自署名菩薩戒弟子魏承貫。他手錄「凈土四經」,交其好友周貽朴刊布流通。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在杭州僧舍坐化,享年六十四歲,金陵刻經處首刊的「凈土四經」,就是魏默深手錄,周貽朴刊印的版本。
金陵刻經處自同治五年創立,至宣統三年文會逝世,四十餘年間,刻印了經典兩千餘卷,先後流通經書百萬餘卷,佛像十餘萬幀,詳見本文附錄「金陵刻經處創辦始末」,此處不贅。
文會於同治十二年,辭去江寧工程局的職務,同時也辭謝了李鴻章函聘他到北方辦工程的差事(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駐節天津)而「屏絕世事,家居讀書」。在家中「參考造像量度,及凈土諸經,靜坐觀想,審定章法。」延請高明畫家,在他的監督指導下,繪成了一幅「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懸在家中供奉觀想。
同治十三年甲戌,苹身泛舟遊歷蘇浙各地梵剎,並便中訪求各寺院古舊的經書,供刻經處刻版刊印。聞得洞庭湖西山有古剎,猜想也許會有古本經書,於是泛舟到西山,而「搜求殆遍,迄無所得」,並且在外日久,旅費用完了,幾至不能回家。
這時仍有老母在堂,而兒女相繼出世,多年辦差事廉俸所入,大半用於刻經。為了家計,於光緒元年應聘到漢口主持鹽局工程-他多年辦工程,成了工程專家。他所經辦的工程,堅固省費,非他人所能及。甚至後來他的長子楊自新也辦工程,南京獅子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就是楊自新督造的。
光緒二年,漢口鹽局工程結束,文會應老友曹鏡初之邀約,到長沙去商議設置長沙刻經處的事。同時,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也約他湘鄉一晤。於是到了湖南。順道遊覽南嶽,登祝融峰。也去拜訪了曾紀澤。
紀澤是曾文正公長子,字頡剛,即世稱的曾惠敏公,文正逝世時,遺命紀澤,謂楊某可堪重用。以是紀澤希望與文會見見面。光緒四年七月,朝命曾紀澤為出使英法兩國大臣,紀澤約文會同行襄助。文會便以參贊名義,隨曾紀澤到了歐洲,在歐三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英倫結識了日本的真宗僧人南條文雄。以後三十年間,他和南條保持友誼,不曾中斷。南條在日本為文會搜購得我國唐代散逸的佛經註疏近三百種,文會以之在刻經處刻印流通。
光緒六年,曾紀澤改派為出使俄國大臣,約文會同行,文會堅辭回國。曾紀澤要保舉他做官,他也堅辭不受。紀澤不得已,給他長子楊自新保舉了一個六品同知。
文會回家後,仍忙他的刻經事業。惟這時經書愈刻愈多,不但經書積存的多,而經版的積存也愈來愈多。木版印書,一片木版刻十行,一行刻二十個字,一本十萬字的經書,就要刻出五百片經版。古語「汗牛充棟」,指的就是竹簡或木版而言,文會為了解決經版保存的問題,他和刻經處的人去了幾次蘇州,到元墓山香雪海看土地,想建一處永久的藏版之所,終以經費未集,土地也沒有購成,直到光緒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延齡巷建了新宅,才解決了經版的保存問題。這所巨宅,他後來捐給了金陵刻經處,列為公產,迄今仍被列為政府保護的文物單位。
光緒十二年,貴池劉芝田出使英國,以文會曾隨曾紀澤使英,嫻於英國國情,堅約文會同行為助。文會情不可卻,仍以參贊名義隨行,二度赴英倫。文會這次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國政治制度,和工業發達的原因,領悟到泰西各國富強之道,在於以實學為本。他建議劉芝田,上種種條陳給清廷政府,無奈這時西太后當國,所上條陳有如泥牛入海。文會為此對時政頗感灰心。光緒十六年,劉芝田回國出任廣東巡撫,文會也由英回國。此後他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經弘法為職志。
光緒二十一年,錫蘭人達磨波羅居士來華,由英國傳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紹,與文會在上海會晤。達磨波羅以復興印度佛教為目標,希望得到文會的支持。文會對達磨波羅的抱負十分贊同,曾計劃訓練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協助達磨波羅弘揚佛教,這就是他後來創辦「祇洹精舍」的原因。
文會晚年(六十歲以後),追隨他學佛的弟子為數頗多,如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黎端甫、蒯若木、孫少侯、梅擷芸、歐陽漸等,是其著者。歐陽漸撰〈楊仁山居士傳〉,稱∶ 惟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亦云夥矣。
光緒三十四年,文會在金陵刻經處內,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學堂祗洹精舍。祗洹精舍是年冬季開學,翌年初春,太虛法師也入精舍就讀。《太虛大師年譜·宣統元年》載曰∶
春,大師以華山之策發,棲雲之慫恿,就學於南京祇洹精舍。凡半年,於古文及詩頗有進益。楊仁老授《楞嚴》,蘇曼殊授英文,諦老(諦閒法師)任學監。同學有仁山、智光、開悟、惠敏等,與梅光羲、歐陽漸、邱 明,亦有同學之誼。
文會門下眾多弟子中,入民國後,實以太虛大師與歐陽漸居士二人最為突出。二人同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對近代佛學之復興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歐陽漸,字竟無,江西宜黃人,生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以優貢出任廣昌縣教諭。受同鄉桂伯華之影響,從文會學佛。後以喪母、大病種種挫折,決計捨身為法,再到金陵刻經處,任校對經書之責。越年,文會病逝,以刻經處編校相屬。時值辛亥起義,革命軍攻南京,竟無於危城中守經坊四十日,經版賴以保全。
入民國後,竟無於金陵刻經處內籌設支那內學院。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於內學院講《成唯識論》,門下學人畢集,如呂澄、王恩洋、聶耦耕、黃懺華、陳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門下。梁漱溟、湯用彤亦從而問學。梁任公亦受業兼旬,以病輟,報竟無書曰∶「自悵緣淺,不克久侍。然兩旬所受之熏,自信當一生受用不盡。」
竟無後於內學院設法相大學特科,闡揚法相唯識之學。時,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緇素兩學院遙遙相對,雖屢有法義之諍,卻帶動了近代佛學的進步。
楊仁山居士,由一段「情緣」,促成他進入佛門,於佛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他之創辦刻經處,影響到後來各地繼起的刻經處,如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他之創辦祇洹精舍,門下人才輩出,促成了中國佛教的復興。他是近代佛教復興的啟蒙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韋爾契教授(Holmes Welch)譽之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文會可當之無愧。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5/5/24 下午 04:06:30編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