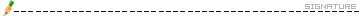2022-02-16 00:00 聯合報 / 張作錦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埃德加•斯諾部分骨灰葬於北京大學的未名湖邊,墓碑由葉劍英手書。(圖/取自維基)
簡體字譯本《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圖/取自網路)
泰晤士高等教育研究機構2021年6月10日公布年度世界大學排行榜,在99個國家1662所大學的評比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並列第16名。台灣的大學未有進入100名者。
到北京參觀「北京大學」可能被很多外地遊人列在行程表上。北大校園風景自然是「一塔湖圖」──博雅塔(儲水塔)、未名湖和圖書館。但還有一處「名勝」,一般人未必知道:在未名湖畔有一座墓,墓碑為一長方形的白色大理石,刻著葉劍英題詞「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下註英文Edgar Snow, 1905-1972。
斯諾是一位美國記者,1928年到中國,1936年訪問陝北共產黨根據地,次年出版《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記》,是外國記者首次將共產黨和毛澤東介紹到西方,造成國際轟動,激勵不少外國人以行動和言論相助中國共產黨;也使很多中國青年嚮往紅區,奔赴延安。在內外條件配合下,幫助中共由壯大而最後取得政權。毛澤東曾說:「斯諾著作的功勞,可與大禹治水相比」。
初臨中國,斯諾還只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年輕人,他起初並無雄心壯志,甚至簡單到僅僅是為了旅遊。可是當他經歷了「九一八事變」和「一二•九學生運動」之後,才發現已置身一個撲朔迷離的國度。他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以及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捕殺和圍剿,同時也看到不少農民、工人、學生卻冒險加入紅軍。
這些都引發了作為新聞記者斯諾的思考: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領導人是誰?這些戰士戰鬥得那麼長久,那麼頑強,是什麼樣的目標,什麼樣的理想,使他們成為這樣的戰士?斯諾說:
我們都知道,要對紅色中國有所瞭解,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裡去一趟!
早在1932年和1934年斯諾兩次計畫訪問蘇區,都未成功。1936年5月,斯諾從北平來到上海拜訪宋慶齡,再提請求,在宋慶齡的協助下,斯諾終於成行。懷著「拿一個外國人腦袋去冒一下險」的心情,在一個午夜登上了一列破舊的前往「紅色中國」的火車。
1936年7月13日,斯諾和美國醫生馬海德祕密抵達延安,他們的到來有助於打破國民黨對蘇區的消息封鎖,因此受到共軍的歡迎和重視,還獲得周恩來「見到什麼,都可以報導,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的承諾。
紅軍給他們每人配發了一匹馬、一支步槍、一套嶄新的軍服和一頂紅軍紅星八角帽。為便於採訪,斯諾的住處被安排在離毛澤東所住窯洞不遠的山腳下。
7月15日,斯諾接到通知,毛澤東將要接見他們。當斯諾等人懷著興奮的心情走進毛澤東住的院子時,主人已經在門口微笑著迎接他們。毛澤東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諾的手,高興地說:「歡迎!歡迎!」斯諾觀察到,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住的窯洞實在是太狹小了。但就是在這簡樸的窯洞裡,毛澤東和斯諾進行了數十次徹夜長談。
根據後來的報導:
毛澤東全面分析了國際形勢,指出可以結成一個反侵略、反戰爭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澤東的談話,開宗明義、簡潔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諾的心。在接下來的數天裡,兩人的話題深入而廣泛,包括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持久戰、統一戰線問題、戰略戰術問題、組織和武裝民眾問題、內政問題、中共同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係,包括自己個人的問題等。
因為毛澤東有晚上工作的習慣,談話常常從晚上九點開始,一直到次日凌晨兩點多才結束。
在對毛澤東和共軍的重要軍政人員進行了深入訪問之後,斯諾又遵照毛澤東「到前線去看看」的意見,到前線生活了一個月。斯諾在紀錄中說:
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的地方,有新鮮的山間空氣,而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餘地。
1936年10月,斯諾離開蘇區回到北平住所,便開始在一些英美報刊發表系列通訊,報導自己在中共根據地的所見所聞,以及毛澤東的戎裝照片,這是全球天大的「獨家新聞」,引起國際普遍的關注。正如斯諾的太太海倫所言:
在斯諾的報導發出之前,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他們的領袖毛澤東,不僅蘇聯人不瞭解,就連中國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說西方了。
作為第一個採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這樣描述他:
他有著中國農民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自己目標的信念。他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兩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彷彿是鐵打的。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但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捲鋪蓋,幾件隨身衣物。
斯諾就此和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一經問世,銷量即超過10萬冊。一年後,它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考慮到要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
《西行漫記》在國際上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加拿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大夫等,都曾閱讀過《西行漫記》,並受到鼓舞。而大批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紛紛奔赴延安,為中共對外宣傳服務。美國歷史學家拉鐵摩爾在為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寫作序言時,曾描述:
在人們政治上陷入思想苦悶的情況下,斯諾的《西行漫記》就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書中介紹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或者只是隱隱約約有點兒感覺的情況。那本書裡沒有什麼宣傳,只有對實際情況的報導。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啊!
用今天的角度重讀《西行漫記》會覺得斯諾對中共有嚴重誤判。誠然,我們不能用今日已知的歷史發展來責備斯諾當年的天真,但是,他前往延安時已經在中國當了七年記者,用「追求事實真相」是新聞界基本守則來審視他這名「記者」,應不為過。其實,他只要稍稍聆聽一下當時中國其他人的聲音,就不至於被批評「陷入中共的統戰宣傳」。
在斯諾進入延安那個年代,有不少中國具有卓見的知識分子,對中共宣稱要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深抱懷疑態度。例如梁啟超,他早就預測社會主義會帶給中國災難。他在1927年5月5日〈致孩子們〉一文中說道:
思永(編按:梁啟超次子)來信說很表同情共產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並非是怕我們家裡有共產黨,實在看見像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擔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
他們(指中共)的戰略真周密極了,巧妙極了,但到他們計畫全部實現時,中國土地將變成沙漠,人民將變成餓殍罷了。
他在同日〈與令嫻女士等書〉中,預測中共會取得政權,他說:
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共黨也不能得到真的勝利——不全像俄國那樣,但是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便算完事。
對照中國大陸今天的發展與崛起,梁啟超當然沒有完全預測準確,但中共建國過程中種種重大錯誤,與當時百姓所受苦難之深重,梁氏的預言,亦屬悲天憫人矣!
斯諾在1960年至1970年又有三次訪華,到了北京、陝西、內蒙古、廣東、西藏、雲南、江蘇、東北、上海等地,寫成兩部長篇報導《大河彼岸》與《漫長的革命》。在這兩部著作中,斯諾依然全面讚頌中共,似乎未注意到中國百姓的生活處境。
但事實上斯諾是注意到了。斯諾1970年的訪華,是毛澤東借他傳個「信息」給尼克森,表示歡迎美國與中國握手。斯諾完成了這個「任務」,但他同時也認識到「新中國」和毛澤東的真實面貌。
斯諾從美國到中國這些年,尤其後來訪問蘇區和撰寫書籍,都曾留下日記,真實記載了他的希望和恐懼,以及感懷和糾結,他的朋友伯納德•托馬斯(Bernard Thomas),使用這些材料,撰寫成《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Season of High Adventure-Edgar Snow in China),應該是了解斯諾最真實的材料──尤其是對他最後一次中國之行。
曾在新加坡《海峽時報》任職的程翔,根據《冒險的歲月》的內容,於2020年6月寫成對斯諾評論的文章,他說,「美國社會半世紀以來,對『紅色中國』產生的幻想和屢屢誤判,追本溯源,同當時斯諾《西行漫記》那一輩左翼知識分子很有關係。」
香港的《開放雜誌》,當年曾刊載了斯諾最後一次回到中國的評述:
斯諾最後一次到中國是在1970年文革時期。他八月經香港到廣州,已感覺「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北京,斯諾見到他當年在燕京大學兼課時的學生、時任外交部長的黃華。黃稱:「我們鄙視金錢和財產,要創造社會主義社會新型更高尚的人。」斯諾後來指出:「毛澤東支配中國的思想和行動的程度,超過了我原來的想像。」斯諾見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很反感和驚訝:「毛澤東的思想是不是沙文主義?是不是埋葬了真理?是不是自相矛盾。」斯諾在四天中都見到人們向黨交心,早請示,晚匯報,覺得是聽了四天向邪教主的懺悔,祈求再生。斯諾去延安和南泥灣「五七幹校」,覺得那裡的情形如同監獄生活。
斯諾回到北京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毛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全面內戰,必須與反革命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鬥爭。」斯諾稱為「毛澤東巧妙地開脫自己的責任。」毛在回答斯諾的提問時說道:「人們崇拜毛澤東是正當的。」後來斯諾在日記中寫道:「毛澤東聲稱每個人都想被崇拜。毛還論證崇拜在政治上的必要性。『皇帝崇拜』是根深柢固的中國傳統。」毛澤東提醒斯諾,他在1965年就說過,赫魯曉夫倒台與他缺少個人崇拜有關。毛向斯諾透露,隨後要掀起對毛澤東崇拜的大規模宣傳,那是必不可少的,那樣才可以打倒劉少奇,奪回領導權。
斯諾發現毛澤東一面以自己是湖南師範學校背景為榮,一面又辱罵中國的教師群體,把知識分子統稱為資產階級。斯諾還發現毛澤東自詡「和尚打傘,無法無天。」1971年2月6日,斯諾因身體疲憊,經廣州去香港,情緒低落。此次大陸之行刺激了他,使他深感困惑不安。他發現毛澤東可厭的一面,對於當年寫《西行漫記》不無悔意。斯諾原先是同情、讚揚毛澤東的,是毛的好朋友,最後,他改變了看法,厭惡毛的為人。
斯諾回到美國,適逢「麥卡錫主義」狂飆,他被迫遷居瑞士,1972年2月15日病逝,部分骨灰葬於北大未名湖畔。
《西行漫記》幫助共產黨取得政權。但是它也可以作為一面鏡子,讓今天的主政者,省思前人的成功與錯誤。
評語[編輯]
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是一個政治術語,含貶義,指的是為某一事業進行宣傳而不完全清楚這一事業的目標的人,常被這一事業的領導人用於諷刺[1][2]。該詞最初使用於冷戰期間,以形容易於受到共產黨宣傳和操縱影響的非共產黨人士[1]。該詞經常被認作是列寧所說[3],也有說法稱是卡爾·拉狄克所說。[4]